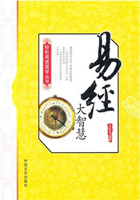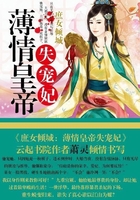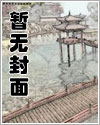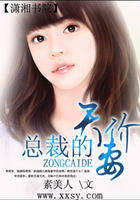如果从体系的角度看刘宗周哲学,那么其最大的特色就是统合归一。这一点已为大多数学者承认。刘汋在评论其父晚年学术特色时就说:
先生平日所见一一与先儒牴牾,晚年信笔直书,姑存疑案,仍不越诚意、已未发、气质、义理、无极、太极之说,于是断言之曰:
“从来学问只有一个工夫,凡分内分外,分动分静,说有说无,劈成两下,总属支离。”
又曰:“夫道,一而已矣。‘知’‘行’分言,自子思子始。‘诚’‘明’分言,亦自子思子始。‘已发’‘未发’分言,亦自子思子始。‘仁’‘义’分言,自孟子始。‘心’‘性’分言,亦自孟子始。‘动’‘静’‘有’‘无’分言,自周子始。‘气质’‘义理’分言,自子程子始。‘存心’‘致知’分言,自朱子始。‘闻见’‘德性’分言,自阳明子始。‘顿’‘渐’分言,亦自阳明子始。
凡此皆吾夫子所不道也。呜呼!吾舍仲尼奚适乎?”这段议论自然并不十分准确,但这段议论足以体现刘宗周哲学统合归一的特色。在这种统合归一思想的指导下,刘宗周开出了自己对儒家心性哲学部分概念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独特理解。这部分内容在他崇祯十五年写的《存疑杂著》里,后来被并入了《刘子全书》的《学言》(下)。《年谱》也通过按语对这部分内容做了总结:
先儒言道分析者,至先生悉统而一之。先儒心与性对,先生曰“性者心之性”;性与情对,先生曰“情者性之情”;心统性情,先生曰“心之性情”。分人欲为人心、天理为道心,先生曰“心只有人心,道心者人心之所以为心”。分性为气质、义理,先生曰“性只有气质,义理者气质之所以为性”;未发为静、已发为动,先生曰“存发只是一机,动静只是一理”。推之存心、致知、闻见、德性之知,莫不归之于一。然约言之,则曰心之所以为心也。又就心中指出本体、工夫合并处,曰诚意。意根最微,诚体本天,此处著不得丝毫人力,惟有谨凛一法,乃得还其本位,所谓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此慎独之说也。先生曰:
“诚无为,敬则所以诚之”是也。夫朱子亦言敬矣,忽诚意一关而缀敬于格物之前,是谓握灯而觅照。象山、阳明亦言心矣,象山混人、道而一心,则必以血气为性命;阳明谓妄心亦照,归之无妄无照,则必以虚无落象罔。先生即诚言敬,而敬不失之把捉,本意言心,而心不失之玄虚,致此之谓致知,格此之谓格物,正心以上则举而措之,盖一诚意而天下之能事毕矣。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宗周哲学思想统合的规模之大。其中以心统摄一切义理性情,一切义理性情皆是“心之所以为心”者,这是从本体上说;接下去又以诚意收摄本体工夫,并以此纠正朱、陆、阳明学说的一些偏颇。
(第一节 心、性、情之间的关系
刘宗周提到的所谓“心性相对”、“性情相对”、“心统性情”都是理学自程朱以来关于心、性、情之间关系的一些观点,但如果上溯这种观点,则可以直追到孟子。刘宗周之所以认为“‘心’‘性’分言,亦自孟子始”,盖因孟子有如下议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在这些议论中用了心和性这两个概念,而他在《告子上》中也提到了情:“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从文字上看,孟子的确做了心和性的分别,但却没有做心和情的分别,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孟子在这里所说的“心”其实就是“情”,虽然这并不为后来的多数理学家所认可。我们拿“恻隐之心”为例来说明。
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是什么呢? 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公孙丑上》)由此可见,“恻隐之心”是一种“不忍人之心”,是由于他人的痛苦或危险在自己这里产生“怵惕”的感觉而有的,人也由此产生帮助他人的道德愿望。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中也被称为“通情”(empathy)。我们很难说这种“恻隐之心”不是一种情感。另外,按照孟子的观点:“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孟子·公孙丑上》,那么“恻隐之心”自然也要扩充了,而孟子又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把这两句话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出,顺人情则可以为善,扩四端之心则可以成性,而性即是善,那么在这个语境里心其实是指情。所谓“恻隐之心”即是“恻隐之情”,其他可以类推。
如果我们总结一下孟子的观点,就应该是这样的:君子的仁义礼智之性是根源于人的内心情感的,比如恻隐之情便是仁的端倪,将这种端倪扩充开来,便可以成仁。其他可以类推。因此,孟子本人可能并没有“由四端见四性”,以性为隐藏(像后儒挖掘的那样)的意思,而只是从明白处指点,由“四端成四性”;并不是情迷性,而是情化为性,而“恻隐之心”便是人的本心,人的本心是一种深厚而且真实自然的情感,是善的基础,仁义礼智四性便由此根芽发展而来,故曰:“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由此看来,在孟子这里的确出现了刘宗周所说的心、性分言,但由于孟子有时将心等同于情,也就是将性、情分言了。只是孟子并不是“心性相对”或“性情相对”,而是心(情)性一体的,从发心到成性在孟子这里是一个过程。结合孟子也曾说过的“恻隐之心,仁也”这样以心为性的话,我们可以认为性和情都是心,而心就是精神世界的总称了。
黄宗羲也有关于情(心)先于性之说,同时他也认为这也是刘宗周的意思,并将这个观点写入《孟子师说》中:
先儒之言性情者,大略性是体,情是用;性是静,情是动;性是未发,情是已发。程子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他已不是性也。”则性是一件悬空之物。其实孟子之言,明白显易,因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发,而名之为仁、义、礼、智,离情无以见性,仁、义、礼、智是后起之名,故曰“仁、义、礼、智根于心”。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先,另有源头为仁、义、礼、智,则当云心根于仁、义、礼、智矣。
是故性情二字分析不得,此理气合一之说也。体则情性皆体,用则情性皆用,以至动静已未发皆然。才者性之分量。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发,虽是本来所具,然不过石火电光,我不能有诸己,故必存养之功,到得“溥博渊泉,而时出之”之地位,性之分量始尽……尤如五谷之种,直到烝民乃粒,始见其性之美,若苗而不秀,秀而不实,则性体尚未全也。
从这段议论中我们可以看出,黄宗羲认为刘宗周反对性为体、为静、为未发,情为用、为动、为已发的观点。因为如此说,则性体为一“悬空之物”,无实义。而孟子的本意是性以情为基础,“离情无以见性”,仁义礼智之名不是在恻隐等心之前,而是在这四端之后,所谓“性情二字分析不得”就是刘宗周所说的“指情言性”,只是此情此性尚如石火电光稍纵即逝,必须经过护持存养才能贞定,就如同苗芽只有经过养护才能得到果实一样。他在这段议论中也是将心等同于情。黄宗羲认为刘宗周反对性为体、为静、为未发,情为用、为动、为已发,“性情二字分析不得”的说法应该是符合刘宗周的本意的。
其实,刘宗周本人在《存疑杂著》中就有对孟子心性说的讨论,兹摘录数条如下: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何故避性字不言?
只为性不可指言也。盖曰吾就性中之情蕴而言,分明见得是善。
今即如此解,尚失孟子本色;况可云以情验性乎?何言乎情之善也?孟子言这个恻隐之心就是仁,何善如之?仁义礼智,皆生而有之,所谓性也,乃所以为善也。指情言性,非因情见性也。即心言性(新本作“善”,似当从新本———笔者),非离心言善也。后之解者曰:“因所发之情,而见所存之性;因以情之善,而见所性之善。”岂不毫厘而千里乎?“恻隐之心,仁也。”又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说者以为端绪见外耳,此中仍自不出来,与“仁也”,语意稍伤。不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只说得仁的一端,因就仁推义礼智去,故曰“四端”。如四体判下一般,孟子最说得分明。后人错看了,又以诬仁也。因以孟子诬《中庸》未发为性,已发为情,虽喙长三尺,向谁说。
世儒谓因情之善见性之善,然情则必以七情为定名,如喜、怒、哀、惧、爱、恶、欲,将就此见性之善,则七情之善,果在何处?又医家言七情,曰喜、怒、忧、思、悲、恐、惊,将就此见性之善,则七情之善,果在何处?《中庸》以喜怒哀乐为情,则四性又属何名? 岂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有性,而余者独无性也邪?从此参入,便破一班。凡所云性,只是心之性,决不得心与性对。所云情,可云性之情,决不得性与情对。朱子曰:“心统性情。”张敬夫曰:“心主性情。”张说为近,终是二物。曷不曰“心之性情”?刘宗周的这些议论主要是针对朱熹“因情见性”、“心统性情”而发的。朱子曾说:“有这性,便发出这情;因这情,便见得这性。因今日有这情,便见得本来有这性。”又说:“性是未动,情是已动,心包得已动未动。盖心之未动则为性,已动则为情,所谓心统性情也。”朱熹的这些观点在刘宗周看来显得支离和没有必要,甚至有不通之处。在统合归一的思想引导下,刘宗周把心、性、情并成一体,即前文所谓“性者心之性,情者性之情”、“心之性情”,如此则心性、性情之间就不再是割裂对待的关系了。在刘宗周看来,甚至连“性情为心中本有之物”这样的话也不能说,因为此三者就是一个东西。恻隐之心即是恻隐之情即是仁。刘宗周认为,后人都把“端”字看错,认为是性发出的端芽,而他认为“四端”就如同四体,而“仁”只是一端而已。“端”既不是端芽,自然也谈不上由端芽发现种子,所以不能因情见性。如果因情可以见性,那由七情如何见得性善?如由恻隐等心见得仁义礼智等性,那喜怒哀乐之情又见得何性?所以只能说“性之情”,而不能说“因情见性”,如果因情见性就会把性搞乱。由于心、性、情一体,所以此三者一善皆善,并且此三者在刘宗周心性哲学的体系中被称为心、独、意。心是同名,自不须说;独为天命之性,前文已有介绍;意为好恶之情,衍生喜怒哀乐、恻隐、羞恶等情感。刘宗周的以上议论可谓十分精彩,但也有不很令人满意的地方。比如他以“四体”的比喻来说明“四端”就过于牵强,也不可能符合孟子的本意。如果刘宗周所说成立,那么“集义”、“扩充”之说又当如何理解?当然,这个漏洞在黄宗羲那里已经被弥补了。另外,朱子“因情见性”之说似也不可废,甚至可以视为对孟子学说的发展。刘宗周对朱熹提出批评,盖因其对“情”字没有作细致分析。朱熹说的“情”乃是“情感”之“情”;而刘宗周所举的喜怒等“情”乃是“情绪”之情,情绪只有过和不及,不可以善恶论,自然不可以见性。并且,如果人的好恶之情是由意志决定的,那么其情感就有“人为”的可能,其真实性就有些值得怀疑了。
刘宗周当然不会认为这种情感是人为的,因为与其相关的人性是与生俱来的,甚至这种人性是以气质为本。他在《存疑杂著》里又说:
告子累被孟夫子锻炼之后,已识性之为性矣,故曰“生之为性”,直是破的语。只恐失了人分上本色,故孟夫子重加指点,盖曰“生不同而性亦不同”云。孟夫子已是尽情剖露了,故告子承领而退。程子以水喻性,其初皆清也,而其后渐流而至于浊,则受水之地异也。盖言气质义理之分如此。但大《易》称“各正性命乃利贞”,又称“成之者性也”,亦以诚复时言,则古人言性皆主后天,而至于人生而静以上,所谓不容说者也。即继之者善,已落一班,毕竟离气质无所谓性者。生而浊则浊,生而清则清,非水本清而受制于质故浊也。水与受水者终属两事,性与心可分为两事乎?予谓:“水,心也,而清者其性也。有时而浊,未离乎清也,相近者也。其终锢于浊,则习之罪也。”从上面这些议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宗周的思想的确对宋明以来的理学所形成的一些思维定式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为后来黄宗羲等人大开新学路奠定了基础。他甚至肯定了告子“生之为性”的说法,只是认为告子尚未体会到人的本质。人生而不同于禽兽,自然有与生俱来的人性在。他也因此不同意程子以气质为人性之障蔽的观点,认为人性必然在人的气质之中,离此气质则人性无以承载。他从气质上说性,便是所谓“主后天”,这种观点和他的理气观是一脉相承的。但这里所说的“后天”与我们一般意义上说的“后天”有所不同,我们一般所说的后天在刘宗周这里被称为“习”,而他所说的“后天”是专指“形而后”而言。因此,因为刘宗周所说的“性”仍是与生俱来的,所以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所谓的“先天”的,如果和“习”相对,那么我们说刘宗周所说的“性”是“先验”的。
在刘宗周看来,人性本善仍是确实无疑的。只是人的恶并不源自肉身,而是源自人的“习”,是“习”使得人性发生了扭曲。他对于“习”的重要性的强调非常值得称道,这说明他敏锐地看到了在人的后天环境中,社会这双无形的手对人的塑造。刘宗周之所以反对离气质而别寻天理,并不见得是因为他对人欲的包容,而可能是因为离气质而别寻天理有蹈虚之弊,使人容易捕风捉影。因此他说:
“朱子以未发言性,仍是逃空堕幻之见。性者,生而有之之理,无处无之。如心能思,心之性也;耳能听,耳之性也;目能视,目之性也;未发谓之中,未发之性也;已发谓之和,已发之性也。”又说:
“未发以前,无极以前,画前,父母未生前,一般伎俩。”所以他是最反对向前一步蹈空的。
关于心性的问题刘宗周在《原性》中也有讨论,可以作为刘宗周对心性关系的总结。他说:
夫性因心而名者也。盈天地间一性也,而在人则专以心言,性者,心之性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生而有此理之谓性,非性为心之理也。如谓心但一物而已,得性之理以贮之而后灵,则心之与性,断然不能为一物矣。吾不知径寸中,从何处贮得如许性理,如客子之投怀,而不终从吐弃乎?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气聚而有形,形载而有质,质具而有体,体列而有官,官呈而性著焉,于是有仁义礼智之名。仁非他也,即恻隐之心是;义非他也,即羞恶之心是;礼非他也,即辞让之心是;智非他也,即是非之心是也。是孟子以心言性也。而后人必曰心自心,性自性,一之不可,二之不得,又展转和会不得,无乃遁已乎!至《中庸》则直以喜怒哀乐逗出中和之名,言天命之性即此而在也,此非有异指也。恻隐之心,喜之变也;羞恶之心,怒之变也;辞让之心,乐之变也;是非之心,哀之变也。
是子思子又明以心之气言性也……我故曰“告子不知性”,以其外心也。先儒之言曰:“孟子以后道不明,只是性不明。”又曰:
“明此性,行此性。”夫性何物也,而可以明之?但恐明之之尽,已非性之本然矣。为此说者,皆外心言性者也。外心言性,非徒病在性,并病在心。心与性两病,而吾道始为天下裂。这段议论中“心性合一”自是可成一说,但此性依气质而立似也有讨论的余地。根据刘宗周“气聚而有形,形载而有质,质具而有体,体列而有官,官呈而性著焉”的话,气聚形立,方有此性。但“心即是气”,终须离此气质方可心合宇宙,此时心虽仍是气,但此气已是宇宙之气,此心也已是宇宙的心,而不应囿于形质之偏。那么,依据心性关系,此性便应是宇宙之性,如何便囿于此形质之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