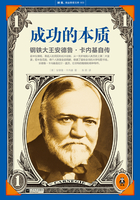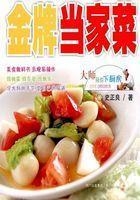一夜大梦,酣畅淋漓。
像睡过了十年的时间,沉睡之中我就想,有梦的睡眠其实比无梦的睡眠更安静,更沉稳,也更容易让人得到缓解。这和医学上的解释有点儿相悖,但却是我的真实感受。之前我一直感觉睡眠不足,朋友们天天聚到一起,逛酒吧,闯迪吧,去网吧,一玩几乎就是大半夜。玩腻了,待在哪个朋友家里无聊地静坐,也会坐上半夜。回来躺床上,一个梦也没有,早晨老醒不了,醒不了也得醒,得上班。
睡眠不足很痛苦,像腌黄瓜,整天没精打采,这种状况直到重回夜里才会改善。晚饭之后我就彻底复苏,双眼大而空洞地炯炯有神,等待着朋友们的如期到来。
昨夜是为我女朋友陈玉过生日,为她的生日我预备了很久,朋友们在酒吧里疯玩,很尽兴,都有点儿醉了,又在深夜浪荡在大街上,七八个男男女女提着酒瓶摇摇晃晃地走着,凌乱地唱流行歌曲。我们还遇到几个打完麻将夜归的中年人,他们像我们的父母那样大,他们不安而略带指责地久久注视着我们,其间张涛走到他们面前,态度挺好地说,没事,不用担心,我们年轻,我们二十五岁。一帮人都胡乱唱起来,我们二十五岁我们二十五岁。好像二十五岁就该这样过,必经的一个路口。
后来我实在有些恍惚,我醉得厉害,我被陈玉送回家里,这是我父母给我留下的准备结婚的住房,办妥这房子后他们就去内地住了。我拉着陈玉的手,我想把陈玉按倒在床上,但我没重心,我从她身边滑过,跌到床上,之后我连睁开眼睛的力量都没有了。但我还能听见陈玉带着嘲讽的一声轻笑,听见她关门而去。我迷迷糊糊地开始做梦,在梦中我还高声唱着我们二十五岁我们二十五岁。整个梦境零碎而散乱,像生活本身,我沉睡中的身体因此总飘荡着,掉不下去。
今天是星期六,我不用急着起床去上班,清醒之后我仍闭着眼睛,享受昨夜飘浮的睡眠,我想这样美好的时刻我该给陈玉打个电话,让她过来完成昨夜没能完成的事,但我懒得动一下,我只是想,我想我打了电话,然后我听见她开门进屋,慢慢向我走来。有时候想真的比做有趣,我继续我的想象,我想她还带着昨夜嘲讽的神态,我说你敢笑我。她说,瞧你昨夜那熊样。我说现在你过来,看看我是不是熊样。她说,我不是过来了吗。我的脸上浮现出一种隐藏了狠劲的笑容,我冷不防伸出手,猛地将她拽到床上,但是天,我真的拽到一个人,我在想象中伸出手,在虚空中一拽,一个人就跌到了我身上。我睁开眼,一张陌生女人的成熟笑脸近在咫尺。我慌忙坐起来,把被子挡在胸前,像一个愚蠢的处子。
你是谁?我说。
笑脸上有了一些惊异,说,还没睡醒?
你是谁?我再一次问。
别开玩笑了,快起来,我们一直等着你。她说话的方式好像与我非常熟,耳鬓厮磨的感觉。
我沉了沉脸,又一次问,你究竟是谁?怎么进的屋?
她有点儿生气了,专注地看着我,声音忽然提高了许多说,我是你老婆,还能是谁,一大早疯子一样。
我环顾四周,我的眼神是迷离的,没有焦点,我惊愕地看见我单身汉的房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了一个成熟家庭的模式,床换成了一张宽大的双人床,整个卧室都经过了装修,最让人气恼的是墙上甚至挂着我和这陌生女人的结婚照,我隆重地穿着西服,她穿了一身白色的婚纱,我们待板地将头靠在一起,一脸假笑,照片上的她竟然还非常年轻,不像眼前,眼前的她已经有三十多岁了,一个成熟的少妇模样。
这个玩笑开大了,我想一定是那帮二十五岁的朋友所干的事,一定是陈玉出的主意,趁我昨夜酒醉,做了这一切手脚。我开始安静了,很专注地看着她,说实话,她算得上颇有几分姿色,特别是那种少妇的风韵,这可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我心里对陈玉说,可别怪我了,这是你们要开的玩笑。同时我脸上浮现出一丝坏笑,我想看到这个沉着女人的尴尬。
你是我老婆对不对。我一脸坏笑地问。
她不解地点着头说,是啊,不是你老婆还能是谁的老婆。
我不再说话,再一次拉着她的手,将她拽到床上。
她惊异地说,你干什么?
你不是我老婆吗?我现在正需要。我说。
这是早晨,孩子在外面等着。她说。
还编了一个孩子出来,我想,看你能怎样表演。不管他,我这时候需要。我说。
好吧,我去把门关一关,今天不知怎么了,疯子一样。她自言自语说,去关了门,就走过来,边走边脱外衣。
轮到我傻了,她真脱,我连忙摆着手说,算了算了,我没兴趣了。
我起了床,她站在边上看我穿,我边穿边说,说真的,别开玩笑了……
谁给你开玩笑了。她说。
好吧,你叫啥?我问。
她再一次瞪大眼睛看着我,用手摸摸我额头,说,你是不是真病了?她的情绪瞬间变化着,又提高了声调说,管你是不是真病,已疯了一早晨,该疯够了。说着她走出卧室。
我跟着走出卧室,在同样大变模样的客厅里,我看见一个七岁左右的男孩子坐在窗边写字。真有一个孩子在,我想,倒设计得周到。我向那孩子走过去,他回过头来,我觉得他的面容非常熟悉,想不起在哪里见过,而且见过不止一两次。
爸爸,你起来了?孩子说。
我装模作样地点点头,走过去小声问,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高慧。
你呢?
孙睿。
竟然还是我的姓。我进一步问,你们从哪里来?
孩子不解地看着我。我摇摇头说,写字吧。
还不去洗脸,早饭都冷了。那个叫高慧据说是我老婆的陌生女人在厨房大声说。
我去了卫生间,拧满一盆水,将头猛地扎进水里,我想清醒过来,现在我相信医学上说的了,一夜做梦,真的睡不安稳。
水凉爽地浸着我的头,我清醒了,但状况依然没有改变。我扬起头,呼出一口长长的浊气,拿帕子擦了水,睁开眼睛,天,镜中的人是我吗?一个三十多岁,早已被生活磨得打不湿拧不干的人,更让人惊异的是我在镜中同时发现那孩子面熟的缘故,他像我,他是我的翻版。除了目瞪口待我没法思维。
端着温热的西饭碗,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轻言细语地对高慧说,告诉我,好吗?
什么?告诉你什么?她说。
真相。我说。
她不明白我的意思。
这一切的真相。
她忽然暴怒起来,大声说,够了,闹了一早晨你还不够,昨晚一晚上你都念着陈玉的名字,陈玉是谁?那个骚货在哪里,你想干什么你就明着来,别装疯卖傻的。
我下意识地躲闪着,这是我第一次面对一个女人的暴怒。我看见孙睿可怜巴巴地站在厨房门口。
我无话可说,我意识到自己的方式大概有点儿不对,我想缓和一下气氛,但我不知道该怎样做,局面有点儿僵,都沉默着,好在孙睿开口了。
爸爸妈妈,我们走吧。
去哪里?我问。
你答应了我星期六带我去游泳的。
游泳?对,我们去游泳。高慧,收拾一下吧,我们去游泳。我想就此缓解一下。
她不说话,到寝室收拾,我跟着进屋,说,干吗生这样大的气?
好情绪都让你破坏了。她说。
是我不对,给你开玩笑嘛。
去游泳池的路上我试探着问,昨夜我喝醉了?
你还说,想好好过个生日,谁知你一喝就醉,醉得人事不省。
我想起昨夜是给陈玉过生日的,她刚好满二十五岁,我比她大一个月。现在总算有一点儿谱,提到生日了。
谁过生日?我问。
你这个没良心的,我昨天忙了一下午,你现在连谁过生日都不知道。
我过生日?我质疑地问。
是猪过生日。高慧恼火地说。
算算看,多少岁了。我故作轻松地说。
爸爸真笨,你过三十五岁生日嘛,这还用算。孙睿说。
我又待了,竟然是十年时间。
你爸爸年轻呢,昨夜一夜都在唱二十五岁的歌。高慧说。
我本不想下水游泳,我不会游,但央不过孙睿一再恳求,他说我答应了要教他游的。我换上泳裤,站到水边,孙睿已抱着游泳圈漂浮在水里,他大声说,爸爸,跳下来。
我不会游。我说。
你会的,你不要骗人,你游得挺好。
我真的不会。
别逗他了,每一次带孩子游泳你都一跃入水。高慧站在边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