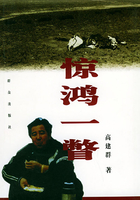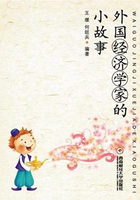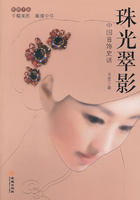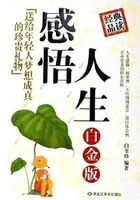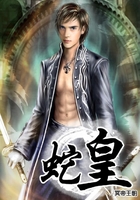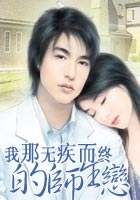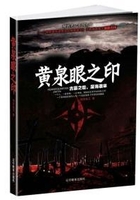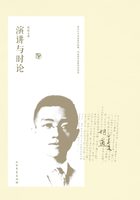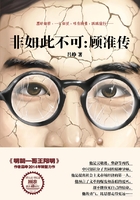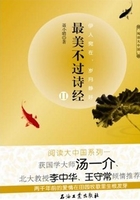关于历史上四川客家学校教育总体发展水平,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也有意采访当地人,或认为四川客家崇文重教,如成都客家文化人士廖明光先生认为客家人文化程度总体上要高于湖广人;或认为四川客家人并不重视教育,如新都县石板滩乡政府文化站的丁启满先生,作为湖广人,认为四川客家人受教育的程度远远比不上周边的湖广人。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谢桃坊身为客家人,也认为客家教育成效并非鲜明,教育普及程度低,只有富有的家庭子女读书的才多,贫困家庭子弟多数难以读书。
不过,这些主位观点多是从感性出发,或出于自己的感情,或以偏概全,难免出现认识的偏颇。因为四川客家教育的时空差异需要进行理性的分析。其实,民国时期教育普及程度低的情况又何止是客家。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的乡村学龄儿童受教育的只有33%,而80%的人未受教育。1926年布朗对四川成都平原的50个农户调查表明,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只有35%,连小孩在内,识字的也只占20%。
因此,要对历史上四川客家学校教育总体发展水平作正确的评价,需要从教育的时空差异出发,对清代以来四川客家进行量化分析,比较客家人与湖广人的教育概况,这种理性思考或许能避免主观臆断,得出较客观的结论。衡量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标准是什么?教育包括两个系统,即培养系统和选拔系统;科举人才属于选拔系统,而学校属于培养系统。一个地区教育水平的高低,是这两个系统综合比较的结果。为此,笔者就四川客家人才状况和学校教育概况两方面对四川客家学校教育发展水平作初步探讨。
一、四川客家人才状况
(一)四川客家科举人才
因资料所限,目前还难以统计出清代四川客家科举人才概况,但可以从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粗略估算清代四川客家科举人才比例及概况。张杰《清代科举家族》从《清代硃卷集成》收录了四川科举及第的21个祖籍明确的移民科举家族。从其祖籍看,客家占5家,即温永恕、李铭熙、卢鸿遇、谢如宾和廖学游等,占移民家族总数的23.8%,但表中列出的四川科举家族如来自江西的聂增荫、章道吉、李士麟、邹容彦等家族有可能是客家而没有列入。因而考虑到有待识别的四川客家,根据前文提到四川客家在移民中的比例有28%,则四川客家科举人才的比例至少不低于其移民人口比例。
这些科举家族在当地文化教育史上占重要的地位。如福建客家袁碧英于康熙六十年(1721)携6子入四川璧山县,袁碧英长子嵩,例增文林郎,第三代袁腾鹤,乾隆年间中四川拔贡,任四川夹江教谕,腾锟也在乾隆年间中举人,袁氏入川第二代后出现科举人才,且以后代有闻人,成为璧山县的望族;璧山陈氏从福建入川后不到200年间共出进士、举人、监生等70多人,在璧山科举人才比例中占重要份额(如表6-2)。三台县谢氏在乾隆年间入川,始祖谢生财耕读传家,治家有方,“以酷爱文学,手不释卷,以身示学,八十七岁仍吟诵不辍”。次子谢用仪乃谢家第一代举人,任潼川教谕。到光绪时,第六代谢绪岷一辈已出进士谢绪熙、谢绪岷等2人,举人6人、秀才30多人,其中谢用仪为嘉庆六年举人;谢绪熙为咸丰二年举人,谢绪纲为光绪十一年举人,谢绪涟中光绪十五年举人,谢氏成为三台第一名门望族。金堂是客家大县,科举家族更是不乏其例。金堂曾氏“人丁最众……其子孙之登科出仕者颇不乏人”;陈氏“耕读传家,其子孙之登科第入宦途者甚多”;黄氏,“其子孙之登科出仕者甚众”。等等。
(二)近现代四川客家名人
1.四川客家名人比例
客家人才比例是衡量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罗香林认为客家人的特点是各业的兼顾与人才的并蓄。前文谈到,清代客家人约占四川总人口的18%。按现在估计的四川客家移民后裔1000万计算,则今天四川的客家人比例不到10%。张明兴也估计,抗日战争和1952年后三线建设以来,外省人口大量迁入和西康并入四川,使四川客家人口只占全省人口总数的14.33%。根据这一比例,笔者据《四川近现代人物传》第1辑至第6辑对收录的近现代四川名人做了统计,力图统计出四川近现代客家名人的比例。
在统计中,笔者对其中的合传人物分开计入,而家族合传的只计1人,结果在所有的435人中,除去50位在四川有影响的外省人,在385名四川籍名人中,本省非客家人110人,其中已识别的四川客家人有28人,占本省名人的7%。当然这只是其中的部分,因为待识别的还有248人,若深入研究也许有未能识别的客家人后裔,估计加起来超过15%。按四川客家人口占四川人口比例的14.33%,则相对湖广人来看,四川客家名人比例要高,四川客家人才辈出。李义让等人对新都的名人研究也证实了该观点。新都客家总数在12万左右,约占新都总人数的20%。而《新都县志·人物篇》列传的人物有37人,其中客家9人,占24.3%。新都的客家名人比例超过了其人口比例。
2.四川客家名人分布特点
为了说明四川客家名人的分布特点,在此将近现代在科技文化界、政治军事界和工商界有重要影响的25位四川客家名人整理。
1)客家文化名人多分布于四川客家散居区,而客家聚居区较少
如东山地区是四川最大的客家聚居区,但在表中东山客家方言区的名人只有洛带的刘子华、新都的廖观音、王铭章等,而多数是分布于客家散居区,如郫县、宜宾、资中、璧山、威远、三台、江津、自贡、乐山、内江、富顺、仪陇、西昌、资阳等地。前文提到的四川客家举人分布也是如此。5位举人即温永恕、李铭熙、卢鸿遇、谢如宾和廖学游等都不是属于东山客家聚居区。
2)客家多出政治家、军人和教育家
四川客家名人多文化与军事领域的人才,名人中缺乏商人,这与客家人崇尚名节、重农抑商的价值观有关。即使是商人,也多从事与传统文化相关的事业。江西客家名人中从事印刷业的较多,几乎垄断了四川的市场。如江西客家书商在成都有“经元八大家”,周达三经营志古堂,成为成都最大的书坊,江西傅金铎经营的“善成堂” 则是重庆最大的雕版印刷中心,江西客家杨宏道在泸州经营的宏道书坊也是泸州最早的一家印刷中心。这些客家书商对四川出版印刷业的复兴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为发展四川的教育事业创造了条件。
3)客家名人的出现都是在入川第6代以后
前文论及,四川客家入川后创业致富的时间平均需要35年,四川客家从白手起家到出现科举人才大概需要80年左右的时间,即约在第三代出现人才,而客家名人的出现都是在第6代以后,按每代25年算,客家移民家族要培养自己的杰出人才,需要150年左右,即所谓百年树人。这说明名人的出现要经过几代人的艰辛。
4)四川的江西、福建客家移民人才较多
从名人的原籍看,在这25位名人中,祖籍广东的有13人(占56%),祖籍福建的有6人(占24%),祖籍江西的有5人(占20%)。从四川客家的比例看,前文提到,广东客家占67%,福建客家占20%,江西客家约占13%。从四川客家名人的祖籍比例看,福建和江西的比例较高,说明四川的江西、福建客家移民人才较多。正如关于重庆的八省会馆的民谚所言,“湖广会馆的台子多,江西会馆的银子多,福建会馆的顶子多,山西会馆的轿子多”。所谓顶子,即科举人才,“福建会馆的顶子多”,也反映了福建客家人才较多的事实。
5)不同的家庭背景造就不同领域的人才
良好的家学渊源是人才出现的重要条件。在四川客家名人中,除天文学家刘子华外,其余文化名人出身都有良好的家庭文化背景,即家庭背景基本上是文化世家,得益于良好的家族教育。如著名作家韩素音出身书香门第;著名学者唐君毅的父亲唐迪风是清代末科秀才,历任四川诸大、中学校教职,其母陈大任名门出身,擅长诗文,重视家教,时比“孟母”,因而唐君毅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诗人林思进的父亲林毓麟,博学工诗,旁通金石书画,林思进幼承家学;著名诗人兼音乐家叶伯和出生于音乐家风很盛的家庭,其祖父叶祖诚,清光绪朝五品衔光禄寺署正,诰封朝议大夫,其父叶大封,清附贡生,候选知州,后留学日本,获法学士学位,祖孙三代皆名重一时;铁路专家蓝田父为廪生、教师;翻译家林如稷出身地主家庭,父为秀才,并留学日本;威远进士林朝圻出生于盐商世家、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恩科进士;诗人谢绪岷出身官宦世家;厚黑大师李宗吾出身耕读家庭;大文豪郭沫若的家庭靠经商起家、耕读门第;画家张大千出生于家道中落的商人家庭。等等。不过,这些书香之家其入川祖先多为文化程度不高的贫民布衣,主要靠佃耕或商贸起家,是耕读起家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四川客家政治军事领域的客家名人中,家庭背景多清寒。除彭家珍出身书香门第外,刘光第、朱德、廖观音、饶国华等家庭条件多贫苦。清贫的家庭环境使他们从小形成一种叛逆的心理,走上从武从军的道路,从而形成独特的人生观。
二、四川客家学校教育发展的时空差异
(一)时间上的差异
清代以来四川文化教育发展分三个时期,即清前期的浑朴时代,乾嘉时期为文盛时代,光绪、宣统以后为进步时代。四川客家教育发展轨迹也是如此。前文已论及,清前期四川处于浑朴时代,经济文化面临重建,正规的学校教育无从谈起。乾嘉时期四川教育开始恢复和发展,四川客家正规教育也从此开始逐渐发展。四川客家教育在嘉庆以后才发展起来,在清末民国时期才出现客家教育的蓬勃发展态势。一个地区学校的创办时间和数量是衡量该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兹以东山客家区学校分布为例说明四川客家教育的发展轨迹。总的看来,清代以来,东山地区创办的私立学校起步晚,数量较少。清前期的浑朴时代,东山客家区无学校可言。东山区最早的书院当属嘉庆年间洛带镇创办的凤梧书院。乡学也是在清代嘉庆二十年开办的。因此,四川客家学校教育起步晚,整体水平并不乐观。正如1947年徐宝田调查,东山客家区 “过去多为私塾,而过去私塾之设立,为数也不多,所以现在客族之中年人和老年人,目不识丁者多,而少年人就差不多皆受过小学教育,至于曾受过中学教育者,比较少,在十余万客族人中,仅有数百人曾受过中等教育,至于大学生,更难得,至多不过数十人而已,故客族人在教育方面仍不能说达于善之境”。
1.清末东山区的义学和乡学情况
东山客家区大部分属于华阳县。前文提到,华阳县东山客家区包括保和场、仁和场、同兴场、隆兴场、西河场、大面镇、得胜场、三圣场等乡场。而华阳东山客家区面积和人口均占华阳县的三分之一。从学田分布看,民国《华阳县志》载,华阳县有学田(地)共2120亩,其中东山客家区有819亩,占38.6%,可见学田比例大。清末华阳县义学、乡学共17所,其中客家区有7所,即大面铺的关帝庙、回龙寺的大面铺乡学、大面铺南华宫大面铺义学、隆兴场龙潭寺乡学、西河场正街西河场乡学、关帝庙隆兴场乡学和得胜场尚义乡学等,占华阳义学数量的41%,客家义学的比例大,而且在所有的义学中,客家地区的义学开办最早。“以上义学、乡学惟龙潭、尚义两乡为旧志所载,余皆嘉道后增置,光绪之际改设学校,一皆废止”。龙潭寺乡学,清代嘉庆二十年开办,办学成绩最好。“为乡学之最早而成绩最优者”。尚义乡学,“清嘉庆二十年设立”。客家区义学和乡学学校数量多,办学时间早,办学成绩好,
2.民国时期客家区的宗族学校
民国时期东山客家区的教育有了很大发展。如前文《客家宗族办学》一节所述,华阳县民国时期城乡共有学校138所,其中私立中小学22所,客家宗族学校共11所,其中中学1所,客家私立学校占一半,而东山区客家人口与面积只占华阳县的三分之一。可见,客家区宗族学校比例较大。客家区的私立学校不但比例大,且客家宗族学校办学成效突出。如1926年金堂县有宗族学校50所,其中以客家陈氏崇本祠为最好。再如华阳县民国时期的学校中,东山区的范氏私立小学校,“该校虽属私立,而校款充裕,成绩颇有可观”;而私立离山初级中学校,“校规严肃、科学亦备,私立中校之井井者”。也就说,在华阳县的私立中小学中,以客家宗族创办的学校比例最大,成效最显著,成为四川宗族学校中的佼佼者。客家区义学或乡学以及宗族学校都能说明客家区的办学热情高,办学质量好,体现了四川客家的“崇文重教”。
20世纪40年代,东山客家区的小学教育更是得到发展。“小学教育之发达完全是最近十余年间事”。成都市龙潭乡更是客家教育发展的典范代表。龙潭乡在20世纪40年代,有小学10所,保小6所,1944年设有初级简易师范学校1所,每校学生从30人至600人不等,全乡在校中小学生约1300人。钟禄元认为,龙潭乡“若与其它各县乡镇比较的话,就可知道他们的教育并不落后了”。1947年徐宝田调查表明,客家居住区,除每乡镇设立的中心保国民学校外,其他各保亦多设保国民学校,同时也有各家族或慈善团体所设立的私立学校,各类私塾仍然盛行。总之,“许多客家人,已颇注意子女之教育,有智识和经济富裕的家庭,他们当然希望子女能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就是无知识和经济困难的家庭,他们至少也希望能使其子女多认识些字,以备应用,故由此而使其小学教育日益发达”。徐宝田的调查基本上反映了四川客家教育当时的实际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