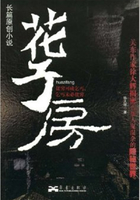二十分钟以后,刘子夕已经坐在祝芳家里了,她儿子已经睡下,她的丈夫不在家。两个女人东倒西歪地埋在沙发里,一人拿着一听啤酒。祝芳说:“其实我已经暗示过你了,要这个男人离婚很难的。你想,我和他认识七八年了,我们就是在最喜欢对方的时候都没有提过离婚两个字。你就不该对他抱太大希望的,这种男人因为被一些女人觊觎着,还真是自己把自己给宠坏了。呵,其实他有什么好的,都那么老了,也不见得有几个钱,要是世俗点的女人又哪能看上他?作家?就写那几本书,又算什么?我们做编辑的看见过多少人会写书,这年头只要识字的都说自己出过书。也就我们这些文艺到骨头里的女人才会对这种男人感兴趣,真是自找的。其实你细想想,他比别人多出什么了?”
刘子夕一下一下地喝着啤酒,听着这堆安慰自己的话,最后酒也喝得差不多了,她才直着舌头悲愤地说:“他想让我做什么?让我一个单身女人做他的情人?一直这样不见天日下去,他怎么就忍心?”
祝芳说:“谁让你找这种还没有离婚的中年男人呢?这本身就是件很危险的事情,你又不是不知道。”
刘子夕说:“我怎么能不知道,我就是想赌一赌,我还能怎么样?真的不结婚吗?我不敢,我心里真不敢,我就是一个俗人。可是,你让我和谁结呢?现在的年轻男人恨不得找有钱女人把自己嫁了,我看不起他们。找同学吧,稍微好点的早被挑走了,剩下的都是歪瓜裂枣。相亲吗?你知道那是多么愚蠢的办法,把两个边也不搭的人放在一起互相挑毛病。就身边认识的人,有过一段共处的时光可以循序渐进,已经觉得很奢侈、很奢侈了。”
祝芳说:“中年男人虽说有些东西是现成的,有房有车,可是他们那点心眼可能比年轻男人还小,想得还多,生怕女人对他们有企图。”
刘子夕彻底喝多了,她笑得歪歪扭扭的,对祝芳说:“你呢,你这七八年里就没幻想过要他离婚吗?你就真不想和他结婚?只不过是你可进可退,反正也是有家的,半死不活也是家,他不给你别人给你,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两个女人“哗”地安静下来了,她们都是第一次这么透亮地坐在对方面前。但透亮之后两个女人反而都觉得可亲了些,真有点像亲人了。
事后两个女人更频繁地约会,彻夜开她们两个人的小型沙龙。现在刘子夕动不动就跑到祝芳家过夜,反正她丈夫也经常不在家,家对他来说形同虚设,这么多年也确实难为了祝芳。两个女人聊完了男人聊衣服,聊完了衣服再聊男人。祝芳给她看自己铺天盖地的衣服,刘子夕一件件地看,看完了再进行点评。两个女人一时都有了些相见恨晚的感觉,恨不得白天晚上都在一起。刘子夕说:“我真想换个单位,天天见那男人,心里硌得慌。”祝芳说:“那就试试吧!不过现在的调动实在是太难,你这真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话虽尖酸,却因为是说在明处的,也像是亲人的话,刘子夕反倒没有那么在意了。把自己的短处给一个人看了,倒像是脱光了衣服后被人看过了,反正也是看过了,再看就不痛不痒了。
又过了两个月,刘子夕的工作并没有调动成,却有一个消息传遍了全杂志社,那就是钟昊佐的妻子从美国回来了一趟又走了,回来是为了签署离婚协议的。也就是说,这个男人真的离婚了。刘子夕感到有些莫名其妙的紧张,为什么呢?说不清。他离婚和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她暗暗斥责自己,绝不能再纵容自己去对这个男人抱有那么多幻想了。即使这样,她那天下班时还是走得很晚,不是因为她很忙,而是她一直磨蹭着不走,终于等到从报社往外走时才反应过来,其实她一直在等钟昊佐的电话。等她从主编室门口经过时才发现,门早已锁了,钟昊佐早就走了。在从主编室门口经过的一瞬间里,她的泪“哗”地一下就下来了,没有爱情都能把她折磨成这样吗?
晚上她又去了祝芳家里赖着不走,祝芳听到钟昊佐离婚的消息一言不发,出神地看着一本杂志,却半天没翻一页。两个女人一晚上没对这个男人发表一句评价,只是各自早早散去,都是装了很重的心事,都和这个男人有关,却都无法说出口。
接下来的两个月,除了上班,刘子夕又开始试图忙工作调动的事,她决定离开,离这个男人远些,现在和这个男人已经不是什么伤害不伤害的事,而是带了羞辱性质的,事关到她的荣誉。虽然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但是她只要在这里多待一天,那就有多一天受辱的风险。他离婚了也未必是和自己有关系的,可是她就是会忍不住幻想他离婚后会怎样。她不想给自己那么多虚幻的希望,一个个像肥皂泡一样,连一夜都过不了就都破灭了,连做梦都不如。
可是工作的调动真是比登天还难,她只好一天天在杂志社里耗着。两个人再没有单独一起出去吃饭什么的,只是平时见了面还是淡淡地打个招呼。
正在煎熬之际,这天下班的时候,手机突然响了,一看却是钟昊佐打来的电话。她有些忐忑,只要是下班的时候他给她打来电话,她就知道是什么事了。果然,他约她出去一起吃晚饭。她沉吟着,他想干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怎么联系过了,今晚这又是为什么?莫不是想和她重修旧好,他现在已经是单身男人了,自由了,和当日不一样了,所以要和她说些不一样的话?要真是这样,她又该说什么?原谅他?告诉他自己一直在等他?太煽情了,太小说化了,恶劣的小说情节,又或者像个烈女那样断然告诉他,不可能了,她不能再回头了。可是,她真的有那么决绝吗?她就真的不给他机会了?那也不好吧,毕竟他现在是单身男人了,有了承诺的权利,而不是当初。天哪!她突然发现她已经在为他开脱,已经原谅他三分之二了。
一个女人为了想要得到一场婚姻就这么下贱吗?她简直要落泪。
她当然还是和他一起去吃晚饭了,因为她拒绝不了,两个人边吃边无关痛痒地聊着一些工作上的琐事,好像这一晚上就要这样聊下去了。刘子夕想,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便也沉住气,他说什么她就随口应答什么。直到饭吃到尾声的时候,钟昊佐看着窗外的夜色突然轻轻叫了一声:“小夕。”刘子夕猛地抬起头,不安地看着他,她知道他要开始了,他终于要进入正题了。今晚的序幕拉得太长了些,已经快让两个人身心疲惫了,现在终于进入正题了,她反而平静下来了。
钟昊佐突然平静地说:“我离婚了。”刘子夕突然觉得血往上涌,像火焰一样烧着她、烤着她,她的目光一瞬间也变得无比明亮,那种明亮也像要燃烧起来一样,却又是无措而慌乱的,不知道该落在哪里。终于,她又把目光落下去了,看着桌面,这样她可以让自己稍微从容些。钟昊佐一直看着她的目光,突然,他迟疑着却又叫了一声:“小夕。”她无声地抬起头看着他,她的目光里有微风里的水波一样的快乐,很轻很浅却是动人心魄。她猜想着他接下来要说的话,一定是与他的婚姻有关的,他打算正式和她谈恋爱了,还是打算娶她了?
她默默地等着他说话,有些虔诚,像个平安夜里等待着圣诞礼物的小姑娘。他的眼睛已经转向别处了,他终于开始说话:“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终归要找个人结婚的,你明白吗?”刘子夕看着他,嘴唇微微张着,却什么声音也没有发出,她怔怔地看着他,像是没听明白他在说什么。他不再说话了,而她就那么看着他,然后她目光里的火焰一点一点地熄灭下去了,变暗了。他仍然不敢看她的目光,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让自己说得从容再从容一点。
“我承认,我是有些喜欢你的,可是我们不适合在一起,我今年已经快五十岁了,你想过吗?”
“可是我不在乎。”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已经哑下去了,像断了的弦。在那一瞬间,她仍然本能地,本能地想把什么拉过来,拉向自己。她真的不想失去那点东西,那就是和他之间那最后一点希望,她都觉得自己有些歇斯底里了。
“你毕竟还小,我们在一起会有很多压力的,世俗的、单位的、亲朋好友的,各方面的压力都会有。”
“你就这么在乎这些吗?”
“我也是人。”
多么好的理由,她还能说什么?他也是人。
这就算是他和她之间的一个告别仪式吧,从那个晚上之后,他和她真的越来越疏离了。在杂志社里,他甚至会远远地见到她就避开,他是刻意的,她知道。他在告诉她,他们之间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事实上,从开始就没有过什么,一切只是她自己想象出来的罢了。
当她把这些告诉祝芳的时候,祝芳说了一句:“我们都不要再理这个男人了,你赶紧再找其他男人,不要再荒废时光了,看看你的青春,我真是羡慕啊!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我也打算离婚了,我不能一直这样过下去。”
刘子夕大吃一惊:“那你离婚以后呢?”她的意思是,你就是离婚了,钟昊佐也未必会娶你啊!
祝芳像看穿了她的心思一样,冷笑着说:“你是不是觉得天下就只有钟昊佐一个男人?说实话,我打算离婚是因为有别的男人向我求婚了,我离婚了才要开始真正谈恋爱去了。”
那个晚上从祝芳家里出来之后,她一个人走到了河边,她在他们曾经站过的那个地方站了很久,在那里她似乎还能找到他留下的气息和那个拥抱的温度。倚在栏杆上她开始无端地流泪,她在做一种祭奠,她要彻底地埋葬这段时光和这个男人,她要强迫自己和他再没有什么关系了,就像根本不曾认识他一样。
就是在第二天,她决定找个女伴合租,她不想再一个人住单身宿舍了,连祝芳都打算离婚再找男人了,也不再陪着她了。她迫切地想找个伴,她已经开始严重失眠,她必须找个伴,而且必须是女人。
那天正好看到杜明明的合租广告后她考虑了一下,离上班不是很远,就去看了看,房子很新,价位也算合理。房东竟然是个和自己一样大的女孩子,这女孩子一个人守着一套空阔的房子让她多少有些奇怪,而且是长得还算漂亮的女孩子,她已经大致猜出她这房子的来处了。聊了几句之后她决定搬家,她顾不得考虑那么多了,她现在只是急需要有个伴,有个可以说话的人,就像快要溺水的人一样随便抓根救命稻草。
有些晚上,她和杜明明一起在酒吧或舞厅里玩的时候,她可以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放纵,这让她觉得自己很陌生,可是那又怎么样?她想:杜明明毕竟在这个城市里有了自己的安身之处,一套自己的房子可以让一个女人暂时结束流浪的生活方式,哪怕是表面化的结束。而她在已经二十七岁的时候有什么?她连个男朋友都没有。就是这点相似把她和杜明明拴到了一起,她们俩只有这点最相似。现在上班的时候仍然能见到钟昊佐,他们还是那样淡淡地打个招呼,像是他们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可就是这样她仍然做不到完全死心,他现在已经没有妻子了,只要他还是单身,她知道自己还不到绝望的时候,人要是愿意给自己希望,哪怕只有一点点空间它都会疯长。
有一天,因为一篇稿子没编完,回去的时候已经有些晚了。刘子夕打开门的时候一愣,那天见过的那个叫岳涛的男人和杜明明正坐在饭桌前,看样子他们俩在一起吃晚饭,已经快吃完了。杜明明看到她,撒着娇说:“怎么才回来?人家都等你一晚上了。”
刘子夕说:“没良心的,等我还不给我留点?”
杜明明指着身边的岳涛说:“你知道吗?这几个菜都是他做的,他当个一级厨师绝对够格,我从来没见过做菜做得这么好的男人。因为太好吃了所以就没给你剩下,不好意思啊!”
那个男人坐在一边微微笑着,却不多说话,又随便聊了几句之后岳涛就走了。
刘子夕说:“他怎么又开始找你了?怎么想起让他给你做菜了?”
杜明明说:“他自己问我想不想吃家里做的菜,天天在外面吃。我当然想了。不过他菜做得很好,他在这方面很有悟性的。”
刘子夕笑笑:“一顿饭就把你收买了,真够没出息。”
杜明明笑:“其实我还见他是一直等着他骗我呢,就想看看他的手段,结果他也没什么反应,现在我倒觉得他还算个不错的男人吧!应该说,是还算精致的男人,还算懂得生活。”
刘子夕没说什么,心里想,恐怕做饭这招已经是他的撒手锏了吧。
杜明明突然问了一句:“你说他为什么找我却不找你呢?是不是你对人太冷漠了点。”
她本是觉得因为刘子夕没有自己漂亮,但刘子夕冷冷一笑,说:“那是因为你看起来比我有钱。”
话说出口了,两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应答,就都沉默了下来。
之后,岳涛又来给杜明明做了几次饭,一次傍晚的时候他来了,提着鱼和菜。他在厨房里做鱼的时候,杜明明静静地走到了他的背后看着他,黄昏时的光线很柔和地投在厨房的墙壁上,蓝色的火焰舔着锅底,不大的屋子里飘起了鱼和姜的香味。不知为什么,杜明明眼睛突然湿润了,她伏在了他的背上,在那一瞬间里,她觉得自己几乎要动情了,但是不能。刘子夕的话早已像谶语一样告诉了她结局,她所做的只是好奇和等待,她布下了套子等待,看这个男人究竟要做什么。可是在刚才的一瞬间她突然有种错觉,有一种家的错觉,和一个精致有情趣的男人在一个不大的空间里做着一日三餐。岳涛不回头,轻声说:“快出去,有油烟,听话。”她一下就清醒了,这个男人对她来说还是个未知,她怎么可以这样?但在走出厨房的一瞬间她还是暗暗对自己说:或许他不是骗子呢?
女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给自己希望,只要是她自己想要的。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周末,她和岳涛逛街的时候,突然岳涛神色紧张起来,他看看周围,拉着杜明明进了附近一家咖啡店。他们没坐在靠窗的位子,选择了一个很偏僻的角落里坐下,要了两杯咖啡。岳涛神色紧张地看着周围,心不在焉地喝着那杯咖啡。杜明明也不说话,就看着他,突然,岳涛开口了:“明明,你身上带了多少钱?”
杜明明正喝着咖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稍微愣了一下,她看着他说:“很少,今天没打算买什么东西,只是逛逛。”
“那,带卡了吗?我现在急需要借些钱,明明,能帮帮我吗?”
杜明明听到自己的声音异样地陌生而冷静:“卡也没带。”
坐了一个多小时,她说:“走吧!”他心不在焉地点点头,她和服务生结了账走了出去,他跟在后面,她的心里有一种奇怪的寒冷,她想:这么快就来了?也太性急了一点吧!难道就凭着做了那几道菜他就觉得可以提钱了?奇怪的是,他那句话说出口的时候她竟没有一点惊奇,就好像在心里等这句话已经等了很久,总算等到了,心底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真是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