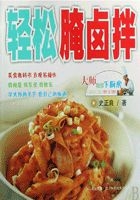陈升有一首懒洋洋的歌,叫《布考斯基协奏曲》,我经常在钱柜点这首歌唱,一般人不会,没有人跟我抢麦,而且我拉了侉的声音能把他们唱得昏昏欲睡。美国还有一部电影,也是讲述布考斯基的事儿,名字叫《苍蝇酒吧》,一个酒鬼整夜混迹在小酒馆里,他是一个美国大兵和一个有波兰血统的德国女郎生出来的杂种,是一个浑蛋牌天使,当然还是个诗人。我周围许多人喜欢他写的诗,当然也包括我。
我总想和布考斯基喝一杯酒,就在他混迹的苍蝇酒吧,然后喝多了一起去大街上打架。但是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这个老混蛋已经死去多年。
我用拼音打“布考斯基”的时候,总是打出“补考四级”,令我想起我悲怆的大学生涯,有些奇异的联想。
那时候我们也经常混迹于各种苍蝇酒馆,这倒是和布考斯基有点类同,事实上,我们最大的类同是没有钱。
在那所三流大学的周边,散落着无数小酒馆,我笑看风云变化,几年之间,许多餐馆关门又开门,我们一次次跟餐馆老板混得熟稔,然后一次次拖欠酒钱,有时候还会把老板娘叫过来,陪我们喝上一杯啤酒。
这种生涯似乎要追溯到更早的中学时代,一群小镇青年去一个东北菜馆喝酒,喝醉了,问老板要三份糖醋里脊,然后再互相搀扶着回学校,跳墙进去,歪歪扭扭地回宿舍。
这些餐馆都太小了,我几乎全部忘记了名字,倒是能回想起餐馆老板的模样,偶尔会怀念一下老板娘的风骚,我们年幼不解风情,以为最风骚的东西是酒,其实总是酒把我们弄得一塌糊涂。唯一能记得起的一个小酒馆叫“英杰”,酒馆名字就是老板娘的名字,两口子开的夫妻店,一个前台,一个后厨,倒也分工明确。两个人都是山东青岛人,过年之后就会带回来一些青岛香肠。
与一般地方的香肠相比,这种香肠黑白分明,不是常见的肉色,切成片,最适合下酒。据老板兼厨师说,他以前是“北京大饭店里的厨子”,要是我们提前打了招呼,要过去喝酒,他就会给我们特别安排两道菜谱上没有的菜哦,最喜欢他做的陈皮牛肉,味道香酥,陈皮的滋味有些像流水,牛肉的感觉像是昏鸦,我们小桥流水人家地在小破店里喝酒,听老板挥斥方遒地跟我们吹牛 B。
那时,我和一个老哥经常去一个便宜的酒吧,啤酒两块钱一大瓶,跟老板喝多了就一起聊诗歌。诗歌是最无聊的话题之一,也是最能聊得兴起的话题之一。要么就转移话题,唱李宗盛的歌,一般都是以《开场白》开场,以《爱情的少尉》结束;要么就比赛书法,学习醉后草书的张旭。我们在老板的店里挥挥洒洒,弄得点墨处处都是,我总是反复地写“大江东去浪淘尽”,而酒吧老板总是写“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待到来到北京,才知道喜欢在小酒馆里泼墨的不止我一个,阿坚似乎更精通此道,北京挺有名的“老家肉饼”就是他题的字,据说他喜欢黄庭坚,但我觉得他的字更有点赵孟頫的意思。他喝多了不但喜欢在酒馆墙上乱画,还喜欢在别人的背心上写字。后来我们就比较忌讳在有笔墨的地方喝酒,很危险,弄不好就把一个餐馆重新装修了。
想来我们都是有小馆情结的人,一到开空调转盘子铺地毯的豪华屋子就坐不住,一到乱糟糟苍蝇与花椒不分的地方就如鱼得水。一次,北京的一家奢华的餐厅请客试餐,发了请柬,上书“请穿中式正装出席”。我没有中华立领,也没有长袍马褂,只能胡乱穿着衣服去了,到了那里,倒是美鬓如云,遇到了同样散乱的几个朋友。我们一商量,附近有一家新疆小馆似乎不错,我们就溜了出来,奔赴热气腾腾的新疆馆子。大盘鸡、馕炒肉看来比美鬓如云更能提我们兴趣。
小馆是我们的通行证,有的人的最低生活标准是“农妇、山泉、有点田”,我对小馆最低要求是:有厕所。
三联书店旁边有一家贵州菜馆,名为“君琴花”,腌臜小馆,做不错的贵州菜。这里跑堂的叫大勇,他认识的北京文化人比我多。我曾经在此大醉,从中午一直到晚上,啤酒四瓶四瓶地要,很快就摆满了桌子,然而走肾是个难题,需要出门,穿过一条不算繁华的小路,去 300米以外的公共厕所。我趔趄着一次次从车流人群中穿过,一个酒鬼未免悲从中来。然而每次想起这里的糟熘土豆片、酸汤鱼,还有热情的大勇,我还是忍不住隔三差五地来一次。
如果一个餐厅有厕所的话,我希望这个厕所能稍微有些特色。我曾经关注过一些餐厅的厕所,寻觅一些奇形怪状的。“湘鄂情”有一家店把厕所包装成太空舱的模样,而一家名为“辣遍天下”的馆子,厕所门口贴着一个招牌,上面是几千字的“如厕指南”,其贫嘴风范不逊《大话西游》里的唐僧。然而这些都是一些大馆子,不在草根之列。王府井的胡同里有一家巴掌小店,做不错的湖南菜,名为“古道田”,看名字颇像日本的早稻田大学,里面的厕所就打造得很舒服,玻璃幕墙,所以我经常去这家,因为能够舒服地走肾(作者注:这几家餐厅都已经不在了)。
去外地出差,我也总是寻找一些小店来试试菜,往往也会有些新发现。和同事去湘西出差,到饭点的时候,我们就溜达到街上,寻找一些小店。我判断一个陌生地方的小店总是遵循着我个人偏颇的原则:要到老城区寻找看上去有些年头的小店,小店里最好人声鼎沸,拿起菜单至少有几个菜看上去对我的胃口,这样下来应该不会错。那家湘西的小破店里已经没有了座位,我们被引领到内屋,老板的孩子正趴在桌子上写作业,老板指着那张堆满书籍的桌子说:“您二位坐包厢吧。”
那天的菜里必然少不了各种腊味,味道非常诱人,我们打算去买点腊肉带回北京,于是自作主张地去了菜市场。菜市场狭仄破败,湘西的口音弥漫其中,我们找了一家专门卖腊肉的地方,买了不少腊肉、腊肠。回北京之后,我的朋友深夜给我打电话,问我吃没吃腊肉。
原来他吃了之后开始拉肚子另加发烧。
小店总会有小店的龌龊与肮脏,对于卫生至上、讲究膳食的人来说,小店就是他们的噩梦。但是对于另外一些热衷民间小馆的人来说,小馆就像美梦一般美好。
在这些梦里,我们安心地喝酒,掏心窝子,把店老板当成可以诉衷肠的兄弟,老板娘也多半风情,他们令这场惨白的美梦多了一些异样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