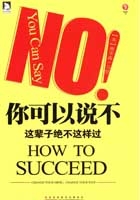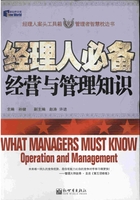当然了,这个题目套用了卡尔维诺的小说《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如果在西藏,一个吃货,想吃得更好,只需要找到一个人,这个人叫贺中。
贺中是个酒鬼,也是个诗人,出生在甘肃甘南,身上有许多个民族混杂的血统,80 年代到西藏,赶上了西藏最盛大的黄金一代。那时候大批文人聚集在此,马原、马丽华、扎西达娃、龚巧明、于晓冬、李知宝、罗浩、金志国、段锦川、牟森、李启达、裴庄欣、田文..于晓冬的油画《干杯,西藏》记录了那批意气风发的面孔,从那幅油画里还能见到贺中年轻时的模样,带着点青涩,远远没有现在的江湖味道。
贺中依然在西藏,当时小伙子成了一个胖子,留起了倔犟的小胡子,如同阿凡提,向上翘着,这也是贺中的标志性形象。他经常是说完笑话,哈哈大笑,捋捋自己的胡子。这个西藏酒鬼简直是全国文化界驻西藏办事处主任,各路诗人、艺术家、导演作家,但凡到了西藏,第一件事就是向他报到:老贺,我到拉萨了。
2010 年 8 月,我去了西藏,向贺中报到。
8 月末的西藏,青稞已经收割完毕,青稞垛规矩地排列在田里。拉萨河的河水有些涨,甚至漫过了河滩上的丛林,它蜿蜒着围绕着拉萨城,汇入雅鲁藏布江。八廓街依然热闹非常,转经的老人、磕长头的虔诚者、小贩和背着单反相机的游客,他们用自己的视角辨别着大昭寺和布达拉宫。
马原说,在 80 年代,他是第一个在拉萨穿短裤上街的人,穿着短裤,骑着车,引得拉萨人大呼小叫。而今西藏大街小巷,短裤随处可见,还有姑娘们的超短裙。
没有去大昭寺,我们钻胡同,去了一个茶馆,喝五毛钱一杯的藏茶。这才是藏民们聚集生活的地方,老人们在此闲坐,聊天,这里也是信息港,各种信息在此融汇,然后传遍拉萨。藏茶微甜,我们身处其中,就像把一块咸鱼放进大米粥里,突兀又有点不合时宜。周围的藏民们聊天,跟女老板开点粗俗的玩笑。每到一处陌生的地方,我都愿意第一时间找到这种有意思的地方,坐在混杂着各种当地口音的人们中间,接点地气。
饿了就去玛吉阿米,这是来西藏旅游的小资们的圣地,位置绝佳,就在八廓街,里面聚集着各路内地游客,勇闯天涯的背包客,寻找秘境的老外,他们顺着狭仄的楼梯向上,坐在靠窗的位子,看着藏式的屋顶。这是被溢美的西藏,也是外人心中的西藏,就像外地游客到北京,总是想去四合院里吃顿饭,去后海看看灯红酒绿一样。
贺中摸着自己的小胡子,讲讲笑话,下午的时间显得悠长。吃饭,改良的藏餐,没有那么强盛,而是温软的,文艺的。我们在留言本上写字,北京的诗人阿坚总是写顺口溜,许多流行语如果刨根问底都是来源于他,比如,“四大俗:上一次镜,出一本书,去一次西藏,信一回耶稣”。这次他在留言簿上写道:“唐古拉,优敏芭,拉萨河边发发呆,玛吉阿米喝藏茶。”
如果想在西藏吃点别致的,好吃的,拉萨不是好选择,好选择是朝向林芝,朝向藏香猪。从拉萨到林芝,驱车需要六七个小时。顺着尼洋河向东,周围的山势起着细微的变化,先是安静而突兀的山,冷峻如内心狂野的汉子,穿过海拔 5013 米的米拉山口,顺着山势而下的时候,山的起伏顿时柔美了许多,植被丰茂,牦牛在很远的地方吃草,小花在很近的地方开着,有点肆无忌惮。
在工布江达县的大街上,藏香猪出现了。坐了几小时的车之后,我们在此停留一下,吃顿中饭。藏香猪们旁若无人地走在大街上,遍体黑色,体形微小,据当地人说,这种猪就是这么大,不会更大了。藏香猪的成名得益于四处往来的游客,如今藏香猪已经成为当地名吃,价格也被炒到天价,与之齐名的是尼洋河的冷水鱼。不过据当地人介绍,不少街边小馆打着藏香猪的名义,卖的不过是饲养之后的普通猪。
一份藏香猪肉价值不菲,当地人用它炒菜,做腊肉,果然肉质紧密,浓香,能吃出一种奔跑的味道,感觉每一块肉都经过了长途奔袭。然而当地的藏民不善烹调,密集的川菜馆子里的出品也平平。如果用这种猪肉做红烧肉应该也不错,至少不会比浙江的双头乌差,但是遍寻也没有找到藏香猪做的红烧肉,颇有点遗憾。
一群吃货体内藏着馋虫,此时正是盛产野山菌的季节,松茸、黑松露、鸡枞一个不少,但是整体品质逊色于云南同品。令人惊喜的是这里的野山菌漫山遍野,随便在草滩上走一圈就能捡回不少蘑菇,然而并非所有的蘑菇都适合食用,越是鲜艳越是有毒。这跟姑娘相仿,越是美艳,越是多是非。
当天下午,我们到了林芝。林芝名吃是石锅鸡,在林芝的鲁朗镇,满大街都是石锅鸡的招牌。最近两年,北京也有了专门经营石锅鸡的小店,打扮得藏味十足,然而在当地,每一家小店都狭仄简朴。石锅鸡的要素首先是石锅,用的是一种名为“皂石”的云母做成,这种石头产于墨脱,需要人力背运出山,再经过当地人仔细凿制。这种锅保温好,据说富含矿物质。许多人都要在此购买一枚石锅,价格在 400 元左右。第二要素才是鸡,藏鸡凶悍,一扇翅膀能飞到树上,这种鸡肉肉质致密,同时在里面加入了各种林芝野山菌和手掌参。手掌参也是当地特产,状如微小的手掌,煮过之后呈透明色。一起用高山雪水炖开,也是富有当地特色的美味。我们在公路边的小馆子里吃石锅鸡,为其中的鸡是公鸡还是母鸡争论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是公鸡,因为母鸡需要留着下蛋,藏鸡蛋往往卖得比鸡还要贵。
吃完石锅鸡我们继续上路,路上美景无限,然而这一切美景,到了鲁朗的扎西岗村,又都算不上什么了,恍如一炉沉香屑,而在扎西岗村,又一根藏香悄悄燃起,芬芳着天地万物。
人们习惯把鲁朗称为“东方瑞士”,其实看过这里,瑞士不过是“西方鲁朗”。高山草甸之上开遍野花,硕大的云杉、柏树满山遍野,把远处的山染成墨绿。一簇簇的绿,令人应接不暇,马匹与牛羊都在山坡吃草,木质的栅栏有意无意地分割着田园,云雾从半山升起,缓缓的一条丝带,佩戴在鲁朗的额头。
村庄不大,恰到好处地摆放在山坳里,黄昏时有炊烟,清晨也有炊烟。我们去了乔卓玛的家,同来杭州诗人潘维说,这个奇妙的地方是他们前几年到西藏时发现的,后来成了他们的据点,每到西藏必来一次。
这里院子宽敞,藏式的老民居,厨房里熏黑了墙壁,而黄铜的锅碗都锃亮。可以什么都不做,也可以上山采蘑菇,或者到后山的经幡阵里,听听风声。西藏总是在莫名的时候给你不知所措的美,叫人一次次崩溃成为碎珠又转瞬黏合。天空中的云静静翻滚,云彩不在意人间。
这时一条三条腿的小狗盘卧在山冈上,它看着我们,神情凛然,蹦跳着走了几步,然后又回了一下头。
晚上的晚宴是乔卓玛一家人操持的,在这里我终于见到了藏香猪做成的腊肉,比我想象的肥,几乎见不到瘦肉,整块发黄微微透明的脂肪,对着夕阳,闪着肉欲的光泽。各种当地的土菜,一把蘑菇,两捆青菜,各种腊肉,下午杀的一只鸡,对于一个吃货来说,这些足够了,足够亲切,也足够乡土。
夏天天气凉爽,我们坐在院子里吃饭喝酒,聊天扯淡,厨房就在旁边,冒着炊烟,藏民一会儿就端出一盘菜。没有想象中的好吃,菜做得随意粗犷,以料理食材来说,藏民不及内地的汉人更在行。然而这有什么关系呢?
饭毕之后才是重点,在二楼的火塘边,我们开始了诗歌朗诵会。屋里灯光昏黄,闪耀着 80 年代老旧的光。
仿佛昨日重现,几天来的俏皮话与黄段子都悄悄隐去,80 年代的文化胜景重现。那些四五十岁的老诗人,认真地读诗,藏民的小孩偷偷在门口张望。马原也开始背诵自己写于 80 年代的一首诗,江苏诗人庞培开始唱一首海子的《九月》,每每有精彩处,大家停下来,喝一杯,再继续。我和阿斐算是在座的仅有的两个 80 后写诗的人,我们互相读对方的诗,故意找那些稳准狠的文字,那些青春勃发的诗。
即便旅程再精彩,饭菜再迷人,诗歌依然是我们最好的下酒菜。为一句话,我们喝一杯;为一首诗,我们喝一杯;为一个故去的朋友,我们喝一杯。贺中还唱起了歌,这个每天晚上混迹于酒肆的胖子,还是个很好的歌者,各种民族小调信口拈来;阿坚也开始唱歌,他唱的是男高音,起步就是帕瓦罗蒂的《我的太阳》,为了一首歌,我们又喝了一杯。直到夜色深沉,我们都沉沉地醉去了,摇晃着回到栖居的小屋。小木屋里简陋,我和阿斐共处一室,他变魔术似的,又找出一瓶酒。
是的,我们如你所想,又喝了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