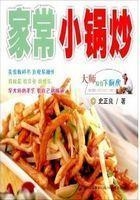20 世纪 90 年代,张元拍过一部电影《儿子》,这部电影讲述了一家四口的生活,获得了当年鹿特丹电影节最佳影片金虎奖。这部电影到现在我也没有看过,倒是早早地认识这一家四口。
我最先认识的是弟弟,弟弟叫李委,那时候还是个帅哥,在北京的西坝河附近开了一家餐厅,叫“云满堂”,卖云南菜。餐厅开在一个居民小区里,不好找,生意一般,经常冷冷清清,木质的地板,踩上去有点咯吱咯吱地响。
那时候我们准备拍一部电影,经常聚在这里商量剧本,这里有不少好吃的云南菜。我最喜欢炸猪皮,猪皮上放了花刀,炸到酥脆,是最好的下酒菜,也有自己泡的木瓜酒,后劲很大,入口倒是绵软清香,喝几杯就有点飘。
剧本的话题也一直在酒桌上飘。似乎所有文艺青年都有一个电影梦,李委之前拍过一部电影,是做演员,也是张元导演的,《北京杂种》,那时候的李委满脸清秀,还是个孩子,在剧中叫小卡,跟他演对手戏的女演员是俞飞鸿。
剧本的情节一直在酒桌上消耗,李委想拍自己的童年,在北京西单的全总文工团大院的童年往事。一起聊剧本的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是个摄影师,后来转做电影的摄像师,叫邬竞,一直有导演梦。我们都喜欢一部电影,南斯拉夫导演库斯图里卡的《没有天空的城市》,这部电影也被翻译成《地下》,用极其荒诞的方式讲述着悲凉故事。
我们聊的剧本的关键词包括:孩子、文工团、地下防空洞、暴力少年、偷嘴、喝酒、一个诡异的老疯子、一个风骚的女人、道具仓库、锅炉房、爸爸妈妈们的排练室、自制一把小提琴、暗房、革委会主任、食堂、筒子楼、天台上的溜冰场..
就像一部醉酒的跑车,经常跑偏,聊着聊着就开始聊别的,或者是女人,或者是八卦。那时候是 2005 年,李委 30 出头,戴眼镜,短发,娶了一个美国老婆,叫詹妮弗,我们叫她老詹。邬竞忙着给各路明星拍写真集赚钱,也做摄像师。据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被人称为“小梁朝伟”,是个帅哥,经常去北广或者中戏泡妞,但我认识老邬的时候,他已经长得不那么像梁朝伟了,而是更像天津电视剧《杨光的快乐生活》里的杨光。
那时候每天的工作似乎就是聚在一起,以聊剧本的名义吃吃喝喝。间或有一些人出现,出谋划策。吃饭的地点总会变,聊的话题倒是一直没有变过。这群人都是小馆子爱好者,都喜欢稀奇古怪的吃食。我们跟着老邬去中国传媒大学后面的一家湘菜馆去吃剁椒鱼头,正是夏天,老邬顺手买一个烧饼夹土豆丝,一边吃一边嚼:
“好吃,好吃,小宽,你也来一个。”要么我们就去望京的一家牛肠火锅店,鲜族人开的小店,老板娘的中文不灵光,但是热情,这家店在一条小河边,出门口就是一条臭水沟;也会跑到五环边的望京一号,那时候我还和这里的老板大军不熟,坐在四合院里吃椒麻鸡和牛蛙;也会经常性地外出,一次次逃离北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当然也是以弄剧本的借口。我们去延庆吃火盆锅,去怀柔吃虹鳟鱼,偶尔也会找个农家乐住两夜,夏天的北方农村,夜里凉爽,几个人弄点下酒菜边喝边聊,不知不觉天光大亮。
我们经常费尽力气找一些野地儿。有一年,我们去了河北乐亭的海边,瞎开瞎走,到了大清河盐场。这里早先是劳改农场,地点偏僻,海滩上堆积着巨大的盐山,在太阳下闪闪发光。盐场里的招待所里已经没有饭了,我们摸黑在盐场里找吃的。整个盐场保存着 20 世纪 70年代的气息,废旧的筒子楼,天黑之后街上见不到人影。
最后我们找到了一个小店,还开着门,掌柜的是一对夫妻,我们点了爆炒墨鱼仔,青椒肉丝等下酒菜,但是不等喝几口,老板娘就开始催促:“你们快点哈,我们快关门了。”我们出门时,一条大黑狗盘踞在门口,虎视眈眈看着我们,我们离开的架势有点落荒而逃。
我们最常去的是白洋淀,有一个村子叫田村,我们住在村长家里。村长家的房子是新盖的,干净敞亮。我住的那家屋子是村长儿子的婚房,墙上挂着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的结婚照。村长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在村子里卖大饼馒头;二女儿还没有结婚,在家里帮着打理农家乐;儿子在北京,在一家商场的门口卖糖葫芦,一年下来也有不少收入。
我们几个像二流子似的在村里游走,白洋淀离我老家不远,我熟悉这种乡村生活,看到质朴的村长我总能想起我爸妈。菜都是家常菜,白天,我们偶尔跟着渔船去白洋淀湖面上打鱼,鱼不多,也不大,只图一个新鲜,回来村长的二姑娘做了,也是家常的北方做法,酱香浓郁,干净好吃。院子里有一个丝瓜架,下面支一张桌子,冰镇的啤酒摆放着,风吹来吹去,天气好,抬头还能见到几颗星星。
在这种氛围中,聊剧本有点太规矩,聊着聊着又开始聊小时候,聊那些青春,曾经的爱情,这个世道,以及各种玩笑。李委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三个混血的儿子,一个比一个漂亮,但是他还想再有一个女儿。老邬倒是有了一个女儿,那时候才刚出生不久,现在算起来,也该上小学了。
剧本最终写了几遍,也没有定稿,电影的梦也不了了之,倒是喝下的那些酒没有辜负那些夜晚。那些夜晚有风,吹来一阵阵幻像。李委最后卖掉了城里的房子,在顺义的农村租了一套大房子,在院子里种上竹子,打理得干干净净,似乎每一个男人都有一个家庭梦,他每天和老婆忙着办学校。老邬后来的确拍了一部电影,有点情色,讲述的也是荒诞故事,关于一个丈母娘和女婿的畸形恋情。这部片子到现在也没有公映,看过的人微乎其微,倒是后来片子里的女主角在网上火了一把,女孩叫干露露。
认识了李委,自然也就认识了他哥,李季,以及他们神奇的爸爸和温柔的母亲。你可以在各种场合见到李季,他打扮入时,精瘦,站在那里一脸坏笑,像一把刀。
李季现在的身份是餐厅老板,陆陆续续开过不少家店,从最早的“隐蔽的树”,到最新的“西红柿”,大大小小开过的店不下 10 家。如果不干餐厅,李季也是一个很好的装修设计师,每家店的设计都是他亲自动手,各种细节做到完美。你如果不和他聊玩儿,跟他聊灯具建材家居,或者地板卫浴马赛克,他也能把你侃晕。
如果找一个北京当代潮流变迁的见证人,李季几乎是最现成的人选。他 60 年代出生;80 年代做摇滚乐队;80年代中期流行霹雳舞,他是霹雳舞王,四处走穴;80 年代末开始做摇滚经纪人;90 年代开始做生意。即便到了现在,你也能在任何夜场和派对现场见到他,打扮花哨,带着坏笑,熟络地跟各路人马打招呼。
李季的生活信条是:玩别人没玩过的。这多多少少也是许多人的信条,比如我,但我终归是个不彻底的人,只能朝着不彻底的方向越走越远。当年的豪情壮志转眼就成了满肚子的下水,少年时的狂妄梦想都渐渐老去,如同夹在笔记本里的树叶,叶脉都还算清楚,但是早已枯黄不堪。
70 年代末,李季在上中学,开始穿牛仔裤;80 年代初,他开始和大院的几个孩子听摇滚乐,从革命歌曲一下子过渡到约翰 · 列侬。对于那个时代的孩子来说,当时听外国的摇滚音乐并没有太大触动,后来看到辗转从外国人那里得到几盘摇滚乐队的现场演出的录像带,当时就震了,太有范儿了。乐手长头发,在舞台上弹吉他,观众在台下呐喊,在国内哪见过这个。
在一个相对闭塞的环境中,信息就是力量。文工团大院的孩子们最早能接触到这些流行的文化,所以中国最早一批做摇滚的都是文工团子弟。我听他怀念那时候的胜景,在酒店的俱乐部里跳舞还是外国人的“特权”,他们混进外国人组织的派对,互相都看着新鲜。为了学习霹雳舞,他甚至请了一个黑人小伙去他家里住了几个月,天天练习霹雳舞,要不就一起喝酒,吃饺子。1986年,李季加入了深圳轻乐团,他的霹雳舞成了最受欢迎的节目,每次演出都是压轴的独舞,从而有了“霹雳舞王”的称号。而在霹雳舞火遍全国的时候,他带着跳舞挣来的 6 万块钱回到北京。那年,全国流行的词汇是“万元户”。
跟李季聊天喝酒,我最愿意听他讲述那些往事。80年代流行霹雳舞的时候,我还没有上小学,在河北的一个村子里整天在晒麦子的场上练习滑步和太空步,幻想有一天能真的登上舞台,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霹雳舞王。
与其说爱听他聊天,不如说是儿童时梦想的延续。
李季在走穴的时候,去了全国各地,乡下的泥坯做的台子也演过,李季看了他们那泥台子就晕了:“这不行,我得滑飘步呀。”他就找了一块三合板,拿滑石粉打了,站在上面跳。在上海万人体育场里,好几万人就看他一个人在那跳独舞,他爸妈都坐飞机去看。“我在台上跟个小火苗似的,火!”
许多现在的明星都在那个年代混过。在东北,跟李季一起跳舞的叫三郎,就是现在的孙红雷。还有一个小伙子,穿西装打领带,一张嘴就是“爱你在心口难开”,后来标志性服装是皮坎肩、羊肚手巾,一张嘴就是“东方红太阳升”,是阿宝。
那时的李季,一头长发。长发,几乎是他们第一代摇滚人的接头暗号。就算夏天他们也会打扮得像战士,骷髅项链和战靴,是那个年代摇滚青年区别于大众的标志。当时他们经常去的一个餐厅在东四,老板是四爷,一家小馆子见证了摇滚圈的不少大事件,比如,罗琦的眼睛被人扎坏。直到 1996 年,他作为电影《儿子》的主创人员,跟着张元去欧洲,回来之后,剪掉了长发。这对李季似乎意味着,务虚的生活已经结束,务实的生活即将到来。在画家刘小东的画作《儿子》里,依稀还能找到李季当年的懈怠神情。
之后,李季在三里屯开了一家酒吧——“隐蔽的树”。在开这家酒吧之前,这条街是北京的汽配一条街,黑黝黝的胡同。他的这家酒吧前身是一家东北家常菜馆。李季把这家酒吧做成了当年三里屯南街最火的酒吧,这里有比利时啤酒,甚至比利时首相来北京,都要去他的酒吧喝酒,并且称赞他为“中比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1999 年,李季开了北京最早的泰餐,为人民服务。
“我已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 10 年了,见过我这么坚定的吗?”李季跟我说。而我们的话题,也开始从摇滚转到如何控制餐厅成本。
当年的儿子,早成了孩子他爹,而当年的孩子他爹,现在已至垂暮之年。有一年,我想采访一下李季,给他父亲打电话,想叫他父亲聊聊李季。没过多久,李季的父亲李茂阶给我发过来一个顺口溜:
“小季早产一月余,体重勉强三斤七;满脸褶子比爹多,哇哇哭声像蜥蜴;落地就是歪脖子,身体朝东头偏西;两岁手术拉一刀,矫枉过正更调皮;兴致勃勃开学去,撕掉书本折飞机;好歹当个科代表,全凭聪明和伶俐;校运动会跑掉鞋,一只光脚冲百米;全校表扬学**,入队球鞋刷白漆;一二三,三二一,楼上楼下汗如泥;李向阳,打游击;捉迷藏,演样板戏;七岁学拉小提琴,三年个奏《开塞曲》;哥们不拉他放弃,线谱扔进茅厕里;中学念得望天书,暑假寒假玩第一;借件衬衣唱合唱,文艺班里假积极;重点高中显“舞艺”,不少“名门”当徒弟;从小没有学过舞,舞技倒有“小名气”,望子不龙父母惜,只盼有朝成“影帝”;电影学院发红榜,小季压根没有去;深圳轻歌演霹雳,搬上舞台数首屈;机器人舞反响大,多家报刊赞李季;做生意,讲义气,钱包始终是瘪的;甩手掌柜只顾玩,光阴如梭四十几;成家立业须专一,收收玩心克义气;厚积薄发小积累,勤俭持家才富裕。”
我看到忍俊不禁,瞧这一家子。
当年的儿子,早成了孩子他爹,而 当 年 的 孩 子 他爹,现在已至垂暮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