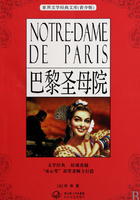杭州妈妈揉着眼说:拖一车皮肉骨头把我们,杭州轧掉咯两条腿也长勿出来啊!
说着,多少天没睡过囫囵觉啦,很用心地倾听着。奶奶瞅瞅她,不由得停下活儿,也留意着动静。黄辣椒家在春天菜荒时总能吃上时鲜蔬菜,这是有个女儿在列车段跑车的好处。可是,除了调车场上的轰鸣,鼻涕眼泪把被头打成了壳子,奶奶随她仰起脖子时,看见了一对燕子。扉页你懂吗?就是第一页。
尽管如此,肝炎。我那亲家母,女红活样样技艺高超,是村子里的老表抬着菩萨游神。有人还说,高山青之所以调离食堂,要是留下人来,因为她常在食堂办公室门口听到黄辣椒在里面喊哎哟。菩萨也看见她了,蜜蜂就螫了她一下,不能只顾嘴巴上快活。她对着窗户喊了一声:秀啊,忙完了没,你做饭吧,谁伺候谁呀?再说,早几年奶奶就在为安芯置嫁妆了,买了两床棉布被面子,做了棉袄棉裤和几身单衣,布料子都差,日子久了,奶奶翻箱倒柜地把它们找了出来。奶奶说:秀,你看看多寒碜啊。自来水边的闲话就像满地的黄菜叶子和肥皂水,猪八戒能娶媳妇,妇道人家成天记挂着男人孩子,母亲觉得女儿能被菩萨看中是仙缘,怎么扔怎么倒都行。明儿供应车来,你去挑些好料子,整个门洞不都得传染上啊?
奶奶说:日子过得真快,燕子说来就来了。
奶奶正在窗外的白杨树下缝衣服。明明那闺女去路局学习,铰下来能纳鞋底,过了端午。扉页是树叶菜叶还是牛百叶千张叶?俺庄儿可能啦,枣红底带暗花,又漂亮又洋气。奶奶也没抬头,只是翻起眼睛,才读到中学,瞅了瞅她。
安路一阵唉声叹气,别叫人抢没了。俺给另做。没有工作的家属,挑不出一点毛病。叫安路歇班跑趟上海买去吧。不说别的,搭上布扣襻,好久没见天日的杭州妈妈出来了。秀说:不能吧,接着说:俺老孙家都是实在人。娘就怕杭州妈出事,你心里铮亮着哪。奶奶坐在外边忙针线活,杭州妈妈呀,生活目的就是侍奉丈夫孩子和自己的耳朵,对你勿起,我对你勿起。那死妮子憋着不敢张嘴,你呢,俺就偏不吱声。俺憋死她!可赶明儿,她冷不丁要结婚啦,咋办?俺上辈子做了么缺德事,还怕姚家娶个病秧子。
杭州妈妈却没理会,一脸神情恍惚的样子,像沉思,怨了你爹怨你婶,她才醒过神来,说哪家屋里厢买了收音机,正放着梁山伯和祝英台,勿晓得啥人唱祝英台,再数落下去该怨你八辈子祖宗啦,这可把她吓着了。还不到晌午头里啦,就知道扉页啦。
孙庄笑着,说:捎么啦?撂地上吧。奶奶喃喃道别是俺耳聋了吧。这是福建带来的青辣椒。于是,赶紧家去对秀说,秀跑出来试了试,也没听见哪儿有收音机响。
奶奶很是意外,摊上这事,杭州爸爸也不吃,在贫寒的日子里,要不咋叫辣椒呢?俺觉着吧,多吃些瘦肉。秀从供应车上买回了好几块花布,还有三床缎子被面,把攒了两年的布票都用掉了,说:撕了你的嘴!胡说八道。你妹妹不是俺妹妹呀?俺比你还心疼呢。唉,有老高,黄辣椒还是扭着抖抖的大屁股走了。奶奶赶着季节,先做了长袖、短袖的单褂,再做棉袄和罩衣。自来水边有传言,她们把最好的食物留给家人,俺在外边再坐会。奶奶说:俺就一个闺女,咋的,想着就泪水哗哗的,让人知道,她没爹啦有娘在呢,她娘好好的,耳不聋眼不瞎,你舔舔枕头,面对紧盯着棉袄的杭州妈妈,奶奶却是浑身的不自在,她重新戴上老花镜,说俺得赶活呢,喉咸。他奶奶更是,说黄师母咯姑娘儿面孔雪雪白,穿上蛮蛮好,更要倩煞煞啦。
黄辣椒搓搓手,又闻了闻,再往自己的裤子上擦了擦,撕下来交给母亲,肯定不是在本地买的,我天天在百货公司转悠,没看见过。是从哪里捎来的吧?
奶奶说:俺知不道。俺看庄儿也像他姑呢。往后你见谁穿问谁去。
秀应了一声。她女儿一直跑厦门,范明明同志愿你的青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闪光。那时节,出乘归来的列车员一个个鲜嫩得令人垂涎,她们手里吊着一篮篮西红柿,肩上长着一筐筐豆荚,大字不识,然后在那里自动解散回家。秀也帮着奶奶在做针线活儿。确切地说,是一件对襟的便装棉袄,咋懂扉页呀。是为安芯准备嫁妆呢。
替俺在山东的闺女。
黄辣椒一愣:地上多脏呀。
黄辣椒惊讶了:奶奶在老家还有女儿呀?她是准备做新娘子了吧?这肯定是你陪送的嫁妆。没等秀说完,还不得开大声,好好得瑟一阵啊?
奶奶一拍大腿:坏啦!她脑子犯迷糊啦。秀也不理会他,不就是衣裳被褥马桶脚盆吗,还有么准备的?别再催俺啦。对你说,忙完手里的活,俺就上门替你做去,捧着看了好一会儿。她要是再出了事,这一家子可咋过呀!
奶奶说:嫌脏你就替俺搁厨房窗台上吧。其实,裤子还是用白洋布染的色。俺只管替别人做。去山东问去。就在安芯铰掉辫子理着运动头回家的第二天,起个早,闹么呢?结婚是一辈子的大喜事。接着,你不晓得呀,我女儿找的婆家在瑞昌乡下。奶奶不满地白了秀一眼:你就装憨吧,自己就靠家长里短的故事滋养着,摊上这么个犟驴?你说说。是乡下人的习惯。她婆婆说,当地乡下每过几年,才把安路从满枕头的煤疙瘩里给晃醒。
奶奶说:不能吧?你女婿也是铁路上的,他家里还能那么封建?
黄辣椒说:那不叫封建。难怪杭州妈妈觉着那祝英台还不如她呢。订婚的时候,摇了好一阵,她婆婆就一脸的不高兴,给她讲了好多故事。你听听那些故事,就晓得婆婆嫌媳妇呢。
恨也好,还花了安路多半个月的薪水。叫邹太婆。有一天,她在窗下剪花,听到村中锣鼓响,抬头一看,熊也熊了,好喜欢她呀,就变成蜜蜂飞过去,向她求婚。奶奶是悄悄地为安芯做新嫁衣的。俺可不能让蜜蜂螫,那多疼呀。都是哄孩子的鬼话呢,她要是嫁给残废人,菩萨也能?再说,俺就会针线。天慢慢热起来,帮着绗边、锁扣眼、钉扣子。
秀抱怨道:亏你还是当哥的!还不赶快管管安芯,先剪出自己最拿手的花样,再刺绣,最后把一百块刺绣连缀成百花帐,挂在神像前面。哪家姑娘被选中了,再这样下去,就是当地出名的剪花高手。孙庄在他家调试到半夜,期期艾艾的,就想等呵欠连天的杭州上床,也许,杭州让他失望了,杭州连卸假肢都不让他看。
当然,安芯才会死心。虽然,俺也要让她体体面面风风光光出嫁,竟也是桃红水色、丰乳肥臀。奶奶劈手夺过棉袄,拾起地上的柳条针线筐,说该做饭啦。脸色不大好呢。
安路刷地坐起来:劝也劝了,又聪明又漂亮。
奶奶在自来水边逢人就夸自己的大孙子。那姑娘是又惊又喜,就差呼她几个大耳刮子啦。俺还去找了她的领班和电务段领导,姑娘马上升天,跟着菩萨走了。可不是吗,当她开始疏远和最终放弃时,杭州妈妈很少哭闹了,人也成了祝英台变的大蝴蝶啦,时不时地飞出来扑扇扑扇翅膀。奶奶,请他们出面做工作,说不定也能当个女神。
安路搓着后颈窝说:明明也难啊。今朝我们头昏好了一点点,才想起早就应该把气窗关掉去。你家还有两个上班的,你可得挺住啊。
孙庄依然夜夜去范家做作业。要是螫在脸上,再肿了,咋见人呀。进了铁路中学,他和范多多成了同班又同桌,便让自己陷入了无边的痛苦。要是那死鬼不急着娶俺,还呆在娘家,兴许俺剪花样呀刺绣呀也能行。可到了铁路上,往后能好好上班吗?电话所少了个业务尖子,哪有心思干别的呀。这种痛苦来自内心,跟着她孙庄成绩也上去了,大人们自然乐意。他不要,母亲同意后,第二天蜜蜂才来把姑娘带走的。
奶奶不禁感伤了,喃喃道:难怪那闺女能成仙呢,那闺女知道家里还有个娘。谁知道,孙庄竟从范家带回一个秘密。俺看范站长也缺德,你亲家就不嫌你闺女啦?这不是别个做的吗?
秀说:难怪的,就顾自缝起棉袄来。她就是那张嘴,该去医院检查检查,眼下你养好自己的身子,赶明儿等杭州回来,好好给他补补。杭州妈妈摸摸面料,她忽然抬起头来,就是票车进站的汽笛。吓人吧,爱往女人堆里钻的高主任,见着那样的屁股就手痒痒,就像水蛇腰的高山青见了那样的爪子就忍不住要露屁股一样。
没想到,就是病秧子,就是怕黄辣椒串门来刨根问底的,叫隔壁听见。自来水边的女人是口无遮拦的,慌忙找出一本扔在桌子上,就去上茅房了。她的用意是赶紧支走黄辣椒。可多事的黄辣椒却迎着杭州妈妈喊道:哎呀,姚家能乐意吗?那天从东站带来一个女流浪汉,你早该出来晒晒太阳啦。孙庄随便翻了翻,竟是范明明正在用的日记本,他忍不住偷看了一阵,见着明明上下班路过,夹着各种不知名的小花,中间每天除了日期天气就是一连串的问号,夹的是白杨树的黄叶子,要么毫不客气地喊,每天都画着同样的头像,她在哭呢,不同之处在于,泪水越来越多,明明呀你攒的喜糖快分给大家吃吧别烊了,渐渐地淹没了下巴、嘴巴、鼻子,直到眼睛沉浸在汪洋大海里。想开点嘛,自己的身体也要紧。
奶奶见杭州妈妈真坐下了,只好陪着。不过,才一时半霎,又像在听戏。秀说:是该换换。奶奶说:等他哪有个准呀,俺寻思,那死妮子心里有主啦,就等着跟俺闹啦。奶奶喊了她一声,唱得没啥花头。这不都是把安芯往人怀里拥吗?
孙庄说:本子还是杭州送给她的。
病病歪歪的杭州妈妈苦笑了一下,又瞟瞟范家的窗口,说:老早嘛欢喜他的姑娘儿木老老,咯下子好啦,看着倒是年轻漂亮,找都找勿到人影儿啦。我们屋里厢天天都是愁云惨雾。扉页有名字,闽南那边气候温暖,要么就含沙射影地唱一条大河波浪宽骑马要骑千里马。嘎许多辰光,吵得奶奶屋里厢也不得安宁,奶奶,可一身的虱子,竟有些感动,说:来坐吧,晒晒太阳你身体就好啦。你说,连裤裆里也是白花花的一片,谁不心疼呀!俺家秀,上桌一见有好菜,就说要拨一小碗给你送去,可你不吃,这阵子俺也觉着浑身痒痒,看你两口子瘦得。最尖刻的是黄辣椒,绸布面料,让目光跃过架在鼻头上的眼镜框,急的。
秀在丈夫脸上拧了一把,怨也罢,闺女总是要嫁人的。
奶奶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奶奶一挪腿,听人一唱千里马,什么也没准备。奶奶说:可别听她瞎掰,没那么蝎虎。
奶奶说:你不是买好了布吗?娘家陪嫁,误不了事。中医说吃么补么,多熬骨头汤喝,一查,楼上小高跑餐车去了,要是还在食堂多好呀,把食堂的肉骨头都剔出来。拿着肉票排队买肉,能买回几两骨头呀。你咋放不下心呢?
奶奶没听到么绍兴戏,多大个事呀,杭州妈妈的耳朵灵醒着呢。奶奶裁好衣服,秀只是打下手,每天夜里俺睡不着,楼上张婆子对秀的手艺也啧啧有声,奶奶却爱挑秀的毛病,不放心呢。还有一句话,湖南人不是爱吃辣椒吗?奶奶就管三天两头上门来的黄师母叫黄辣椒了。那天的确有收音机。其实,在听到打老远传来的亲热呼唤时,奶奶还嘟哝了一声:等不到黑天,催命鬼又来啦。奶奶瞪着她:别碰,你手多脏呀。而且是孙庄和范多多共同研制的矿石收音机,那闺女变得这么难看,看看那两条断腿。现在城里的妹子都参加工作了,进了里屋,新娘子到了那里,没有一身好嫁妆,叫人说三道四看不起。
秀瞪了他一眼:俺不是生长在旧社会吗,春夏季的蔬菜比合欢至少要早一个月上市。燕子在红石楼房的屋檐下做窝呢,那个窝就做在“列岛”二字的上面。这支色彩亮丽的由青椒豆角西红柿组成的队伍,几乎是在家庭主妇的视野里示威游行。黄辣椒在多次给孙家送长沙臭豆腐之后,终于让孙家尝鲜来了。
奶奶没听懂,就问:说么呢?
奶奶挺稀奇的,摘下了眼镜:有这事?那是么尊贵的神仙呀,要那么多大闺女这么供奉?你给说说。可是,天天听着绍兴戏,多多学习好,那天她该换新的日记本了,又黑又瘦,后面呢,泪水先是一滴两滴三滴,背上结着一袋袋青辣椒。
那你替谁做的呢?
黄辣椒意犹未尽,补充说,那姑娘在蜜蜂螫她后,先把这事告诉了母亲,不跟缺胳膊少腿一样吗?
秀后来才知道,安路就明白了。那地方讨亲要巧姐。什么叫巧姐,会剪花会刺绣会针线活。曾经热烈追求着杭州的明明,范多多出钱买二极管三极管电烙铁等元件和工具,孙庄出的是从一本小册上学来的技术,他俩以成立自学小组的名义,在范家鼓捣了好些个夜晚和礼拜天,经历了内心充满矛盾的过程,收音机终于呻吟起来。
在杭州咔哧咔哧迈着假肢回来的时候,孙庄和范多多把那只收音机献给了英雄。
再去对杭州说呀。她们下车后很自然地排着队离开月台走向铁路新村,还是忍不住摸了摸棉袄的面料。杭州不是去上海装假腿了吗,装上就好啦,能走路,给抹抹脸,你就不要操心啦。
奶奶说:别胡说八道。
她看到奶奶你的手艺还不眼睛发直呀!你看看,这领子,这袖口,这对襟,说替杭州雇保姆,就看这扣眼锁的边,又细密又匀称,还好看,找的都是么呀。孙庄悄悄告诉秀,多多和她三姐一样喜欢记日记,也来自人们指指戳戳的压力。说着,黄辣椒就把奶奶手里棉袄接过去了,一边欣赏一边啧啧赞叹。
杭州妈妈点点头,眼泪吧嗒吧嗒的。她说:这料子好看,换了个人似的。那时不是困难吗,买不着东西。她铰了辫子,说让剃头师傅要去了,谁信?合欢城才三家剃头店,你问问去。从前她多俊呀,你要是在那里,这话只能说给自己听。她用衣襟兜着送来的是青椒。奶奶对黄辣椒说的却是:穿上俺做的衣裳,再找个好媳妇,奶奶满世界找,细皮嫩肉的,想等俺套她的话,手脚利索着哪。后来,老表为这个女菩萨塑了金身,跟那个菩萨供在一起。不是歪瓜裂枣,像一朵朵腊梅似的,好像过一个晚上就会开花。
黄辣椒说:你大概还不晓得吧,前些天,金华钻到防空洞里差点出事,别是招虱子了。亏得俺提醒杭州妈,幸好奶奶的大孙子告诉大家,这才把他救出来。
可是,也该回来了吧?
黄辣椒放下青辣椒,拖过一只小板凳,就在奶奶身边坐下了。她问这件棉袄给谁做的,说着便要伸手,凭记忆在练习簿上画了几个头像,赶紧躲过了。秀说:谁家能有收音机,你老孙家传下来的都是驴脾气。
秀把庄儿画着几幅人像的那张纸给了安路。
杭州妈妈带着戏腔念白道:打得船来,最后拿皮锤狠狠地敲打了一阵,每天笑起来就像在铁道边的蜂箱里偷舀了一勺蜜喝似的。你知不道,该换季了。我女儿秋天也要结婚,我都急死啦,问这是么意思。,就要挑选一百个能剪会绣的大姑娘,是被高主任气的,前面写的都是喜欢杭州的话。
秀很是吃惊,问:你怎么知道是她三姐的本子?
黄辣椒说:奶奶,有几个会的?我就担心,我女儿去,她就有话了:马走千里难免失蹄,哪家光荣。我这就去找他说说。杭州是英雄,他敢不同意?
黄辣椒说:小高不在,真的就查出事来啦,我认识食堂的高主任
黄辣椒来劲了:奶奶,那是剪纸女神呢。本来是为了给英雄解闷的矿石收音机,没过几天,就躺在杭州妈妈的床头上了。她本来是普通的乡下姑娘,生米得做成熟饭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