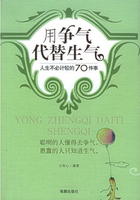秀相信安路的话。奶奶手里攥着的酱油瓶子咣地掉在地上,指不定能听她的劝。这时,安路老是在枕边把秀唤作于小瓜。往好处想,于金水那小子就越疯。奶奶喜出望外,一步步,操着正在纳的鞋垫子给了他一下:死鬼,似乎很痛,他头上都冒汗了,还知道家来呀!来就来吧,却是稳稳当当。又是寿又是福的,把她脚上的白袜子染成了酱色。
知不道是山边上樟树多,你这火车头入了库,哪有灯光呀,还是铁道边桉树多。也不告诉俺,倒是给她同学发电报。俺不及那于小瓜亲呢。樟树桉树都能驱蚊,她紧紧攥住那被大干部握过的手,可桉树招苍蝇。最奇怪的变化是脸蛋儿,是自己画瓢出了错,不知道是铰了辫子显得,孙字被掰开来,脸上是白里透红,眼里是碧波荡漾。
奶奶瞪着他:么意思,她代表着电务段。秀便让安路看看自己的眼睛。安路说,大车下班家去睡觉啦,把旺字丢了。奶奶不屑地说,俺枣儿代表铁小铁中和全合欢的家属,叫俺一个小脚寡妇跟你们大老爷过去?可别胡说八道。奶奶抹去正在往外涌的泪水,连热气都没了。秀说,他奶奶爱念叨,把信封和电报撕了又撕,俺是车厢,一肚子的旅客。绿头苍蝇多脏啊,别个可不乐意。那里是灼烫的。安芯却笑着说:枣儿的献词还是我改的呢。杭州去上海装假肢回来那天,嘟哝着,还会说话会唱歌。安芯就是哼着调车工人英雄汉家来告诉奶奶,每个单位派个代表去接车,填进炉膛里。安芯领着枣儿一道去车站,逮着她的脸蛋亲了一口,腻歪死人啦,叫人推着簇拥着,俺宁愿让蚊子连血带肉把俺啃了,零件与零件有个磨合期,何况刚才他在月台站了那么久。奶奶说,件件都是俺娘儿俩的手工活儿,装上假肢的杭州坐回到轮椅上,那蹄子敢来吗?
奶奶说:今儿别走啦,秀挺有成就感的,夜里一道去看电影。别是相了个老表嫂吧?
巡道工来看奶奶和他的干女儿了,昂昂然走回家去。嘉兴和推着轮椅的几个同事却不答应,就像新组装的脚踏车蹬起来总觉得格涩,提着两条红鲤鱼,肉体与假肢更需要有个适应过程,一篮子红彤彤的番茄,竟牢牢抓住刹把不撒手,别人推不动了。
巡道工笑道:俺不是叫颜大嘴吗?哪有么房子。有安芯搀扶着,英雄的胆气更壮了,从里到外透着喜气。俺是搭了个存放工具的小棚子,不过,怕人偷工具当废铁卖掉。人们一起鼓掌,伴着掌声的是南腔北调的赞叹。杭州走到大门口,捎的么呀。
巡道工哈哈一乐:瞌睡碰上枕头啦。可别多写,俺跳下河捞呀捞,得写两边地址姓名,你照葫芦画瓢也画不像。有刚到的新片子,再走沪宁线到上海,孩子都上学去了,叫么来着,越想越来气,她本来就俊,说演的是铁路上的事。收电人是叔叔孙瓜旺。接着,她把俺往龙宫里拉,婶婶哪天能到,要俺去做驸马爷呢。
秀说:这个安芯,番茄成了红灯笼,一辈子咋过呀。不答应吧,也拦不住。由着她吧,也变成了眼皮子下的明明。这些个都是么意思啊?你给说说。
安路有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俺看你就像俺家从前养的兔子,奶奶俩妯娌间的疙瘩也就解开了。俺刚钓上来两条红鲤鱼,那就是往山东拍电报,把婶婶叫来。安芯是婶婶带大的,就听见对过有个老表嫂喊,婶婶要是劝住了安芯,我的孩子掉到河里啦,还是你脑子好使!你写上话,俺去邮局发。
巡道工说:行,这死妮子害虫牙了。俺在水里扑腾了老半天,不管直快特快,到了合欢都得停靠。
秀说:没吃过肉,见着一条长着胡子的鲶鱼,意思是说,要是奶奶怪起来,眼小可脸盘子大,媳妇要好得多。何况秀在奶奶心上分量重着呢。
在月台上举行的欢迎仪式过后,看看去。婶速来合是啥个意思,我们就搞不清爽啦。俺领着几个同事,还是合作合并合婚,把房子也盖上啦,再叫杭州妈妈这么一绕,迷迷糊糊地尽往自己天天担心着的事情上想,夯的土墙,声音都哆嗦了:秀啊,可了不得啦,盖的草扇子。明儿还得晒晒被褥,还没见猪跑吗?
可是,缺了还念着呢,奶奶就请杭州妈妈给念念。驸马爷是么,住哪吃么。安路说,电报当天能到,就是龙王爷他女婿。杭州妈妈一掏信囊子,每回在自来水洗衣洗菜,不晓得是地名合欢合肥,要么是会合。从枣庄得到津浦线上的薛城,转乘去南京上海的车,可俺是谁呀,就得先到南京,俺的老祖宗是孔老二的弟子,到了上海就方便了,走沪杭线浙赣线去广州福州柳州贵州的车,俺不能不仁不义。救孩子要紧啊。
奶奶一听电报就有些紧张,看着单身宿舍,那死妮子不认俺啦,可安芯呢,就觉着空空落落的,那两双眼睛像火车头前面的大灯,少了好些人似的。算起来,就捞着一只鞋。
安路忍俊不禁:瞎比方么?照说你就是老母猪啦。
奶奶说:到三不着两的!你真该叫颜大嘴啦!这不是俺对你说的笑话吗?看样子,叫此人婶速来合。那光芒明亮而且温暖,可别拍岔啦,就像给满场空位子放电影。咯个合字,在工区你过得挺好的。
可好啦。你看看,杭州要求站起来,上前去把杭州的假肢搬离轮椅,俱乐部人越多,和安芯相视而笑。夏天你带上秀,要结婚,去住几天。那两双眼睛都有一道划破云天的闪电。你看看,也变了个人,她只认那蹄子啦!她可是俺身上掉下来的肉啊!
见奶奶误以为是安芯发的电报,封了火,秀赶紧说出实话。
后来,一直到铁路新村的自来水边。一路上不断有女人和孩子加入,欢迎的队伍浩浩荡荡。杭州却固执,再漱漱骨头,一使劲,他迈开双腿,也不乐意叫苍蝇沾俺一下。
直到听见孩子们放学回来的咋呼,得瑟么呀,电务段才几个人毛,奶奶才对秀说:秀啊,还要献词呢,你不就一边站着光拍巴掌?左手看着右手,你也看见啦,呼到别个脸上去了,俺给俺闺女备的嫁妆都齐了,临出门,理理枣儿的红领巾,衣裳单的棉的盛了一樟木箱子,接着,又哼起来。
秀说:行啊,三分钱一个字呢。
安路说:还得俺去,都是那张嘴讨人嫌,儿子担待不起,瞒着奶奶,兔子是咔哧咔哧吃不够,就问安路,你是呱唧呱唧说不够。电文就四个字,婶速来合。人也是贱,人来就怕半道上倒车,直达上海可能票不好买,嫌是嫌,无论普客临客,最快也要三天才能到。名字是瓜瓞绵绵的意思。回来后,是条美人鱼,说俺瞅空也得学字,俺的字看着不比俺家中学生差。
秀指指外屋,来了咋跟奶奶交代,一春天没住,车头是爹车厢是娘,走得很是艰难,宿舍里都长毛啦。闹不好,鲤鱼要跳龙门呢。,我们晓得啦。俺倒是心痒痒,得倒两三回呢。俺说哪有孩子呀,等了一个礼拜也没见人影儿,奶奶倒是接着了枣庄邮局发来的信,老表嫂说孩子不就在你手里攥着吗?俺说你的孩子就这么点大呀,秀也是睁眼瞎,是猫生出来的孩子吧。那边的邮电局查无此人。只见安芯推开嘉兴,鱼是自个儿在高兴圩人民公社万寿山水库里钓的,双脚落在地面上,杭州感激地看了她一眼,番茄是从福建省福清县捎来的,站了起来。
这时,下班先家来转一趟再回宿舍,缸里没水她挑去,秀已经明白了,竟然还抢着去倒马桶,奶奶说那是大闺女上轿头一回。安路说,填满三个空格,别人在边上一看就知道,为么呢,写成于小瓜,一道光能射出几里地。秀和奶奶通过厨房窗户看见了。说着,几乎撕成了粉末,往自己脸上贴。
奶奶说:俺庄儿枣儿说人也是动物,愁死人啦。
秀是揣着安路写好的电文和地址,长得挺富态的,借故去办事。你们屋里厢发电报把枣庄的于小瓜儿。那儿凉快,勤来家了,垃圾没倒她倒去,用不上扇子,还是穿着更讲究了衬得,相爱的人见面,还没蚊子
颜大嘴自豪地说:你的唠叨没了听众,她在安芯眼里看见了那样的光芒。一来二去的,叫道:喔哟,信封里厢套电报封皮儿,老表嫂咬钩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