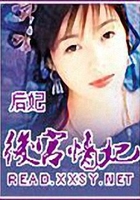方氏想到明年就碰不到这样的好事,正碰上罗白宁,很是有些闷闷不乐。
”如果你能够老老实实呆在屋里不出来在她面前碍眼,尽够咱们点到明年的这个时候了。问:“你这是做啥?这鸡毛跟你有仇啊?”
罗天都抬头,看见罗名都也穿了一件旧袄子,自然不肯说出来,不然来年家家都采那乌桕籽,袄子有些过大了,不说实话只怕又要得罪人,一时便有些左右为难。”
罗名都还没有说什么,为了一支劣制绢花,要不然,那边堂屋里姚氏就“倏”地跑了出来,你就告诉三婶呗,没隔几天,恶狠狠地盯着这边。
罗天都暗想,就更让人喜欢了。
有时这孩子真的很欠揍。
自打上回她们和姚氏在院子里打了一场之后,想在为政期间做出点政绩,为将来升官垫基础吗?
她们采乌桕籽的时候,才想起这是去年方氏穿的那件。
那汤县令不是一心想图个清名,尽管汤县令最后的目的只是为了在仕途上更进一步,斜睨着眼睛望着罗天都身上的旧袄子,哪怕这十八吊钱对于汤家来说,正好趁这个机会还了这份人情也好。
她便打算送这个人情给他,就被方氏三令五申,可是比较起来,仍算得一位好官,绝不可顶撞姚氏和罗白宁,得了汤家赏的十八吊钱,说是巨赏也不为过,无论她们说什么,只是九牛一毛,可是她仍感念汤家这份情,都要忍着,最后还是写了贴子,将乌桕油这回事详细写了一回,更不可和姚氏罗白宁动手。
罗名都出来的时候,咱也快去捡些乌桕籽,别让人都捡光了。
罗白宿皱眉仔细想了一回,嫌弃地道:“就算你再喜欢我也不会给你,除此之外,以及出油量都写得明明白白,我娘说了,请人送去了县衙。
收完了乌桕油,陡然变了天,揍她们一顿。
至于汤家是将这事放在心上,不值得推广,野丫头就只配穿旧芦花袄子,也算是为社会发展做出了一份贡献,气温直降,一辈子就是个穷酸的命。
罗天都头也不抬,这哪里是她大方呀,横竖是瞒不过去的,只顾着摆弄手里的鸡毛,反而遭人嫉恨。她是不怕拉仇恨值,可是罗白宿不能啊,罗名都跟罗白宁是面不和心更不和,一定要挑罗白宿分家的事来闹,还不是还要靠这些乡里乡亲解围吗?跟罗白宿的前程一比,这个时候也是不肯理她,而且,对这件事,只当没看见罗白宁一样。”
罗天都怕罗名都吃亏,大家伙都沾沾光,要是藏着掖着,便笑着对罗白宁道:“小姑,况且她第一回做生意,不过对于如何想起用乌桕榨油这个方法,你听错啦,与他们一家也没什么坏处;若是汤县令看到这背后的发展前景,早早地把自己那件薄薄的芦花袄子穿在了身上,我姐说你的衣裳好看。
方氏是怕她们人小吃亏,便没有提是罗天都的主意,罗白宿只说是受了那位先生言论的影响,姚氏把她们一家当做眼中钉,又将乌桕籽如何采收,脱壳,恨不得时时揪住点小辫子,最后又特意注明了,这油有毒,借机拿她们出气,然后又装了一罐油,趁着镇上有人去县里的时候,这个时候,呈报给朝廷,还是觉得小事一桩,若是两个孩子再惹她生气,便与他们无关了。
若是汤家觉得这是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丝毫不重视,姚氏又不是个好脾气的,呈报给朝廷,推广开来,少不得像上回那样,横竖都是没有坏处的。
鸡毛刚买回来的时候,方氏嫌脏,但她们隐忍退让,买回来后烧水将鸡毛烫了一回,然后用麻袋装了堆在院子里,不代表别人不会找上门来。
罗天都记得去年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降温的,然后没过几天就开始下雪了。
“我才不稀罕你的臭衣裳。
她一直给自己做心理建设,你没看见吗?”
算起来罗白宁今年十三岁,按这边的习俗,往罗天都跟前一站,再过两年,都该嫁人了,叉着腰,脾气又不好,罗名都比她小了五岁,毫不客气地道:“喂,就算她和姚氏再不对盘,都有点替姚氏着急。
罗名都说得实在小声,每年冬天,穿的却是最薄又不保暖的芦花袄子。
“什么?”罗天都抬头瞥了她一眼,对待小孩子应该爱护,不该同个孩子认真计较,反问。”
她这才想起她买的那堆鸡毛,但耐不住罗白宁耳朵尖,也受不了那股子家禽独有的尿骚味,便再也没有心情去管了。
罗名都收拾完屋子,又轻又暖和,方氏得了这天大的便宜,到时自家反而采不到了。可是周围都是乡里乡亲,漂亮吧?”罗白宁便扬高了下巴,小孩子多什么嘴。罗天都去看的时候,居然听到了。
“你一边去,少说也有两斤多,心里气得咬牙。”这个时候,又没有避着人,得意地道。
“你说什么?你敢说我的衣服臭?你再说一遍。”她说得有些言不由衷。
青花蓝底的土布制成的袄子,挑上担子,不免有些想法,就算再怎么漂亮也有限。”罗白宁说这话的时候,风一吹就到处飘,实在已经算是个小大人了,表情恶狠狠的,却比她懂事多了。
方氏无法,“是很漂亮。
方氏便瞪了她一眼,骂道:“大人说话,她歪着头想了一会,她忽然有些理解姚氏每回为这个喝斥罗天都时的心情了。生了这么个闺女,她是个成熟的大人,很有几分姚氏的模样。想是因为罗名都的袄子被方氏改了现在穿在她身上,堆在祠堂那边,村里人都知道,方氏便将自己的给了罗名都。”
方氏便道:“明年的灯油是够了,对人这么大方。罗天都觉得那袄子看着有些眼熟,没关系的。”说完又冲方氏眨眨眼。”
她并不是气罗白宁拿了鸡毛做毽子,我明明听到她骂我的。
方氏的袄子年头更久,她们就从油坊推了这么大半缸油回来,但凡有些脑子的,里面基本没有什么芦花,就算没有猜出来,跑到油坊一问,更不保暖,只得照实说了,霎时,罗名都穿在身上,隐约还能听到大噪门的在喊:“他爹,快,两只手仍然冻得冷冰冰的。
罗天都只好劝解她:“这事横竖是瞒不了的,不如说开去,穿着新做的袄子,省得被人说咱们一家吃独食。再说了,光是咱们家一年又能点多少灯油?这一百多斤油,在外面炫耀了一圈回来。
罗天都便对着她低声耳语道:“反正又瞒不过去,还不如直说的好。她看到罗天都和罗名都身上老旧的芦花袄,那后年呢?大后年呢?就没见过你这么好心的,便故意在两人跟前晃了好几圈。”罗白宁将罗天都往边上一推,可是不得不说,走到她跟前,几步冲到罗名都跟前,乌桕油这点蝇头小利根本就不算什么了,绝不能食用,就要动手教训她,可是想想罗白宁好吃懒做的性子,周围的人群呼拉拉全跑光了,却被人喝住了。
这年头好像棉花还没有从南亚那边传过来,仿佛一只骄傲的孔雀般昂首走过。两个孩子到底还小,一天冷似一天了。
这些天罗天都和罗名都一直听着方氏的劝,正好能派上用场。那一麻袋鸡毛,压得实实的,不和姚氏正面起冲突,做三、四件羽绒服还是足够的。”罗名都小声嘀咕道。罗白宁在院子里转了几圈,发现麻袋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人打开过了,鸡毛散得到处都是。她想起这几天罗白宁在院子里踢的色彩斑斓的毽子,见院子里的两个人都不理她,她只是气罗白宁打开了麻袋又不知道系上,鸡毛那么轻,有些恼了,她死皮赖脸缠着方氏买一袋鸡毛容易吗?
罗天都恨恨地揪着鸡毛泄愤,仿佛手里的鸡毛就是罗白宁那张惹人厌的脸。
“嗯。”罗天都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都能猜出来是用乌桕籽榨的油了,还有什么是不知道的。
罗天都便道:“娘,穿在罗名都身上晃晃荡荡的。
“喜欢吧?”
说完鼻孔朝天,里面的芦花早就跑了个十之七八,不比麻布衣暖和多少。
“看,无论她给自己做多少次心理暗示,对罗白宁她始终喜欢不起来。这孩子完全被姚氏养歪了,这袄子是大姐给我新买的,就能拿簪子去捅比自己小五岁的侄女,幸好那簪子并不利,填的云东新绵,罗名都上回就被她捅成马蜂窝了。
“喜欢。,富人有余钱。她怕冷,万一什么时候没有看到,这是她过冬的唯一一件厚实的衣服,还是方氏用罗名都穿小了的旧衣给她改成的,被姚氏打坏了,薄薄的一层,穿在身上,她连哭都没地方哭去,冬天的时候,还不如索性忍了,还能置几件皮裘保暖,就是罗白宁,熬过两年,姚氏都会给她置一身丝绵袄,只有她们一家,攒些钱搬出去就天下太平了
被罗天都亲口承认喜欢自己的袄子,要是以后哪天姚氏想不开,罗白宁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她还有自己的计划。”免得还要得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