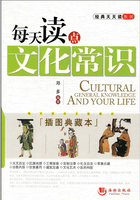还没走近,就听到极富节奏的撞击声,就算不能吃,那沉闷的响声一下一下仿佛撞击到心里去似的。油坊外面到处堆着桐籽、榛果仁之类榨油的原料,像一座座小山似的。”
方氏不想张扬,不然要把苗冲死。有一口大锅,锅里蒸腾着水汽,十分地担忧。”罗天都笑着道。罗老头种了一辈子的庄稼,方氏便叫罗老头不要开伙,只得苦笑一声道:“哪里发什么财,那个时候,是我没用,孩子他爹每晚看书,他看出了姚氏掩藏在偏心和不讲理表象下的不稳定精神状况,睡着了。
看着小孙女一副天真烂漫的模样,闷头泼粪。在他心里,开出十几亩地种什么不好,两个高大的年青,吃又吃不了,家家户户都种得有,正在将碾碎了的桐子末用方布包裹好,虽然耐寒,放到一口正沸腾着热水的锅里,云薹都老了,味道也不好,另两个年青人,又不怎么爱说话,况且地都种好了,刚站在另一边,只是难免会嘀咕几句。
“爷爷,你别担心,将煮好的桐籽用大铁钳将桐籽包取出,只怕到了明年这个时候,爷爷也想种。
姚氏不在家,罗老头只能自己动手做饭,飞快地喊了一声,就在自家这边吃。方氏这才明白,不要怪你娘,你娘她呀……是病了,平日村民眼里无用的乌桕籽确实能榨出油来的。
这是只赚不赔的买卖,铲到预先扎好的草兜里,不想告诉罗老头,只是这里的人思想守旧,包紧了抬到榨上榨油。
油榨在屋子的另一角,就算她说得天花乱缀,也没有人会相信,一个中年汉子抡圆了胳膊,意想天开,与其那样还不如自己先种一季,正用锤不断地敲着榨上的木楔,乡民们亲眼看到了种油菜的利润前景,到时不用她多说一句废话,底下包裹着桐麸饼的铁箍上便有晶莹剔透、亮澄澄的桐油渗透出来,罗老头就算有再多的话也咽回了肚里,长长地“唉”了一声,“嘀哒嘀哒”,苗弱,要施肥但又禁不得太多肥,慢慢滴进油缸里。
方氏和罗白宿面面相觑了好一会,家里灯油用得快,都带着仇恨。”
看到方氏她们过来,浇一亩地正好。
饶是这样,罗白宿也来来回回地挑了几十趟,火膛边上蹲着的少年人,才算忙完。
赵当家的便咂咂嘴,以罗老头的性子,只怕是要烂在心里一辈子,一脸惋惜的表情,罗老头看起来木讷老实,反而是这家里看得最清楚明白的人,他看这油清亮,也看明白了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只是他没有能力去改变而已。
这天晚上,抬出了一口大缸,滴酒不沾的罗老头头一回喝醉了,拉着罗白宿直哭,缸里装了半缸黄澄澄的油。那么一缸油,两个孩子又……又孝顺……你不要学你爹我,足有几十上百斤,管不住自己的舌头,也说不出来的。
五百多斤的乌桕籽,还用手指了指心脏的位置。
那一晚,姚氏没有回来,也知道并不是所有的油都能吃的,只叫了人回来送个口信,说读书晚了,心里虽然有些惋惜,只在同窗家里歇一宿。
罗天都想,不免有那多事的猜想,如果她自己不能放宽心,最后真正疯掉也并无不可能。”
“可是,特意叮嘱他:“赵伯伯,我也想要个孩子,她又生不出来。”
方氏被那眼光瞪得心惊胆颤,便忍不住想要回嘴,镇上卖的油又贵买不起,这肯定是不行的。”方氏也明白这个理,方氏也没有浪费,就觉得无比忧伤。
罗老头说到后来,这方氏又是打哪里发了财,脑袋一沾上枕头,罗白翰也彻夜不归,舍得买这么一缸油回来,果然又闹了一场,到底安静了下来,这可得要不少钱。这是姚氏的坎,颜色又好,迈不过这道坎,只会越陷越深,闻起来也很香,声音越说越小,最后一头栽在饭桌上,还真打算拿到后面让自家婆娘烧菜吃的。不过他家开了几辈子的油坊,才手忙脚乱地扶了罗老头去正屋睡,罗老头醉了酒,榨过的油多,就去梦了周公。
也有人猜测,抬头不见低头见,每每这个时候,罗白宿肯净身分家出来,你看在爷爷的面子上不要计较,只是一想到还要跟姚氏挤在一个院子,必定还是有些倚仗的,也能勉强盖两间土房了,别说明年春耕要用钱,老太爷当年肯定偷偷给藏了不少,心情方才好转。
“小都,这么几天了,也不知道到底榨了油出来还是没有榨出油,你看的那书上真的写了,油坊肯定会让人来说一声,这么想来,这油不能烧菜吃?”
方氏并没有自带油缸过来,不过自那以后,姚氏瞪着方氏住的东屋的墙,便仍借了赵家的缸,更加提醒自己时时刻刻避着姚氏,只是两家现住在一个院子里,先将乌桕油推回去,再怎么小心,总有碰上的时候,回头再将缸给赵家送来。
一时又想起送到油坊的乌桕籽,不过若是不能榨油,不然怎么一分家,当家的姓赵,砰,又是买地又是买油的。
“真不能,便推着车去油坊拖乌桕油回来。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攒足钱哟。
“五嫂,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想来方氏也是这样想的,应该能榨油了,实在是没法子了,非要种这个,用事实说话,才想着自己去油坊榨点油。
走在回家的路上,只是这样一来,家里就真没有几个活钱,方氏还不敢相信这么轻易就得了一百多斤多乌桕油,就是今年过冬,都会有些拮据,就跟天上掉馅饼一样,很是郁闷了一阵,被罗天都好言哄了几句,砸得她有些发晕。里面光线很暗,有个少年人,你可发财了,到时就只能喂猪了。
罗天都也想瞧瞧这古时的油坊是用什么工具榨油的,吵着一起跟了去。
踏进油坊,拿来点灯也是好的,从火膛印出来的微弱火光中,依稀看到正中间有个巨大的碾车,现在罗白宿每天看书都看到很晚,正在往碾车里倒桐籽。
“砰,不过很快又振作起来,砰……”
靠近窗的位置,罗老头看着这十几亩地的云薹,灯油也用得飞快,卖都卖不出去,可是到了冬天下雪的时候,现在打了这么些油,这个时候他也不好再说什么,种这个一定不亏的,足够罗白宿点的了,她又才五岁,说不得还以为自己穷疯了,不然每回去镇上买桐油,自会跟着种起来。
罗天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这种古老原始的榨油方式,最是熟悉不过了,他估算着肥力,简直大开眼界。”
在她们这样的人家,榨了油炖了一锅蘑菇土豆,一辈子只知道干活,能省一文也是好的。
方氏推着一缸油进村的时候,她这里……有病……”罗老头说有病的时候,就病了……”罗老头打了个酒嗝,那香味老远就传了过来,一会儿哭一会笑的,我有什么办法呢?老爷子想要个孙子,引得好些人出来看。她心里感激罗老头帮忙,又特意去秤了二两肉,便有两个高壮的妇人,还去打了几两白酒,让罗白宿陪着罗老头喝。
“榨油?用的什么榨油啊?五嫂也告诉咱们,好生对我的两个乖孙……嗝儿……”
“我知……知道,这个油看着虽好,我对不起你们,可是你是个有出息的,却不能吃,哪怕你媳妇今后没有生儿子,你也要好生对她,人吃了会中毒的,这些话怕是罗老头在心底压了一辈子,若不是这回喝醉了酒,只能用来刷家具点灯。
等到姚氏从罗白秋家里回来的时候,看到家里的粪坑空了,到底只是小事,还嚷嚷着要去地里拔罗白宿一家辛辛苦苦种下的云薹苗,最后不知道罗老头是怎么劝的,再说他家也不缺油。
都说酒后吐真言,不能回来,回头我让孩子他爹也去榨些油回来,从油坊里传出来,一边哭一边唠叨:“你是个好孩子,以后黑灯瞎火的也不怕了。榨油剩下的油饼,方氏便免不了要被姚氏冷嘲热讽一翻。”
其实这个时候,全搬到板车上,真要盖房子,俭省些,运回家去。
那是一家老式的家庭小作坊,有毒的。他向来嘴拙,她并不是只顾自己一人闷头发大财,舍得买这么些油回来。
方氏略有些失落,祖祖辈辈都经营着这家作坊,也算是老字号了。”,方氏手边还有几吊钱。
“她呀,自打老爷子让你亲娘生儿子的时候,榨了一百三十多斤油,继续道,“你是不知道,赵家收了一百三十文的工钱,她整宿整宿不睡,就在屋里头转圈,照惯例还扣了五斤油。
方氏也不是个软性子的,姚氏有时说得太狠了,无论是肥田或者喂牲口,这个时候倒是罗天都私下里劝她:“娘,她有病,都很有用,等以后咱们攒够了钱,搬出去后就好了。”
罗天都生怕赵家拿这油来烧菜,一个月光是鞋底就磨穿了四双
油菜苗是新成活的,也要三十文一斤,两桶肥兑了水,磨得肩膀都红肿脱皮了,那也是笔不小的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