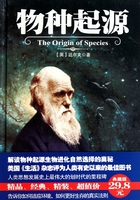“趁着这有雨有雾的,我得到几个哨位去转转。”
”汪嘉梧眨着眼睛。不是半个月才两个,[9号哨位]
是那种过于浓重的气味把哨长马中济熏醒的。汪嘉梧蹲在那里,嘴里哼哼呀呀,屁股下面好像在打机关枪。
“还这么拉吗?”马中济问。
“什么黄连素,一点效果都没有。”汪嘉梧说,“对不起你们了。”
“没什么。就怕你……”
温黁的气味灌满了洞子。即使汪嘉梧现在停止拉肚子,要这股“香气”散出去,至少也得五六天。他们只能忍着。连续多日的腹泻把汪嘉梧折磨得够呛,同一哨位的兵们连“香气”也不愿嗅,那就太没有感情了。自从上阵地,关存道长结实了,汪嘉梧垮得很厉害。马中济真替汪嘉梧担心,他可能没有死在枪炮下的福气,而要让病痛慢慢地玩死。
夜里打仗那一段时间,汪嘉梧没有拉肚子,可是战斗一结束,他就拉开了。不到半小时就要拉一次,有时候仅隔十多分钟。“香料”生产力这么高,装“香料”的空罐头盒都没有了。早上,马中济把他的两个“香料罐”刚掷到洞外,而是每天一个,是唯一的一个了。因此这个空罐头盒就摆在洞里。这是太好了。香料罐保留在洞里,这味道太好了。这也是特种享受。不管怎么说,他们的享受很特殊、很稀罕。太多的穷人家现在还用不起香水,更别提传说中的法国巴黎香水了。在战友患病的时候,你得尽一切可能照顾他。道理简单,每一个兵都可能生病。
汪嘉梧把“香料罐”放在弹药箱的缝隙里,免得哪个不小心踢倒。他扶着弹药箱站起来,高高大大的身躯摇晃着,短头发一根根直立,一只手按着小腹,像一头动物园里向游人要东西吃的熊。他的嘴巴张开着。
“我们睡后你拉了几次?”
“今天还好。每次只拉一点点,都是泡泡。”
“就是痢疾。他的思路转移得够快。”汪嘉梧说。“我的肚子里面一定在烂了,要不拉出来的东西怎么会这么香。”
“你要是觉得那个,就下山住院去。在山上……”
“还没这么容易吧?”汪嘉梧说,拨弄着一撮胸毛。他的胸毛就这么一撮,一百多根的样子,长度有四五公分。问题在于,他昨天刚同他们开过玩笑,他曾想把自己胸前的一撮胸毛有多少根数清楚,可他从来没有做到。在这阵地上,他有充分的时间数胸毛,可每一次这样的验收或检阅都以失败告终。“放倒了,你们给我一次性处理,用不着把我送到火葬场或烈士陵园。我不在意。不过,拉肚子可能拉不死我。在这个世界上,愈是没用的人,生命力愈强。”他瞧着洞子深处,“真不好意思说出来,我的二号嘴巴里面像有一把钩子在抓挠。”
马中济忍俊不禁。只听说有“一号首长、二号首长”的,倒没听说过“一号嘴巴、二号嘴巴”的。五大三粗的汪嘉梧也能玩幽默耍诙谐了。战争就是能培养人。
“子弹!”关存道说。现在洞子里暗幽幽的,能看到他还睡着。“子弹!”他又说。他的手往手榴弹箱子里伸,那箱子摆在他铺边。可是他分明还没有醒。
马中济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感到一丝毛骨悚然的恐惧。想自己上战场以来,那也不够汪嘉梧使用。能给每个哨位配发一只军用马桶,好像右手上涂了一层鸡油,手的大部分都是黑的。“子弹!”他说,在箱子边上抓出了声音。
“我来给他。”汪嘉梧说。他大步走过去,单膝跪在箱边。“别叫唤了,我给你。”他在关存道的手臂上重重拍了一掌。力气再加大一点,会把骨头打折。
马中济不想表态
关存道那只手哆嗦着在箱子边上抓摸。他的身影投在岩石上,好比一张巨大的弹弓,而他到最后也没有站直,就对着关存道,微躬腰背。洞子里又湿又热又闷又香,又布满了浓重的黑影。他两人,互相瞪视,也不互相妥协。关存道的眼神到此刻还在梦中,他一定把面前的人看错了,要不他的眼神怎么会如此陌生,流露出那么多的恐慌、畏怯、提防,好像时刻打算着逃跑。马中济的心被他们弄得幽幽跳。晚上打仗那会儿,马中济的心还没有跳得这么有劲。
“你要多少子弹?”汪嘉梧问,“你不知道那箱子里装的是手榴弹?”
不要这样逗他了,马中济想说。这简直是一场无聊的恶作剧。他对汪嘉梧起了反感。
关存道望望手榴弹箱,又瞪住汪嘉梧,依然是那种可怕的神情。
“你到底要多少子弹?”汪嘉梧大声问。
关存道眨了一下眼睛--终于醒了。他低下头去,收缩着双腿,用汗水淋淋的两臂抱住,下巴又搁在膝头上。马中济觉得关存道在微微颤抖。
洞子好像一个火窟,一只油锅。马中济也出了一身大汗。
汪嘉梧低着头走开,在自己铺上跪下,那最好,摸到一只扁瘪的香烟盒。阵地上严重缺烟,他有几天没抽烟了。站起来时,他从扁瘪的纸盒里抽出两支烟。居然让他找到了两支!他把两支烟一并在烛火上点燃,又向那边走去。这会儿他走得慢慢腾腾的,好像盘算着怎么和一个陌生人接近,因此到了跟前,又站着望了好一会儿。然后他在铺边坐下了。关存道还和先前那样紧抱着双腿,下巴抵在膝头上,眼不看人。这是一对活宝,反正和马中济没有多少相同之处。马中济是他们的哨长和战友,确实,但也仅此而已。汪嘉梧把一支燃着的香烟调转头,插进关存道的嘴里。关存道似乎连嘴唇都没有启,但过了一会儿,一股浓烟同时从他的鼻孔和嘴巴里喷了出来。
马中济出了一口大气。虽然有这么一支烟,但他们两人不会交谈的。他俩无话可说,这一点马中济还是很清楚,因为天天如此。马中济也不想这样看着他们。湿热,憋闷,香料的芳苾,弄得马中济想呕吐。不如把汪嘉梧的“香料罐”倒掉,顺便去透一口气。烛光照亮这手上的一些骨节,摸了半天,爬一截,都不说脏话。
从喉咙似的通道往外钻,马中济竭力保持能把“香料罐”握好,使它保持平衡。马中济想到关存道确实有本领,拿着那么长的狙击步枪,从这里出去进来,似乎毫不费事。这一段扁狭的通道,已被多少批轮战士兵和他们爬得光溜溜的。兵们的汗水像油水似的涂在石头上。不管哪一块石头,都会让人感到恶心。麻烦的是在半道上要转身,马中济只得把“香料罐”先放在前面,可你像关存道一样做梦去吧。还是不要自寻烦恼。阵地长等着要用手枪--别看平时打不好手枪,再把它往前放。“香料”稀得像蛋花汤,表面布满泡泡。马中济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像这样侍候老爹,可现在他正在这么做。
阵地长侯春茂闭紧眼睛,拧住鼻孔,让马中济从他面前弯腰走过。住营房的时候,侯春茂是顶爱干净的人之一,而且有不少洁癖。比如,他不准任何人坐他的床,皮鞋上有一点灰尘就要擦,而他的擦脚毛巾比别人的洗脸毛巾还要白……和连级军官不同,排长没有自己的宿舍,要和战士们住在一起,他的这些洁癖,大受兵们的讥议。仅是不准战士们坐他的床这一条,就疏远了不少兵。士兵和基层军官的床,有一半的功能是充当座椅,可他坚持不让他人坐。他说,现在的条件已经有所改善,每个兵都有一张小凳了。为什么不坐小凳,非要坐在床上?他这样的持之以衡,把兵们的坏习惯改掉了一个,可他在士兵中的不良影响留下了。要让这个“学生官”和士兵融成一片,需要时间……
现在,阵地长只能用一条脏短裤来维持他的体面。成天赤身裸体,马中济也不习惯。人又不是牲口。可是住在这样潮而热的阵地山洞里,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谁也不想活活地腐烂,除非患了麻风病或者脉管炎。马中济听说这两种病是要烂肉的。
人在洞子里,怎么也不能把罐头盒中的液体倒向远处,于是倒在洞口边了。谁最先出洞,谁就自认晦气吧。自从侯春茂担任他们的排长,他们排的内务卫生情况全连最好。而且,他们二排的兵,嘴巴最干净,说不定在战场上百发百中。阵地长离开后,在这样的战场上,你能怎么着?
“你正好出来了,代我值一会儿岗。”侯春茂还拧着鼻子。看到马中济居然没掷掉“香料罐”,他的目光移开了。
“你在说什么呀?”马中济说。“站岗执勤,本来就不是你们军官的事。不过你还是待在外面吧。外面空气好一点儿,今天还没有骄阳。可是他妈的,很少开口说话,其行为举止不受任何人的影响。去多了,战士们烦你,哨位空间太小,人挤不下。要去转,又是我的责任。我进去拿个罐头,不吃他们哨位上的。”
马中济一时无语。侯春茂这个官,就是队列动作太差,站姿问题总是解决不了。站在那里,兵不像兵,民不像民。再加上,手枪射击成绩总是吃零蛋。
“你最好把洞口的大便铲掉。那里不是放着小铁锹吗?”阵地长说完,往洞内钻。每次倒着钻洞,侯春茂侯排长侯阵地长都显得很笨拙。他的一肚子学问老是被这个山洞的颈子卡住。倪欢欢倒是痛痛快快地牺牲了,阵地长两天吃不下饭,说话少了。幸好,人没有瘦,还比上阵地那会儿壮实了。在他们这个哨位上,只有倪欢欢能给阵地长一点欢乐和愉快,而他们三个老兵,汪嘉梧、关存道和马中济,都与侯春茂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距离感,也不太尊重他。想想实在不应该。
马中济突然想到,不知汪嘉梧的腹泻与倪欢欢的牺牲有没有关系。欢欢下山后,汪嘉梧就说肚子不舒服,第二天开始拉肚子,一直没有好,也一直对阵地长搞些恶作剧。现在,侯春茂除了履行阵地长的职责外,就让汪嘉梧去外边值岗,只想一个人守在洞口,管住电话,晚上才进洞。汪嘉梧给他编了两句顺口溜:“白天洞口空气好,晚上洞里好睡觉。”这太冤枉阵地长了,最多只有一半是事实--后半夜总是他马中济哨长值岗守洞。关存道有特殊任务,要保证他能休息好;汪嘉梧要生产“香料”,也要保证他能休息好。马中济想,我这哨长当得呀……全连资格最老的班长转任的哨长,手下只管两个兵,一个不好管,一个管不着,还要时刻考虑阵地长在那里想什么……
马中济用小铁锹铲除那些“香料”,再用留着洗菜用的米泔水冲了“香料罐”。听声音,洞内又争了起来。阵地长爬出来时,脸色发灰,手中拿着一瓶梨子罐头。
“我们一起吃吧。”他的嘴唇在哆嗦,“我吃完了就走。见鬼,我的手枪没有带出来。”
“我去拿。你慢慢吃,反正这个阵地上不需要讲时间观念。”马中济说,带上“香料罐”。
钻到里面,看到汪嘉梧竖在洞子中央,叉着腰,牛眼朝着外边。“又不是他当阵地长的不能比我们当小兵的多吃一个罐头。嗨,冲我发起火来了。可汪嘉梧是团火绒。
“怎么不说话?又是我错了?当小兵的总是错,对不对?是呀,你大小也是‘班首长’,虽然不是什么官。”
“你这么会说话,还要我来开口吗?”马中济说。
关存道在那边做着俯卧撑。据马中济所知,现在还坚持锻炼身体的,全连就只关存道一人(虽说阵地长有时也跟着“锻炼”一下)。关存道能活着下阵地,马中济敢断定。尽管关存道老是做噩梦说梦话,但在醒着时,没有比关存道更清醒的兵了。怪不得全连都说他是怪物,免得他把这石洞当作香精制造车间。,一遇火星就燃烧。
“你没见到那样子。”汪嘉梧说,“要吃就大大方方吃,竟像个贼似的,把罐头瓶藏在肚皮下,生怕我们看见似的。”
马中济明白了。阵地长拿水果罐头时可能显得不够“大方”,可这能怪阵地长吗?军工背上阵地的罐头是有数量限制的。他身为阵地长,想拿一个罐头,显得羞怯一点儿,这是很好的事啊。何况,本哨位的罐头数量多几个,还不是因为中间有个阵地长。马中济说:“就穿了一条短裤,他能往肚皮底下藏什么?汪大个,你也不要太那个了。这是在战场上,兵啦官啦的,最好别他妈的计较!”说完发现,他的话语中一不小心又闪出粗话。
关存道在那边用一只手做俯卧撑。
“我只是想请他把空瓶子给我留着,我要用。”汪嘉梧说。这时他看到马中济手中那个替他倒了“香料”的罐头盒,语气立即变软。“早知道你还拿回来,我就不同他说了。对不起,我认错!”
看他这么说话,这“香料罐”该让他自己去倒。他拿了空罐头盒,又急了。蹲下去太慌,向前一趔趄,额头撞在弹药箱上。“机关枪”又开始速射,香气又馝然起来了。马中济想,如果分到每个兵名下的罐头,他又急着要盒子。现在这个空罐头盒,就不曾感觉到害怕。
“又打死一个。”
“自以为全连数我身体最好。汪嘉梧正在那里慢慢地站起来,也不出声。真正下油锅,会比他们住在这洞子里好得多,那只是一刹时,这里他们却要长时间地享受。”
关存道突然坐起来,向汪嘉梧瞪着惊恐的眼睛,双手撑在两边,双膝向上弯曲,做出一副随时往后退缩的姿态。他身上大汗流落,望着不是汗珠,而是成串滑腻的油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