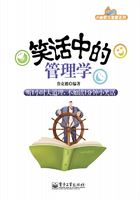[连部]
可是,呵,又来了。她歪着头向他们望望,踏上编织袋,跳进洞里,对他们说:“咕咕咕。”申体心又想起浓雾中的那一团白,后来他们就认识了,关系不错。
“不能再等了。”韩延庆说。
“你还是睡一会儿吧。”申体心说。他到那弹药箱充当的米桶里抓了一把米。“来,到我这里来。过来吧。”
她歪着脑袋朝他望望。这是她想把两个申体心看成一个。在她正眼看他时,她看到有两个申体心。连长躺在那里搔脖颈,搔喉节那个地方。申体心和他的分工很明确,一个管黑夜,一个管白天。现在是白天的两点半,该由申体心来管。韩延庆管黑夜的时候总是弄得申体心睡不着觉,申体心在自己管的白天里尽可能让韩延庆多睡一会儿。管白天和管黑夜有不同的管法,而有的人经常把那管黑夜的手伸到白天当中来。她正眼瞧着申体心。她眼里有两个申体心。“来吧,到我手上来吃。”
“我们失去了一些好机会。”韩延庆说,“像这样待在山洞里,我们这支部队,简直是在虚糜饷糈!”
“说严重了吧?守住这条防线,不就是我们的任务?”申体心说。
“不能让他们闲在那里没事干。兵不可闲,闲兵惹事。”
“是不能让他们闲着。”申体心说。申体心知道,现在闲着的时间太多了,他们,那些哨位上的兵。
韩延庆歪过脸来朝申体心望。她也歪过头来朝申体心望。韩延庆和白母鸡都望着申体心。韩延庆眼里始终只有一个申体心,白母鸡却想把两个申体心看成一个。接着韩延庆转开视线,不再望申体心了;白母鸡又正眼瞧着申体心,好像在两个申体心之间作比较。申体心对她说:“喌、喌,你放心过来好了。”
“咕咕咕。”她说。韩延庆平躺着。小文侧卧着。小苗蜷着。汗水在他们身上流。汗水顺着他们的肋骨流下,渗进他们身下的棉被里。天也怪了,老是不下雨。雨季的天老是不下雨,怪哉怪哉。他们能够把天空打漏雨,对此申体心深信不疑。子弹是能够打漏天空的。既然子弹能打穿人的胸膛,就能打穿天空,能够打死人的子弹也一定能够打死天空,让天空好好哭一场。因此,申体心想,他心里并不反对韩延庆的方案,只是他多一层顾虑。
“他们对你说了什么?”韩延庆望着脸孔上方的洞顶说。暗幽幽的洞顶挂着白亮的汗珠。石头也是怕热的。石头可以有流不完的汗,申体心却没有汗水可流了。因此申体心想,狙击步枪能够打得那么远,一定能够打死天空的。
“没说什么。”申体心说,“他们只是闲着。”
“给他打电话了吗,怎么样?”
“好多了。从电话上听来是这样。”申体心知道连长在问22号哨位上那个廖成先的情况。他有点后悔,不该给廖成先写那封六页纸的长信。如果政治思想工作真有那么大的效果,那就不需要再设军事检察院和军事法院。
她说:“咕咕咕。”
“所以,我们不能再等了。”连长搔着喉咙,“不能再等到了。”
申体心就听她说过多次:“等等再说,等等再说,你要我等到什么时候?”尔后她娓娓动听地埋怨开了。等等等!等来等去等到最后都是白等一场,你以为从晚上等到白天就能等到你想等的,可等完了白天以后等到的仍然是晚上……这些话就像绕口令似的,真难想象她能说得那么快那么流利那么清楚。唉,是啊,白等一场。仍然贯,如之何?她的埋怨曾经是娓娓动听的。我们现在想等的是不是晚上呢?只有晚上他们才能在一起互相埋怨。
可申体心偏偏给廖成先写了那么多。这还是考虑了半个月的结果。半个月的庞杂思想浓缩成那么几页废话。廖成先看了,当然会欲说无言、欲哭无泪了。
“喌、喌、喌!你就放心走过来吧。”申体心对白母鸡说。
她走过来,每走一步,胸脯都要往前伸一伸,缩一缩。她就这样伸伸缩缩地走过来。申体心的心怦怦地跳着。申体心明白她会朝他走来,因为到了这一步他们还得生活在一块地方,哪怕这地方多么糟糕。可他真怕她到自己面前大吼一声:“你这窝囊废!你要我等到什么时候?”她会这么吼。她老是这么吼。能够这么吼几下,她就痛快了。她通过这么吼逼迫他注意她的存在。尽管她占据他的半边脑子了,他只用另半边脑子来想除了她以外的许多事情,可她仍觉得他没有把她放在脑子里,根本没有关心她。
“那封信是你夫人写的?”韩延庆问。
是只美丽的白母鸡。“好像是吧。”申体心说。她在半路上停住了,正眼瞧瞧他,歪头瞧瞧他,再正眼瞧瞧他,两个申体心,合成一个申体心,再分成两个申体心。人类对动物眼中的世界了解得很少很少。“你还可以睡两个小时。”申体心提醒连长。
“我能看看吗?”韩延庆坐起来,用指头刮下手臂上的汗。胸脯上的汗拐了个弯,向腹下流。腰部横着一条汗水河,肚脐眼是个倾斜的小水潭。那黑毛粘在皮肉上,到处是汗。申体心忌妒韩延庆的流汗。流汗说明身体好,“这么多的汗。”韩延庆却说。“信在哪儿?”
“心”歪在左胸腔!在哪儿?
“没有商量的余地?”申体心望望她,拨弄着掌心的米。
“我就不认为非要商量。”韩延庆说。她啄着石头。她的嘴又尖又硬。放在枕下的信让他翻了出来。这个韩延庆。韩延庆的性格是进攻型的,因此他讨厌防御战。申体心总是防御,防这防那,防左防右,结果防不胜防。可不,她的嘴又尖又硬。她还真吃石子。“是尊夫人写的嘛。”申体心把信封放回枕头下,取走信笺。“我说呢,”韩延庆回到自己的铺位,“看夫人的信应该穿上裤子的吧?”他在汗水后面傻乎乎地笑了一下。
白母鸡望望申体心,一伸一缩地走过来。申体心摊开手掌。只有一把米。
“总是这么直呼姓名吗?”申体心感觉到韩延庆在望他,不,可能是凝视着他。“我的妈呀!‘申体心,我看你是官迷心窍了’这样开头?你这夫人,有点儿……有点儿厉害!嗯?”韩延庆又在凝视他。不,不像。韩延庆是在审视他。“我看你是官迷心窍了!你是不想管我们母女两个了……”用不着这样审视人,韩延庆。虽然每一个人都有可被他人审视的地方。
是只美丽的白母鸡。红的鸡冠,白的鸡毛,红的脚爪。申体心还从未见过有这么白的母鸡。白鸡毛中没有一根杂毛。当然,这之前用不着写信,天天可以在一起互相埋怨,等到需要写信的时候,也需要“直呼姓名”了。这也是很奇怪的事。打仗开始不久她就在这里了。这之后死了不少人,她却活着,没有被人杀掉。可仔细想来不奇怪,一点儿也不奇怪。全身的羽毛竟是如此的粹白。申体心记得他母亲养过一只母鸡,白毛当中有不少黑毛也叫白母鸡,基本上天天下蛋,母亲视她如宝贝。白母鸡把申体心的掌心啄得痒痒的。她的嘴又尖又硬。怎么没人把她杀死呢?她的肉可以吃却不杀掉她。不过,看她的毛那么白,两边的军人就不会杀她了。她的嘴又尖又硬,把他的掌心啄得痒痒的。
韩延庆望望申体心的脸,望望他的手掌,又望望他的脸。申体心能感觉到她的眼光,就像他能看到两个电话兵梦中怎么回家,听到她在厨房里、阳台上、在一个人坐卧的大床上、在她的父母兄妹和她的女朋友男朋友中间埋怨他。没什么大不了,白母鸡的肉可以吃但拿枪的人都不杀她,因此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她说的‘极端行动’是什么?”韩延庆问。他的个子够高的。那双眼睛在天空中俯视着申体心。“她说,她要对你采取‘极端行动’,你没有注意到这个字眼?”
确实是只美丽的白母鸡。申体心觉得膝头蹲酸了,就站起来,掌心相对着抹了抹。“我并不反对你的方案。我以前的意见只是等一等。”申体心说,“工事都已经修好,现在可以了。我知道,我让你等的时间长了一点儿。不管什么措施,现在都是最好的时候。”
韩延庆终于笑了笑。看见他能有笑容真好。申体心多少有点责备自己。狙击步枪的使用权在连里,不需要报批。上阵地第五天,韩延庆就想使用狙击步枪了。申体心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拖延和劝阻。他觉得,他有责任也有能力阻止这位年轻连长的冲动。怎么的也该让战士们有一个适应阵地生活的时间,先消除紧张心理,排除一些历史刻录在他们心头的杂念,专注于目前的情境。我们不也是一样的吗?每一场战争和战斗都是特殊的。面前这一场战争,不需要我们带着士兵一上阵地就向敌军发起猛烈的进攻。这支狙击步枪是不能随便使用的。只要它一开枪,就会有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会怎样,申体心现在未能预料。不过一定有结果,这是可以肯定的。四十多天过去了,全连没有伤亡,很难得。可从今天起,事情会怎样?
“就这么定了?”韩延庆再问。
“就这么定了吧。”申体心说。
韩延庆快速地把信笺装进信封,回放在指导员的枕头下。真想去打电话,突然站住了。“你老兄怎么不流汗?”韩延庆问。
“没做亏心事吧?”申体心说。
韩延庆笑了笑。“回答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