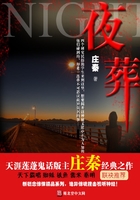匪叔的两个哥哥,也就是我的大伯和二伯,尽管在父母去逝时,年纪都不大,但是脑袋瓜不白给。春天种完地后,便背起铺盖卷,到当时就很繁华的龙城去打工,这也是我们合庄走出去的第一批打工仔吧。等到老秋回来,再把挣到的现钱变成庄稼人用得着的,既便宜又新鲜的小物件背回来。每逢集日,就腿二十多里山路,拿到黑龙镇上去卖,这样里外里又孵出一些钱来。如此几年下来,他家也就跨越了温饱线,奔走在通往小康的路上。又过了两年,就卖了那头老黄牛和它的一双子女,置买一匹马和一辆胶轱辘大车。我大伯和我二伯策马扬鞭,在黑龙镇与龙城之间,倒腾起土豆、干蘑、粉条子一类的东西。家里的田地,就交给我三伯,也就是后来的匪叔莳弄。
匪叔是合庄第一个种大烟的。他家种大烟的那年,别看地不肥,但匪叔的胆肥,两亩多地一下子全部种上那玩艺。烟苗出来后,全庄大人孩子看西洋景似的。虽说这些人中有见识过大烟土,却还没人想要去种那种东西。因为在庄稼人眼中,大烟不是庄稼。人们都说匪叔是个败家子,净瞎整,有了两个臭子就不知道咋美好了。
到了该割烟的时候,恰逢其它人家耕锄已毕,秋收尚早的当口。庄上有的是可以雇用的劳力。青黄不接的季节里,女人不出庄就能挣到现钱,这在合庄人的眼里,就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庄上的大姑娘小媳妇们为这事都犯争了。当时我大姑也想去,只是她还很小,才十五岁,匪叔就没答应,气得我大姑回来后还哭一鼻子。我爷爷知道后,就气呼呼地去找人家。匪叔孝顺,不惹老的生气,就笑着对我爷爷说,叔,不是我不乐意用我妹子,我是看她太小,怕你舍不得,这才没敢答应。你老要是没意见,那赶明个就来吧。我还乐不得找自个家人帮我呢。
我是没见过大烟这玩艺,在我记事的时候,政府早就不让种了。据我大姑说,割烟得起大早,天刚放亮就动工了。每个人发一把割刀,割刀是由两根小木条当中夹着一个可以调谐高度的刀片组成,是匪叔提前预备好的。割烟时,每个人的胸前挎上一个或缸或罐的容器,一只手用割刀从烟桃的顶部向下旋转,在烟桃上割出一条螺纹状的刀口,那白色的液体就从刀口处溢出来。再用另一只手的食指转圈抿起,刮在容器中。等到太阳一火起来,消了露水,也就该收工了。我大姑还说你可别小看那一点一滴的白汤不起眼,等大家伙都割完后,汇总到东家的手里,每天都有几洋瓷盆子,白花花的像一盆盆鲜奶。匪叔家就是靠这一盆盆的鲜奶喂胖的,到土改时,喂出了我大伯和我二伯这两个地主、还有两个地主婆子和一帮地主羔子。
至于种大烟挣多少钱,匪叔家从不向外人透露。有人问起,哥仨都一个口气,说没几个子。但匪叔家是靠这些钱,秋后治买了十来亩地、两匹马、说了两房媳妇,也就是我的大娘和二娘。过年的时候,每人做了一身西洋布面的衣服,年夜饭吃的是洋白面皮一团羊肉馅的饺子。每个人的脸上也都喜气洋洋的。
第二年春天,合庄人便开始红眼疯似地种开大烟了。我爷爷也种了,烟籽当然是从匪叔家里买的。据说,光卖烟籽这一项,匪叔就又把头年雇人割烟的工钱掏了回来。
到了大烟开花的季节,老天爷便开始不高兴起来,整天阴着个脸,偶尔笑一下,也是十分的勉强。再加上种的人多了,家家都忙着割自己的,想雇个人也都找不着。错过了季节,有不少人家的烟都瞎在地里了。难怪当时许多人都报怨,说赶上咱们烧香,佛爷掉腚了。
这年,匪叔家没种大烟。他们兄弟三人,贩买起了大烟。匪叔在家把烟土收购上来,他的两个哥哥再拿到龙城去卖。这比种起大烟来,竟少操不少心、少受不少累、又没少挣钱。秋后,匪叔家就盖起青砖青瓦的四间正房和土墙瓦顶的三间厢房,照样又置买一些田地。兄弟三人换上缎面长袍,成为跨出合庄,走向黑龙镇街面上的人物头。
也就是这年的腊月,奶奶说是腊月廿一的晚上。她说她清楚地记得,再过两天就是小年的时候,这天的后半夜,庄上招贼了。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匪叔家来的。他们翻墙进了匪叔家的院子,便打开了大门。三个贼当中,其中的两个端着洋炮,另外的一个人去圈里牵牲口。马也牵出来了,我大伯也从屋里听到动静了。他顾不得穿外衣就从屋里窜出来,刚刚打开外间屋的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被外面的洋炮给烀上了。身上中了六七颗铁砂,要不是那半开的木板门挡一下,那肯定得打成马蜂窝。屋里的人吓得再也没敢往外冲,外面的人硬是把三匹马活活地给拉走了。那一年的小年大年,匪叔家过得死气沉沉的,连鞭炮都没放。正月初一,大家伙去他家拜年,我大伯还起不来炕,身上的枪伤定着黑糊糊的血嘎巴。也就是从那时起,匪叔家与庄上的二赖子就结下了暗仇。
二赖子是一个人的绰号,这个人姓刘,叫刘天栋。我记事的时候,他都六十多岁了,一个干巴巴的挺和气的一个小老头。奶奶说二赖子年轻那阵子,才不是个东西呢。在合庄这疙瘩也是个混混,家里没地,他也不种地,谁家的地该收成了,他就老早去收成。抓不住就等于没那么回事,要是给人抓住了,那也是抓住而已,顶多把东西给你扔下,他还得骂着走。你要是敢咋地他,那你的麻烦就大了,不是下药害死你家的猪呀狗呀的,就是设法作践你家孩子。惯用的手法是哄小孩子说井里有个什么好看或好玩的,鼓励孩子去井口爬着看;再不就是说那个沟涯上有好看的鸟巢,说那巢里的鸟是他养在那里的,你可不能去掏啊。小孩子不明是非,就背地里去了,鸟倒是没掏着,手却被蛇咬了。这次匪叔家被抢,合庄人都百分之百认定与他有关系。
那天的头半夜,狗叫就是从二赖子家开始的,叫上一阵子,就没动静了。事后人们都核计到了,可能那时候贼就来了,就藏在他家里。到了后半夜,狗叫又是从他家传起来的,等到全庄子的狗都开始叫时,洋炮就响了。
如果说这只是一种猜测的话,最可信的根据是,头年秋天,他去匪叔家的地里偷苞米,被匪叔逮住了。匪叔没惯着他,窜上去就抽他几个大嘴巴。那时匪叔刚刚二十来岁,壮实。几个大嘴巴,抽得二赖子找不着北了。被打后的二赖子本该往西跑才能回家,他竟毛蹶地向东窜去。边跑边不住地委屈,说好你个小三子,你今个敢打我,咱们走着瞧吧!
刚出正月,匪叔就失踪了。走前没有丝毫迹象,走时也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只是家里准备买马的那笔钱不见了。全家人找遍了所有的亲亲故故,犄角旮旯,急得都冒了烟、着了火,所有的人都确认,他一定是去找那伙贼拚命去了。凭匪叔自打小的性子和家人对他的了解,可以说,这个猜测是可能的。
大约过了半个月,匪叔回来了,见了谁都有说有笑的,没事似的。当有人问起这些天他干啥去了,他极轻松地回答,说家里太闷了,出去逛了一圈。但每个人都觉察得到,堆积在他脸上一个多月的愁云不见了。
当天晚上,他家的院子里又响起枪声。这一次的枪声比上一次的清脆,响亮,连发三响,直冲云霄。庄子里有胆大的跑出来看,见匪叔家的大门关着,各屋子里都亮着灯,院里还有时抑时扬的说笑声。人们明白了,匪叔这趟出去是买枪去了,而且这枪还不是上回那几个贼使用的那种洋炮,应该是快枪。自打这以后,合庄就再也没有招过贼。
匪叔提出分家,是在买回枪的那年夏天。农忙过后,他就莫名其妙地把我们家族的长辈全都叫去了,分家的方案也是由他提出来的。所有的房子、田地、家用一切,全部归属他的两个哥哥,他就要那支枪和一匹新买来不久、种地还不知道抓垄的枣红马驹子。我大伯和二伯都不同意,他们说哥兄弟在一起过得好好的,又没吵过架,又没红过脸的,干啥非得要分家不可?就是要分家,那也得给老三张罗上媳妇再说,到那时,连房子带地,哥仨三一三十一,现在的这种分法,别说是对不住兄弟,也对不住死去的老的。满屋子的人也都跟着再五再六地劝说,匪叔就是不听。
整整靠了一个下午,匪叔堵着门口,连人们上茅房都不让出来。众人一看,实在是执拗不过他,也就同意了。按照匪叔的要求,我的大伯和二伯作为协议的一方,他作为协议的另一方,写了文书,画了押。经我们家族的老人公正,这个家就算分开了。
晚上,匪叔家宴请我们家族在场的人,四个菜喝烧酒。当时我爷爷也在场,他后来回忆说,那天小三子喝多了,给在座的各位叔叔大爷们每人都磕了一个头,敬了一杯酒。然后又给两个哥哥和两个嫂子也磕了头敬了酒,就呜呜地哭了。
第二天早晨,天都没亮,匪叔就走了,一人一马悄悄地出了合庄。以后的合庄人,除了二赖子以外,其它人就再也没见过他。当然了,这里面很可能不包括我大伯和我二伯。
匪叔离开家后,就奔龙城方向去了。以前他和两个哥哥来过几次,对这里轻车熟路。他在一家镖局对面找了家不显眼的客栈住下后,白天没事就上街上闲绕,晚上回来,吃了饭,要一壶浓茶,坐在客栈的台阶上望着对面愣神。直到第五天的傍晚,匪叔结了帐,买下十几个馒头,背在身后上路了。
匪叔赶了一夜的路,天放亮时,他也到达距龙城二百多里的二道山上,这是通往省府的必由之路。
进了山谷,匪叔找一处背静的沟岔子,把马拴在树下吃草,他自己找了一蓬树荫席地躺下。他在等那个马队——那个昨天下午从龙城出发的,由十匹马和五个人组成的马队。
匪叔整整地等了一天,太阳渐渐地偏西了,沉寂一天的山谷也一下子热闹起来。喜欢夜间出没的小动物开始蠢蠢欲动。突然一只野兔从匪叔的身边窜起,箭一样地射出,吓得匪叔从头到脚一倏痉挛,身上立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的手不知啥时候已掏进怀里,手指触到那硬梆梆东西,一下子蹦到嗓子眼的那颗心,又慢慢地沉了下来。他对着远山顶上那抹燃烧的红霞,长长地吁出一口冷气。
匪叔牵了马,从山坳中走出来,他边走边环视着四周,可能是受这青山绿草的薰染,他渐渐地觉得自己的心情舒展一些,周身的血也流得顺畅了。他有一种唱几句京戏的渴望,他是喜欢唱窦尔顿盗马的,可是不知怎么了,那词,一时间竟一句也想不起来了。他的脑子中又出现他喜欢的另一个人物,他要像张飞那样,立在当阳桥头大吼一声,啊——可这吼声一出口,却显得有气而无力。他顿了一下,又一次地吸足了气,想再来一次。可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竟是一声嘶哑的呼唤:爹——娘——哥——那声音九曲回肠,在空旷的山谷来回盘旋,被山风冲击着,撕扯着,变得断断续续、丝丝缕缕,飘向远天。
匪叔步行大约一里多的山路,来到大道上。那匹枣红马驹子可能是看见天色已晚,吃住还没有着落吧,就咴咴地叫着走在匪叔的前面去了。匪叔被它拖着,又走了大约半里来地。
终于,匪叔在大道的拐弯处选定一个位置,他把马连打带骂地赶进道旁的小树林里,拴在一棵树上。他解下背在身后的包裹,从里头拿出十几个铃铛,分别系在马的脖子和尾巴上。又脱下外衣,撅一些树杈子,把衣服打扮成一个人的形状,支在一棵大树的后面。让这个“人”既能被路上的人发现,又看不太清楚。做完这一切之后,匪叔从怀里摸出那支带着他体温的手枪。匪叔抚摸着它,端详着,像是在感受或者区别它与镐头、铁锹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