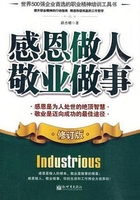我爸老糊涂了,竟然还要我念四书、五经,他难道不知道现在是民国了吗!那天我说想去外地上学,他虎起一张老脸:“不行!圣人云……”没办法,我只好踅出来,沿着寨墙慢慢地走。天空静静的,墙边有不知名的黄色小花正一朵一朵地掉到地上来。我看着日头下自己又瘦又扁的影子,一肚子的无聊全堵在嗓门眼。正好呆毛的儿子阿雄迎面走来,阿雄说,一起去——文庙玩!
孔夫子是铁木雕的,又黑又大,板着一张老脸。孔夫子的后心有个碗口大的洞,真古怪,我刚想把手伸进去摸摸里边有啥东西,不想阿雄抢在了我前面——阿雄家里穷,我爸说过,穷人就是猴急猴急的,办不成大事情。
阿雄的手一进去,马上烫到火似的抽出来,天啊,他的手腕上叮着一条蛇,一节黑一节白,一节白一节黑。阿雄双手一捺一扯,把蛇扯作两段,紫着脸侧过眼微微一笑,轻轻说,哎哟。说完就趴在孔夫子的脚边,不动了。我望着一动不动的阿雄,想,我还有很多没看过的东西呢,我还有很多没去过的地方呢,我不应该像阿雄一般轻轻易易就不喘气了啊。
我出了寨门,望定东方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路上,尘土比巴掌还厚。
可是,刚走到盘龙岭下,问题就出现了——我身上没有钱。我总不能饿死在路面上啊,所以我走进了九一八加强师的师部。汤师长说,啊,末叔,啊,末叔。
洗好吃好,汤师长取出一套浆得笔挺的副官服套到我身上,他说,副官不是官,不是正式军人,只是附着官陪官说闲话的人,委屈末叔了。
那身副官服实在太宽大了,风迎面一吹,我就想飞起来,跟只大鸟差不多。
汤师长几乎天天陪我泡工夫茶,茶杯一捏在手心,他的话就止不住。他说,流氓会武术,谁都挡不住;他说,坏人活得当然比好人好,不然,他们把自己弄得那么恶心就没啥意义了,保长就是个坏人;他说,他是真的喜欢大眼媚,噢,不是喜欢,是爱;他说,那天晚上要不是我爸他爷爷亲手捆的他,他早就被半月塘的红鲤鱼啃成了零零碎碎的骨架子……
可是我一直就没法想明白,他为什么每次漱完口非得把水吐回井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