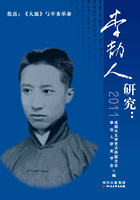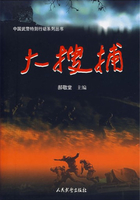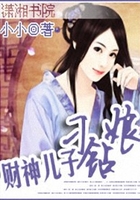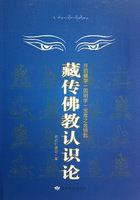沙拉丁和吉布列尔等移民或曰自动流放者就在这样的心境中开始“翻译”自己的文化身份。对沙拉丁而言,他在适应伦敦生活的同时,也以一种骇人听闻的方式投入到“逆写帝国”的阵营中,尽管这是一条注定坎坷不平的道路。仿佛是卡夫卡笔下那个变为甲壳虫的变形人格里高利,身体状态每况愈下的沙拉丁在某一天头上长出了角。“他的情况的确糟糕透顶。他的那些角长得又厚又长,扭曲成阿拉伯花纹状,以包裹黑骨头的头巾缠绕在他的脑袋上。”沙拉丁尴尬地告诉朋友:“我真的说不出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时我害怕自己正在变成什么,变成别人一定会称为糟糕的东西。”到了后来,他的朋友们、邻居们都梦见他怪异吓人的模样。“在那一千零一个梦里,每一个梦都有肢体庞大、头上长角的沙拉丁在唱歌,那歌声如此诡异恐怖、喉音不清,人们难以确定是哪首歌词。”这样的噩梦夜夜光临,使人们惊魂不定。沙拉丁的歌声可以视为一种对抗殖民话语和“逆写帝国”的特殊方式,而他畸形的角则是“文化休克”和白人话语双重压迫环境里启动的防护机制和紧急预案。斯皮瓦克认为,《撒旦诗篇》打破梦幻与现实的边界,这应该为它带来一个副标题:“帝国主义与精神分裂症(Imperialism and Schizophrenia)。”这是因为:“帝国主义搅乱了身份认同。”与此思路一致,印度后殖民理论家阿西斯?南迪(Ashis Nandy)从精神病理学角度分析后殖民时代移民的身份认同困境。南迪认为,殖民主义导致自我与非自我的分野、梦与现实行走的结构性分野。如头上长角的沙拉丁变成异形人便是一种“精神崩溃即自我意识的丧失”,自我与非自我分离,这是一种特殊的“分野”。南迪将这一分野视为“后殖民时代主体人的一种防卫机制”。对南迪来说,人的主体变成“他者”或与自己相异化,其目的是“拒斥那些在他自我本质要素中受到的暴力伤害和精神侮辱”,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使他的世界“变得梦幻一般或虚幻模糊”。《撒旦诗篇》里的一些描叙与南迪的理论相一致。吉布列尔的精神困惑也说明了精神分裂症的“防卫冲动”:“他的自我意识被分为两个本体……吉布列尔将其中一个当作另外的自我加以刻画,他保存、培育之并悄悄地变得坚强起来。”这种防卫机制的启动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心理的“翻译”程序。经过“翻译”,吉布列尔似的移民者似乎变得“坚强”起来。
在这样一种特殊环境中成长的沙拉丁逐渐被西方文明所“改写”,他后来回到故土时感受到奈保尔似的又一种“文化休克”。他因想砍掉象征传统文化的老夹竹桃树而与父亲闹得不可开交。他不喜欢别人不预约就来拜访他。他忘记了祭祀祈祷的颂词和仪式规则。他对人说,“在自己长大的城市里,只要我走自己的路,我就迷失方向。这不是家。它使我迷惑,因为我感觉它既是家又不是家。它使我心跳,使我头晕。”在受到同胞的呵斥后,他取出了返回伦敦的机票。但不管怎样,沙拉丁与奈保尔一样,还是没有完全忘记自己的文化之根。小说接近尾声时,这个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来回摆渡者回到了东方岸边。沙拉丁的父亲将要去世。他对父亲的温柔动作是:“沙拉丁走到父亲前面,把头低在老人抚摩他的手掌下面。”再一个标志性动作是语言传统的回归:“现在沙拉丁找到了更好的词语,他废弃已久的乌尔都语又回来了。”于是,他用传统语言跟即将辞世的老父亲说:“阿爸,我们大家都在你身边。我们大家都非常爱你。”父亲虽然不能言语,但以轻轻点头表示认可。可以说,在《撒旦诗篇》中,正是文化差异和精神失衡导致了萨拉丁等印度海外移民的自我分裂。“萨拉丁的自我分裂为世俗与社会、伦敦与孟买、东方与西方;吉伯列勒则是灵魂的分裂,他失去了自我原有的信仰,渴求但又找不到新的信仰。”
与沙拉丁稍微不同的是,吉布列尔在移居状态中的体验相对来说更是宗教上的。虽然他曾有过与白人女性艾妮短暂的跨种族结合,但这并未给他带来多大心灵的冲击。吉布列尔充分发挥他的演技,在梦里成为萨利姆般具有特异功能的“宗教变色龙”即一个天使长。他具有过人的胆识和未卜先知的特异本领,变成了虔信者顶礼膜拜的对象。这些对象中包括了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白人。他们对这个移民身份没有公开的天使长打心眼里佩服。吉布列尔高高地翱翔在伦敦上空。“他俯视这个城市,瞧见了英国人。英国人的麻烦就在于他们是英国人。这些该死的冷鱼!” 吉布列尔非常亢奋。“他想给他们炫耀一下他的权力,对,权力!这些软弱无能的英国人!他们难道不知道他们的历史会回过头来纠缠他们吗?……英国妇女拿他再没办法;阴谋已经败露!它和雾一样消失了。他将使这片领土变得崭新。他是天使长吉布列尔。他说:‘我回来了!’”在叙述中间,拉什迪颇有深意地穿插了后殖民理论始祖之一法侬的两个句子:“本地人是被压迫者。他永远梦想成为迫害者。”“以这种方式,每个人接受上帝赐予的变化,向定居者和命运低下头去。”将吉布列尔的颠覆性梦想和法侬解构殖民帝国话语的理想两相对照,可以发现拉什迪借吉布列尔的魔幻之梦解构西方话语的意图,这是一种典型的“逆写帝国”姿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学者的话有些道理:“第三世界的流亡小说是政治性的。”不过,悲剧的是,吉布列尔对西方的大胆解构被发挥到极至,运用到东方文化经典的颠覆和改写上。于是,他的命运急转直下。故事接近尾声时,吉布列尔回到了孟买重操电影旧业。他决定改编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他将史诗中神圣的印度教英雄罗摩写成腐败邪恶分子,印度教妇女视为贤妇榜样的罗摩之妻悉多被写成轻浮之女,而掳掠悉多的魔王罗波那被刻画为正直忠厚之人。这招来了愤怒的反对声。一个叫乔治的外国人说:“吉布列尔在玩弄罗波那。看起来吉布列尔是故意与宗教保守者最后摊牌,尽管他明知自己赢不了,还将身败名裂。”这些评价似乎是拉什迪对自己后来厄运的准确预见,但这实在太过悲剧的味道,令人叹息。这或许是解构主义自我作对的活生生的例子。结合拉什迪自己的思想再往深处思考,我们发现,他的解构姿态来自于他对母邦传统文化的逐渐疏离。有一次,拉什迪从印度回到英国时透露说,访问印度使他感到相当的不舒服,因为:“我对印度的疏离感已经接近于一种纯粹的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状态。”在故事的最后,吉布列尔告诉他相依为命的同胞沙拉丁:“很久以前我就告诉过你,如果我觉得疾病缠身并不断发作,我就不可能再忍受下去。”说完,吉布列尔将枪筒伸进嘴里,扣动扳机,一切就此结束。吉布列尔的灵魂升天与罗摩、悉多等神祗的灵魂汇合。吉布列尔这个先以西方“权力”话语解构西方的移民代表,将其解构主义手法运用到本土印度,失败在所难免。吉布列尔的自杀和《午夜》结尾处萨利姆身亡、乃至《耻辱》的黯淡尾声也显示了拉什迪印度书写的某些微妙心思。黑色结局暗示着许多复杂的信息。
总之,沙拉丁的回家之路和吉布列尔的生死轮回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体现了拉什迪关于后殖民时代世界移民问题的深刻思考。例如,拉什迪借书中一个人物的口说:“我们将改变事物。我曾经承认我们自己也将被改变。非洲人、加勒比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孟加拉人、塞浦路斯人、中国人,我们可能不会成为现在的模样,假如我们没有跨越海洋,假如我们的父母不穿越天空去寻找尊严和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生活。我们已经被再造了,但我想说,我们也将重建这个社会,从底层到表层来改变它的面貌……现在轮到我们了。”这说明,拉什迪相信,世界移民大潮将改变移民者的文化心灵,而移居地国家也将因为这些身份各异的世界移民或曰世界公民而改变面貌。这就是《撒旦诗篇》在移民主题上的新思考。正因如此,有人指出:“拉什迪的《撒旦诗篇》是已经出版的关于英国移民体验的最雄心勃勃的小说,尽管它无论如何不是此类书中的第一本。”
有人说:“拉什迪在《撒旦诗篇》中关于移民身份问题的积极判断,一定程度上可与奈保尔此前出版的《抵达之谜》相比较。历史与当前现实的定位(location)、疏离(dislocation)这一相同问题被两人所检视。两人都在作品中呈现了相似的意象和场景,然其得出的结论和唤起的感情却有天壤之别。”具体说来,两人都从自身历史与身份出发,探索了移居者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这包括适应新环境或与之疏离的问题。在《撒旦诗篇》与《抵达之谜》中,移民者关于新家园的幻象与他创造出来以与这一幻象挂钩的新身份成为共同的关注焦点。对奈保尔而言,这一新身份的创造会导致对英国的模仿(mimicry),他的《黑暗地带》已描叙过这一点。但对拉什迪来说,真实身份与家园幻象二者之间并非截然分开,而是互相交融。“沙拉丁与吉布列尔都是演员,都擅长彼此间互相模仿。他们是文化变色龙。”在《撒旦诗篇》中,沙拉丁的人格是“模仿与声音的半组合”,而吉布列尔的身份似乎是一种“暂时而过渡的建构”,他的快速裂变似乎与神的死亡相似。“与文本相似,吉布列尔在影片内部和外面的身份建构,打破了幻象与现实、世俗与神性、神圣与亵渎的界限。”吉布列尔的身份是一种“破碎的、有裂痕的人格”。吉布列尔对于现实的思考和奈保尔的移民观有点不同。吉布列尔能看清“水面下隐藏的冰山的十分之九”,他有超自然的坚定信仰,而奈保尔似乎很轻视幻象和不真实。另外,对奈保尔来说,死亡是变化和衰败腐烂的流程,而拉什迪在《撒旦诗篇》里将死亡视为一种比较积极的因素,尽管他的积极心态也是不彻底的。对奈保尔来说,抵达文化家园是一个幻想、是不可能的,但拉什迪在《撒旦诗篇》中暗示,对移民而言,抵达的概念有多重涵义。旅行本身便是回家(The journeying itself was home),有回家的念头便也是回家。仿佛一种心中有佛即是佛的味道。说到底,拉什迪与奈保尔之间最明显的一个书写差异是心态问题。因此,有人说:“拉什迪并不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地描述印度形象,而奈保尔在他的《黑暗地带》和《印度:受伤的文明》中就是这样做的。”拉什迪充满魔幻激情的笔触则将将读者带入一个“怦怦心跳、热血沸腾、色彩斑斓的文学世界里”。
值得一提的是,名字的变化是后殖民创作的一个基本道具。对拉什迪所有文本而言,名字的消隐和重新获得是身份印证的一个关键索引,因此非常重要。沙拉丁和吉布列尔的名字和身份几经变化说明了这点。
印度学者认为,拉什迪的《午夜》、《耻辱》和《撒旦诗篇》都属于自传性质,因为它们“将拉什迪自己精神生活和知识生涯的各个阶段进行小说化”。从《午夜》和《耻辱》着力思考印度次大陆历史风云与现实政治再到《撒旦诗篇》探讨移民主题,这反映了拉什迪关注中心的显著变化,反映了他由思考家园文化到思考跨越东西文化的思想轨迹,这与他在西方文化的漩涡里“出生入死”并自得其乐有很大关系。正如克巴尔所说,我们生活的时代是“流亡和避难”的时代,而此前就有许多这方面的范例:“叶芝、康拉德、乔伊斯、劳伦斯和艾略特等二十世纪初期的伟大作家都是边缘人(marginal man),他们在冲突文化的无人地带不同程度上黯淡地生活着,六十年代最有趣的作家如贝克特、巴德温、纳博科夫、贝娄等人也以清高姿态这样生活着。”因此,我们可以将拉什迪视为西方世界书写移民主题或自我流放谱系上一个坚固的链环,他的艺术之花开在东西方文化传统交融的土壤里。
$第三节 “愤怒的‘Fatwa’”:“拉什
迪事件”及其文化内涵
1984年,拉什迪在接受访谈时说:“我正在写一部小说,我很惊讶,这本小说的背景又是印度……它似乎不是政治小说,而是关于神和宗教的小说。”这本小说就是后来为他带来杀身之祸的《撒旦诗篇》。拉什迪接着说:“然后我确实还有一个更大的小说创作计划……一本背景设定在西方并涉及移民观念的小说。”这说明,拉什迪原本准备在《撒旦诗篇》之后,再另外写一本以自己移民体验为主的小说,而不是实际上将移民与宗教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撒旦诗篇》。《撒旦诗篇》出版后第二年即1989年,拉什迪在一篇文章中补充说明道:“我原来打算写一本小说,其最基本层面是有关变异的问题……我对语言、社会、地域的自我传统之根怎样在移民迁徙中崩溃断裂很感兴趣……那才是我真正想写的东西。”但十分遗憾的是,拉什迪没有坚持最初设想,而是将移民主题和宗教探索混在一起,形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混杂性叙事。《撒旦诗篇》整个五百四十七页英文首先就是一个主题情节的大杂烩。第1、3、5、7、9章讲述沙拉丁和吉布列尔两个从飞机上掉下又奇迹般生还的印度移民的故事;第4、8两章以发生在巴基斯坦一个村子的真实悲剧为基础,叙述阿伊莎率领民众走向大海无一生还的故事;第2、6两章则涉及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某些方面的故事,这一故事部分基于历史事实,部分来源于作者的想象。实际上,就是第2、6两章最先引发了穆斯林世界的抗议怒潮,并最终升级成为东西方外交危机和二十世纪后期最引人注目的国际文化现象之一即“拉什迪事件”。
《撒旦诗篇》之所以如此“臭名昭著”,是与它在描叙伊斯兰教时涉及的三个方面问题有关,即小说名字、小说人物描写和小说情节的叙述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