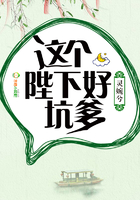很平常的五月,上午十点暮晓的员工各司其职,整间办公区传来噼里啪啦敲键盘的声音,苏暮哲手持文件从会议室走出来,郑重其事地拍了拍沈信的肩膀:“好好干。”
阳光明媚,纯白的柳絮从窗外飞进来落在阳台上,紧接着打个旋儿团在角落里。筱雅站在窗边屏住呼吸欣赏着远处的美景,她从小就喜欢这种落地窗,将一切尽收眼底仿佛君临天下。
她不需要君临天下,她只要虏获一个苏暮哲就够了。
只有苏暮哲才是她的归属。
她抚摸着被太阳灼热的玻璃窗,想起自己鱼一样褪下衣衫站在暮哲面前的那次闹剧,记得,当初他慌张得拉紧所有的百叶窗生怕她的身子被谁瞧了去,这么高,有谁会看得见呢,又不是飞鸟。
她的笑如花般绚丽,踩着高跟鞋向后连退了几步,毛茸茸的地毯松软得像被水泡过似的,有些发胀,她笑着向后仰正好被人接住。
“真是调皮,万一不是我,看谁那么大胆子敢抱你!”
苏暮哲从会议室回来,正看到她张开双臂向后躺,他三步并作两步冲上去抱住她,筱雅自然而然跌在他的怀里,瞬时笑个不停。
“算好了是你才会这样的嘛。”她撒娇的样子让人招架不住。
苏暮哲随手将文件搁在桌子上翻过她的身子,他勾着笑猝不及防的揽过她的腰。筱雅猛得撞上他的胸口,抬头惊愕的瞬间被漫天霸道的吻压到窒息,她享受着他给的甜蜜,下意识得腾出手护住自己的小腹。苏暮哲有所察觉立马松开她:“走开。”
她笑着挣脱他的怀抱:“自控能力还是不够出神入化啊。”
苏暮哲不答话,转过身不再理她。
“还生气呢?”
苏暮哲狠狠瞪了她一眼,低下头委屈的像个孩子:“我真的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你明知道我拗不过你,更不可能忍心伤害你。是不是我太宠你了你才会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们努力经营的爱情,不在乎我们的……孩子?”
自己的妻子明知道怀孕了却不把实情告诉他,他怎么可能不生气。不告诉也就算了,他姑且还能幻想着她想给自己一个惊喜,可是当听到她缓慢沉重地说“我是无法确定该不该生下他”的时候,他的心都凉了,整个人一下子仿佛陷身于南极大地,周身寒冷,听不见任何语句,看不见其他景色,他的心里、眼里独独只剩下一个她。
“别生气了,我错了还不行吗?从下个月开始我就按时去做检查,保证让宝宝安然无恙的生下来!”她握紧拳头,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
苏暮哲舍不得丢她可怜巴巴地站着,无奈走过去抱着她,筱雅见他原谅了自己,甩开高跟鞋跳到他面前,脚踩在他的皮鞋上:“哼,就知道凶我,我那是气话你也信!”他箍紧她的身子恶作剧的向后退,最后靠在落地窗上:“这玻璃被咱们俩倚碎了可怎么办?这可是二十八层。”
她伸出手指摩擦着他的鼻翼:“那就一起掉下去呗,大不了作对苦命鸳鸯,奈何桥上一起投胎呗。”
她笑着抬起头,刚才开玩笑时的轻松表情一下子被害怕和恐惧代替,她从苏暮哲的身上跳下来,抓起他的手躲得远远地。
在一旁的苏暮哲看到惊恐万分的筱雅心里顿时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攥紧她的手,她的手冰凉,此时脸色也异常苍白。他回头看向窗户,什么都没有。他问:“怎么了?你看到了什么?”
筱雅身上虚软,瘫坐地上,她双目直视着玻璃窗,外面依旧晴空万里,艳阳高照,云朵飘来飘去宣告着这个不平静的五月天,再远一点是飘渺的山岚,星星点点的绿蔓延到无边无际的天尽头。她终于抬起颤抖的手,指着外面:“有……有……有东西从这里掉下去!”
她的脚像灌了铅似的,只能撑起身子扶窗向楼下张望,一层又一层的人向这个方向聚拢。她能想象到,残忍的人类从四面八方而来,像丛林中嗅到猎物的豹子,他们挪动着好奇的步子,一步步,然后发出感慨,发出品头论足的惋惜,然后谆谆教导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苏暮哲扶着筱雅乘电梯下楼,一出大厅就闻到一股腥气,浓重的血腥味混合着刚刚被雨水冲刷过的青草香让人呕吐难忍,筱雅有孕在身,胃里一阵恶心。她只觉得这会自己的脚像踩在棉花上似的,稍稍松懈就要栽倒。办公楼外的暮晓广场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了,广场一边远远停着两辆警车,警察走到苏暮哲面前出示证件:“苏董你好,我们收到消息有人在你的公司自杀身亡,”他看了看手里相机实拍的照片,“你们公司的目击者表示轻生者是暮晓前任董事苏柳,也就是……你的父亲。”
“哇”的一声,筱雅挣开苏暮哲的怀抱反身直奔一楼盥洗室,她趴在梳妆台前干呕着却吐不出任何东西,她只觉得恶心,手接凉水不停得拍着脸颊,尽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刚才,她亲眼看见有东西从高空坠落,她以为是自己胡思乱想,或者是看错了。
没想到……是苏柳。
她胸腔起伏得厉害,心脏突突突跳得极快,耳边根本没有警笛却恍惚能听到扰人的噪音,她看到广场上人头攒动,一群捕风捉影的记者将苏暮哲紧紧围在中央,她看到他无所谓的表情,突然觉得好累,累得不能呼吸。
大脑一片空白,机械般停止运转。为什么?为什么会闹到今天的地步?她只想帮暮哲夺回一切,不曾想要逼死谁。为什么现在的所有所得并不是昨天的自己奢望和渴求的?她做错了!又是哪里错了?
她强迫自己重新打起精神,刚要往外走却被角落里一股力量带进了黑暗,还没等她做出反应眼前又瞬间恢复了光亮,昏黄的灯晃晃悠悠地在上空摇摆,这里是在一楼仓库,她踏实下来,回头看过去:困她在此的人竟是苏少哲!
苏少哲跟刚离开公司的时候相比瘦了好多,脸颊凹陷,双目突出,此时再看不出从前帅气绝美的样子了。他穿着一件亚麻短袖露出双臂,筱雅沉默地打量他,他的胳膊上布满密密麻麻的针孔,这情景让她心有余悸。
她试图让自己镇定下来:“有何贵干?”
此时落魄的苏少哲依旧秉着过去的高傲,他勾着笑,少了一丝魅惑多了一分恐怖:“苏柳死了,你们满意了?”说完他放声大笑。
筱雅连连后退:“他是死是活与我们没有关系,是他自己从顶楼跳下去的。”
苏少哲冷笑着:“不必害怕,你们不必担惊受怕,也不用自责内疚他的死是因为暮晓!跟你们没关系,是我害的,是我逼他的!”他笑起来猖狂无比,让筱雅想起《死魂灵》中邪恶的诅咒。“你看,”他指着扎满针孔的双臂,“我戒不了,又不想死,债务上写的都是他的名字,他死了债款就能一笔勾销!这是规矩。所以,我……才推他的,是我推他掉下去的!”他笑得让人寒毛竖起。
筱雅不敢相信这世上还有人会做出这么疯狂的事,他是疯了!他们都疯了!“你知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这是犯法的!”
苏少哲听了“扑通”一声跪在他面前,面布表情抽搐得厉害:“求你!行行好,给我点儿钱,我戒不掉,浑身都在被蚂蚁啃噬,它们咬我!你们有了暮晓还在乎这点钱吗!求你,给我!给我一点儿就好,好难受!”他浑身像长满了刺,不停地扭动。
筱雅看他哆嗦的样子才反应过来,苏少哲是精神失常了。她看他在地上打滚、嘶喊实在是于心不忍,从皮夹里取出厚厚一叠粉色的钞票:“拿去,别再来找我了,我帮不了你,这是要命的东西,趁着清醒去戒毒所吧。”她扭头要走却被苏少哲狠狠扼住脚腕,他浑身打颤,汗珠顺着额头淌下来,艰难地说:“没……没用,我在那里待不住,”他拾起钞票冲筱雅晃了晃,“谢了,你是好人。”
“还有事吗?没事我走了。”她语气冰冷,面对这样失控的苏少哲她心里说不上来的悲怆。
苏少哲支支吾吾吐字不清,只是费劲的从怀里拿出一支录音笔递给她,她无法会意,不肯去接,“你已经一无所有,我不会乘人之危,何况一支录音笔而已,对我实在没什么用处。”话说到这份上他却迟迟不松手。无奈她只好收起来:“现在你可以从暮晓出去了,永生都别想再踏进来半步,不然我可不敢保证下次会不会报警抓你!”说完她蹬开步子甩他而去。
欲望真的能让人变成魔鬼。
她明明知道他依然会用那些救命财交换毒.品,可还是奢望他能早日悔改,去戒毒重整旗鼓。
似乎还是半年前,她刚刚嫁给苏暮哲做苏家的儿媳妇,那时他们父子三人就水火不相容。那晚家宴卡其色风衣趁着苏少哲修长的身子,他清新俊逸地倚在门框上打量着所有人,略过她的时候礼貌地点了点头。她清楚:苏少哲是尊重自己的。
而那些不三不四的话都是说给命运听的。
他是怪命运的无情,为什么要让他生在勾心斗角的家庭!又为什么会摊上一个连自己女人都守不住的爹!如果从不沾染权钱利,是不是他也能像普通人一样开心、简单、阳光的活?
筱雅能读得懂他的心,她能读得懂所有无可奈何人的心,却唯独读不懂自己的。她更不懂,这世界,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冤冤相报,一命抵一命难道就是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