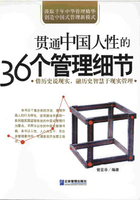莫北顿了一下,转头看了我一眼,再转回去望着湖面,语气平淡的道:“索酒应该去建康了吧?她平安出来,你也安心了。”
我默了一默,没有说话。莫北继续说:“但是徐平南就……”
我一愣:“徐平南就怎么?”
莫北转头看了我一眼,眸子深深。我忽然一个激灵反应过来——是了,依索酒的性格,会放过徐平南吗?我抬头看向莫北:“你……”
“你”字说出来,我却忽然不知道下面应该说些什么。
莫北低头看了看我,唇角提起一点点,展开一个带了暖意的笑容,对我轻轻道:“去吧。”
我皱了皱眉,他好像总是能知道我在想什么,总是能知道我会担心的是什么,这种感觉很不好,会让人觉得很不安。便点点头,说了声:“告辞。”便转身而去。
回家之后,连备马车的时间都没有,奔到马厩随手牵了一匹马骑上,便急急赶去阮郁的府上。建康与钱塘相距虽不算是特别远,可是料想索酒应该不会一天之内就办完事情赶回来。
想来也许是我从马背上翻下来,然后提着裙摆小跑上阶梯的动作有点不雅,守门的两个侍卫将我拦下来,上下打量我一眼,语气还算客气的对我说:“我家公子尚未起身。姑娘若是没什么要事,还是请回吧。”
我喘匀了两口气,急促道:“我有急事,开门让我进去——或者先去通报你家公子,我在这里等。”
我一路急匆匆而来,虽是清冷的天气又吹着风,可额头身上却都已出了些薄汗。发丝有些许粘在我的鬓角,我的衣服都有些不太端正。两名侍卫像是看我实在是不像一个大家闺秀名门之后的样子,便有了些烦躁,挥挥手对我道:“你到底知不知道这里住的是谁?我家公子还未起身,谁敢去打扰?便是有着天大的面子也要等!”
我一愣。另一名侍卫继续说道:“你长的不错,可是我家公子昨夜已经有人服侍了,你……我看你长的这么漂亮,比昨晚的那个人强多了。我家公子最不喜欢纠缠不清的女人。你且回去,等晚些时候再来,说不定公子就见你了。”
我站在寒风中吹了半晌,方才明白他两人到底是在说什么,顿时一股心火升起,手里的马鞭反手便抽到了一人的腿上。我这一鞭确是怒极,手里的力道便也不浅,那人并未料到我如此,立刻被我打的“啊”的叫了一声,半跪到了地上。
另一人呆了一瞬,一边扶他一边对我道:“哪里来的泼妇——来人,快来人!把她赶出去!”
话说,我苏小桥至今算是活了三十年,虽然平时不算是多么淑女的一个人,可毕竟没人敢这样骂我是“泼妇”。立时怒极反笑,用马鞭指着那人道:“今日我苏小小便站在这里,看看你们到底有什么人,敢‘赶’我出去!”
府内早已闻声而来了十数人,原本都对我怒目而视,准备将我赶出府去。可听完这句话,却突然在我身前一步处生生止住了脚步。
我听到站在略后面一些的一个人很小声的说了一句:“是苏小小……我在灵隐寺见过她——她穿着墨梅襦裙。”
我不着痕迹的低了低头,裙摆上手绘上去的墨色梅花若隐若现,在白色的衣衫上格外的显眼。
双方有些僵持不下,旁边有人轻声说:“要不要去请示公子?”
便又有人说:“还没到公子起身的时间……谁敢去打扰?还是先去问问暗卫白羽……”
几个人正低声说着,忽然后面响起一个男声,盖过所有的议论声传入我的耳朵。他说:“属下管教不严,让苏小姐受惊了。”接着又斥了一声,“还不滚下去!留在这里丢人现眼吗?”
人群立刻消失的一干二净,穿着深蓝色衣衫的白羽快步走过来,在我身前行了个见长辈的礼,让我着实的受宠若惊。他说:“公子听说苏小姐来了就起身了,现在在房里梳洗。请苏小姐随在下过去。”
我点了点头,随手将手里的马鞭递给他。白羽愣了一下,才伸出双手恭敬地接了,引着我向前走去。
路上,我瞥了一眼这个,无论我走快走慢都始终保持在我身前半步距离的白羽,实在没忍住,叫了一声:“白羽。”
白羽回过头来,说了声“是”。我继续道:“你以前不是总是穿黑色衣服的么?怎么突然换了颜色了?”想当年我还被他这身打扮和这个名字雷了一下的。
白羽沉吟了一瞬,对我道:“公子让属下换掉的。”
“为什么?”
白羽忽然抬眼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了一下,不自然的笑了一下,方才道:“这就要问公子了。”
我心里觉得有些怪,可是却又找不出到底是哪里奇怪,便不再多问。终究是别人的家事,我也不能太多的打听。
阮郁确实是刚起床,还有些微的惺忪,如以往一般的穿着一件白色的衣服走入堂内,脸上依旧是那千年不变的笑容。
我一见到他,便直截了当的问道:“索酒不会放过徐平南的吧?”
阮郁着实着实的愣了一下,微诧的说:“大清早的,怎么会突然这样问呢?”
我吸了口气,看向他:“索酒的性格如何,你我再清楚不过。平日谁稍微惹她一次,都断然不会有好下场。如今徐平南将她关进狱里足足两日,她会放过他吗?”
乖乖,这可千万不要出人命啊……
阮郁依然笑着看向我,说:“徐平南如此不近人情,确实应该让他吃些苦头。”
“你疯了吗?”我皱了皱眉,“徐平南有什么错?他是侍御史,也是钱塘的地方刺史。这些事情确实是归他管辖的。索酒性格如此,你也跟着糊涂了么?!”
阮郁默了一默,脸上的笑容却半丝都没有变,笑着对我道:“小酒知道分寸的。”
我有些诧异,看着阮郁半晌,方才开口道:“我原以为你懂得拿捏,却没想到你也会随着索酒——你们这对义兄义妹,自己活的舒服了,便不将其他人的命当命看了吗?!”
说完甩了袖子就向外走。
“小小!”阮郁一个箭步冲过来抓住我的胳膊,叹了口气,对我道,“你这个脾气,什么时候才能改改?我原以为小酒的个性之强已是这世上少有的了,你却比她还要强上几分。你平时都是那么个随遇而安的样子,可脾气一上来,却是谁都劝不动的。”
我转头看向另一边,没有说话。
阮郁继续说:“小酒是有分寸的,她不是胡闹的人。只是这次这口气,她肯定是咽不下的。小小,小酒过去经历过许多……不好的事,我不方便对你说,但是希望你能明白,她心里都有数的。”
我默了一阵,对他道:“徐平南并未做错什么……你们……”
阮郁看着我的表情,顿了顿,突然略带惊讶的对我说:“小小,你该不会以为,小酒会要了他的命吧?”
我“呃”了一声。阮郁已满脸是笑,看着我说:“小小,你……你真是……”
我被他笑的脸颊有点热,一把甩开他的手,有些忿忿的道:“你们两个人都是……”说着突然顿住,继续道,“谁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
阮郁像是没有注意到我的不自然,只是又笑了两声,便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我和他回到房里坐着聊了将近半个时辰。这是他成婚后我们第一次坐下聊天,我细细看他的眉眼,带着些疲倦。我们始终没有谈及他的婚后生活,倒不是我有意避开,而是每次想要询问,话到嘴边看到他疲累的样子,便又咽回肚里。
聊了许久,两人都说了许多话。我看了看天色,天早已大亮,想着事情既已解决,就该告辞了。便再聊了两句,站起来向外走。
刚走出门,突然想到还有一件事没有问。便一边回头一边笑着道:“欸,对了。你为什么突然让白羽换衣服呢?”
回过头,却看到阮郁一脸奇怪的表情看着我身上的那件外套,脸上的笑容已然不见,眉头微蹙,呢喃了一句:“怎么会……”
我问他:“什么?”
阮郁又愣了片刻,对我笑了笑,说:“没什么,快回去吧,路上小心些。”
再次见到索酒已是两日后的黄昏。我与她开封了一坛与我年纪相仿的陈酿梅花酿,两人坐在院中的梅花树下无言对饮,秋风萧瑟,借着些酒兴,心里颇有些不痛快。
就这么喝了许久,索酒忽然开口低声道:“这坛酒……当初还是我娘亲手埋在这棵树下的。”
我吃了一惊,回过头去。只见索酒一手端着酒盅,一手覆在脸上。我看不清神情,却觉那声音寂寞。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索酒也默了很久,才再次开口。语未出口,一声苦笑已飘散空中。
我想起阮郁说的那句“小酒过去经历过许多……不好的事”,叹了口气,没有说话。
两个人都有些郁闷在心,正坐着,墨阳突然从院门外走来,却不走近,远远对索酒行了一个礼,道:“小姐,徐平南来了。”
我一愣,看向索酒。她却依旧是那个用手覆着面孔的动作,坐在尚未开花的梅树下。风吹过她的肩膀,削瘦的有些凄凉。就这样维持了有几乎一盏茶的时间,索酒才将手从脸上缓缓移开,微哑的开口,说:“让他进来。”
院子里没有点蜡烛,我借着屋里透出来的光看了看她的神情,却因了烛光摇摆而看不真切。想了想,我将手里的丝帕递了过去,举在她身前。
索酒先是愣了一下,随即接了过去,却没有擦拭脸颊,而是缓缓的擦了擦手指。然后低着头摩挲着手帕半晌,对我道:“这是你自己画的吧。”
我点了点头,又反应过来她低着头是看不到的,便又赶紧出声道:“是。”
索酒忽然手腕翻转,将手帕放到了袖袋里,对我语气略带了些笑意的说:“送给我吧。”
我也笑了:“你若是喜欢,我改天专门画几条送你。这一条我已经用过了,恐怕就算你愿意要,我也是送不出手的。”
索酒却淡淡摇了摇头:“这条意义重大……不用麻烦你了。”
我一怔,忽然不知该说些什么。
好在徐平南很快便走了进来。
上次事出仓促,我并未有心思好好打量他。今天借着些许微弱的烛光看去,只见他面上一丝一毫的神情都无,却有一条细细斜斜的刀疤盘踞在他的左侧脸颊上,不算狰狞,却有了沧桑。
索酒又倒了一盅酒,淡淡无言。
徐平南在她身前四五步处站定,忽然一展衣襟跪了下来,语气全无温度的对索酒道:“在下徐平南,前日对姑娘多有得罪,特来赔礼。”说完伏地恭恭敬敬的叩了三个响头,然后撩起衣襟站了起来。一串动作干净利落,竟无丝毫愤慨。
我有些诧异的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索酒。想了想,笑对他说:“徐大人实在客气了,既然来了,不妨坐下饮一杯薄酒。”说完看了墨阳一眼,示意她备好器具。
墨阳点了点头,看向索酒。我原以为索酒会立刻赶徐平南出去,却没想到她只是挥了挥手让墨阳去准备东西,用手掐了掐眉心,颇有些意兴阑珊。
徐平南却道:“在下从不饮酒。”
我的笑意却更浓,歪着头对他道:“既不饮酒,便饮杯清茶。我今日刚巧带了些好茶给索酒,徐大人来尝一尝,是否合口。”
墨阳搬了椅子过来,徐平南面无表情的坐下。索酒又倒了一杯酒,正待饮尽,徐平南却突然出声说:“女人喝这么多酒做什么。”
我心里有些惊讶,只见索酒拿着酒杯的手突然重重的抖了一下,杯中的酒泼出来了几滴,却又很快恢复平静,淡淡将酒饮尽。
徐平南饮了口茶,对索酒道:“你在红袖招此处做……”顿了顿,继续道,“也不是长久之计。你可还有什么亲人?”
索酒将手中的酒杯满上,抬起头来看着徐平南,淡淡道:“我爹,死了。我娘,陪葬了。我倒是有个哥哥,不过就快死了。你若是赶得快些,也许能见到他最后一面。若是赶不及,就去掘坟——估摸着尸首应当不会烂完。”
我吃了一惊,徐平南也吃了一惊。
我从来没有听过索酒这样讲过话。或者说——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一个人这样讲话。索酒一直敬重爱戴她的父母,怎么会突然……
徐平南显然是被她这番话雷了一下,默了半晌,才继续说道:“在红袖招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我愿为你赎身,你离开这里,找个地方住下来……不要再做这样的事了。”
索酒也怔了一秒,随即有些好笑的问他:“你说‘这样的事’是指什么事?”
我自以为他的意思是说妓子,便知道索酒是故意为难,就也有些想笑。可没想到的是,徐平南的嘴唇动了动,吐出了四个字——
“以色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