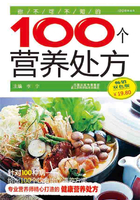如果在我的心里,有一个黑暗潮湿的洞穴。
如果存在光的轨迹。
如果我瞬间忘了呼吸。
狭窄的车厢被暖黄的灯光泡涨,电压不稳,光亮闪烁让人担心下一秒周遭就会突降黑暗。
大雪攀附着车窗缓慢下落,可以想象在靠站时车顶迅速积满白色尘埃。车窗外的世界陷落在夜幕里,虽然看不见,但闭上眼依然能毫不费力地将白天的景象重现--长着高大白杨树的土地像毛毯在迅速向后席卷。
所有的光聚焦在少年的侧脸上。
列车已经在沉闷的气氛中开了两天两夜,像驶向一个悲剧。
无论过去多久,都可以凭借清晰的记忆轻易补全每个细节。他挺直脊背坐在靠走道的座位上,微微压低帽沿,手撑着头打瞌睡,列车每一次靠站都能让他惊醒。他转过头看向窗外,顺便看见少女不那么友好的半垂眼睑。
白昼时会有明晃晃的阳光穿过沉重的大雪打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他的笑很耀眼。
然后……
烈日在眼睑背面画下怪异的红色图案,耳畔的声浪逐渐往远方飘摇,还听得见教官气急败坏地责备:“第二排第四名!不要闭眼睛!”全身的筋骨松软下去,没有了知觉。
醒来时,眼前是白色的墙面,女生勉强支撑着坐起来,身旁好友敬亭的脸上露出释然的神色:“哎,你总算醒了。吓死我了。”说的同时笑着拍拍胸口。
医务室的护士表情冷漠地取过登记薄用笔“刷刷”地写着,问道:“是七连的?”
女生缓慢松开紧锁的眉头:“七连六班,游离。”
眼角余光瞥见纸面上潦草的“中暑”二字。那护士扔给游离两支软包装的棕色药剂:“喝了。”游离刚喝下去,胃里就一阵翻江倒海,但只是干呕了几下。护士看看时间,临近中午,料想是空腹喝药伤了胃,取来一杯糖水扶过游离灌下去,安慰道:“没关系,想吐是好事。吐出来就好了。”
过了十分钟,游离把刚喝的糖水吐了出来,护士一副大功告成的神态让人感到心很累。
军训到第四天,连医务室的工作人员都见惯了站军姿时中暑晕倒的女生,只晓得感叹“现在的女生真是娇气”,却没有谁会去操场上跟着站半天证明自己的不娇气。
医务室冷气太强,半分钟后已经明显感到脊梁上的汗结成冰刺着骨。这样下去喝多少藿香正气水都要感冒。游离被敬亭扶着回了寝室。
很快到了休息时间,别的同学也被释放回来,进门第一句话就是无一例外的“游离,没事吧”,女生微笑着一个个回应过去。
记忆就似这样,明明令你刻骨铭心地痛,却还要努力微笑。
一点一滴,即使时间像输液瓶里的盐水一样以恒定的节拍无情流逝,即使整整一年时光,你不敢在心里提起他不敢去想那次旅行,即使那么久假装失忆,你也依然会在晕倒失去意识前不由自主地记起每一个细节。
即使看见一个“翔”字,也可以像荆棘刺进心脏室壁。
更不用提--
他站定在下面两级台阶上,转过身,穿的是橄榄绿色的军大衣,英俊如早期苏联电影里帅气的男主角。他抬起头看向自己,自己身后涌来的光线爬上他的眼睛,形成瞳孔里明亮的高光。他的眼神里恍然浮现一丝孩子般的迷惑不解,身边甬道的玻璃窗外落下白寥寥的雪片。
慢镜被打上柔光,幻化成黑暗潮湿洞穴里一道漫长的光的轨迹,不知延伸向什么地方。
那天,少年朝自己仰起脸:“你没事吧?”
无限温柔的声音。
让人瞬间忘记了呼吸。
晚上突然通知,教官要教匕首操,重新在操场集合。等敬亭拖着一向动作慢的游离赶到操场,前路已经可以用“怨声载道”来形容。
“应该是休息时间啊!真没人性。”
视界里是一厢黑暗,只有丁点幽黄的光亮,游离大致可以辨出那是一盏路灯。除此之外,仅剩的活动影像便是近处做操的敬亭,无数个影子重叠,人形在方寸间摇曳。
游离跟着敬亭做动作,模仿得模棱两可。各班教官“匕首操格斗准备”、“第一节”和“杀”的喊叫声此起彼伏。
忽然听见不太真实的声音,“后面的人看得见么?班副,班副,你看得见么?”直到连敬亭也停下动作转头看向自己,游离才反应过来教官是在叫自己。
教官被称为班长,在校身为学生干部的自己被称为副班长,也就是班副。
游离抬起头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依旧是黑暗。黑暗旋转起来,声线朝外抽出了丝:“班副,你看得见我的动作么?”又重复问了一遍。
女生咬了下嘴唇,回答:“看不见。”
脚步渐响,似乎是移近了一些,但仍不足以近到让游离看得一清二楚。
视野里不变的是一团氤氲的光,暗黄的颜色。有风声敏捷地绕过示范的教官的身侧,从行列里穿梭而来。如果足够心细,也许能“听”出他的动作,然而,仅仅是理论上存在的可能性。
明明闭上眼睛能听得更加清晰,却因为畏惧某种不存在的东西而始终盯着空无一物的前方。
明明做过那么多努力,却还是无法彻底忘记那辆列车上发生过的一点一滴。
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游离下意识地捏紧了手中的“匕首”--只是用来充当替代品的笔。在空气中腾起了“这次看得见了吧”的问话之后,听见教官渐渐走远的步伐。他想当然地在心里替游离做出了回答。
有谁会在这么近的距离内依然看不见呢?
敬亭趁着转身的动作回头看向游离:“干吗不直接跟他说?那样就可以申请不练啦。”
“嗯?”游离反应有点迟钝。
“直接告诉班长你有夜盲症不就行了么?”
游离的手腕顿时感到一阵犹豫的压力,迟疑片刻,已经来不及,等把视线重新收回到自己的右手,恰好看见“匕首”在晚风中划出悲伤的无形轨迹,将无数断点连起,凭借最后一丝气力消失在游离狭窄的视野之外。
不见了。
完全看不见了。
炎夏的怀柔军训基地,沙石铺就的操场没有承载阴影的能力。可以清晰地看见汗水顺着自己的刘海滑落下来。
白昼,地面有冉冉的热风腾起,远处的景物在这种衬托下变得扭曲。像是世界和人一同在气化。
因为迟迟不下“休息”的命令,观礼台受到无数诅咒,难说哪天不会被实体化的怨念压垮。--脑海中冒出如此滑稽的想象,游离“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惹得教官凶狠地瞪来一眼,游离却丝毫不觉得生气或难为情。
就算同样穿着军装,却有着天壤之别的气质,教官和他完全没法相提并论。
不是当光线切下来,半张脸隐没在阴影里的沉默的少年;不是当列车飞驰,墨色头发被窗外呼啸而过的白杨树枝映出深浅色泽的少年;不是那个为了让自己好好睡上一觉消失一整夜的少年。即使他只是段借着在自己身边所有人身上投下落点而存在的回忆,也不是任谁都在自己心里取得和他等同的地位。
其他人的态度,游离不在乎,可以一笑而过。
连长的喇叭响起:“各班班副和寝室长出列!”
游离回头看向敬亭,然后两个人一起跑去行列的前面。“呃,天天检查内务,烦不烦啊。”敬亭摊着手抱怨道。
“唉,你不觉得,比起他们,”游离手指了指身后依然在站军姿的同学,“我们已经幸福多了?”
“那倒是。”敬亭插进被召集起来的小队人马里。游离跟在她后面。刚学了齐步走,游离在小队列中尽量保持姿势的标准。
四班副自发地喊起“一二一”的口号。三班副走在游离身后轻声笑起来,游离茫然地回过头去看她,她答道:“你走路姿势好可爱呀。”
仅仅一句话,就让游离泄了气,恢复成平时走路随随便便的姿态。
站在寝室门口,连长叫道:“六班副?”
“嗯?”女生惊觉地抬起头。
“六班副?”声音不明所以地放轻一点。
“嗯?”
“六班副?”
别班的副班长和寝室长都纷纷掩嘴笑起来。
游离这才反应过来,答:“到!”
“我觉得进步很大呀。你觉得呢?”连长看着整齐的被褥笑着说。
“嗯……我也觉得。”游离有些不知所措地附和。
“都学会‘嗯’了。进步不是很大么?”
“欸?”说的原来是这么回事。女生绷紧的脸终于松下来。
午后阳光投射进寝室,光线的通路中,升腾起无数细微的灰尘颗粒。幻象穿过时空,来到自己眼前坐落成真实。
列车员要求登记身份证。少女从包里掏出自己的证件递过去,途经少年的眼前。
“游离?”
视力很不错。女生点点头。
“我叫京翔。”见女生的眉型微微弯曲上扬,少年进一步解释道,“北京的京,飞翔的翔。”
“京翔?”语气中带有一点迟疑。
“到!”
车行到第三天,少年的脸上露出孩子气的笑,下颌敛出利落的曲线,栖息在颧骨上的阳光顺势下滑。稀薄的雪花无声地从窗外飞过。
少女的瞳仁微妙地改变一些,深色中泛起晶莹的光泽。“京翔。”
“到。”
列车一个大幅度的摇晃,所有人往前栽了一下。稍许惊慌的女生抓住身边少年的袖口,很快轻易地稳住了重心。
被子是同寝室的小诗帮忙叠的,如果换作自己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把棉絮压成豆腐块儿那个地步。不能拆了来之不易的被包,所以,只能盖多余的床单。熄灯号吹响,灯光一盏一盏灭下去。已经不是属于自己的世界。
从来不清楚那些所谓的灿然星光是什么样。一旦没有灯光,对自己来说就是千篇一律的漆黑。
即使把眼睛睁到很大很大,也依旧什么也看不见。
游离凭空瞪着上铺的床板,眼前其实只是虚空。明知道它的存在。
听见水房里传来女生们摸黑洗衣服的水声和说话声,明知道她们的存在。
就连自己寝室里也还不时响起手机发短信时的按键声,明知道它们的存在。
--但是,你看不见。
以及你见过的、爱过的、留恋过的、想念过的、依依不舍的人,明明知道他的存在,却同样命令自己刻意隐瞒。
甚至会订阅他所在城市的短信天气预报,却不敢提到他的名字不敢回忆他的容貌。知道那里的天气,是证明你感知到他曾存在的唯一线索。
一直以来都是最受照顾的那一个,人群中最温柔又本分的女孩,即使稍显胆怯也可以忽略不计,像只晃晃然的慢船。安静的心思中沉眠了太多“明知道”的航道,一切都可以凭借别人的帮助找到经验的范本,只需沿着那些方向行驶,无需有任何改变。
所以,才会失去。
从小到大连春游的乐趣都没有体会过的女生失去了多少该怎样计量?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因为医疗事故死亡,所以游离是绝不能出现任何意外的女儿。每当同班同学兴高采烈地挤在大巴士里集体出行时,母亲就会以病假的借口把游离领回家。而真正的失落会出现在春游归来的次日,同学们余兴未减地扎堆讨论昨天发生的趣事,游离被排除在每一个小圈子之外插不进话题。但是,久而久之,也会习惯。
习惯在兴奋的话题圈外无所谓地做自己该做的事。
习惯在别人过度的关怀和帮助下度过每一个日子。
即使和女生们玩在一起,也常常成为受到庇护的柔弱少女。理所应当地对做不到的事坦然放弃,因为--明知道自己做不到。
就这样波澜不惊地生活着。安然驶过日光喧嚣的午后和漆黑的深夜,哪怕平静的海面没有一分一毫的起伏,微风也能送船到港湾。
直到有一天,那个神情清淡的少年转向自己:“夜盲症?”
少女缓慢地眨眨眼睛,露出些许无可奈何的神色:“嗯。”
他的眼里就也染上一点无奈,然而却马上换出释然的笑来:“可是,你有没有尝试过努力去看呢?”
“欸?”
就像平地汹涌起一阵狂风。黄沙被舞得在视野里旋转成漏斗状,连接着天与地。
从来就没有人问过,自己也没有问过自己。
--你有没有尝试过努力呢?
也许,就是从此开始不同。可为什么后来刻意忘记?
游离不愿再想,用力地扯开被安放在一旁行李箱上的被子,捂住脸无声地哭起来。
为什么明明那么无奈却会重新想起?那个寂静落寞的冬天,那场肃杀无声的大雪,那个有一点无奈却有更多真实笑容的少年,那列仿佛永远开不到尽头的火车,以及那些封存在回忆中被上锁了泛黄了的言语。
军训过半,承训的教官们组织了一场盛大的拉练,去靶场打靶,十公里路步行来回。在城市里呆惯了的学生对十公里路没有感性的概念,以为是一场轻松的踏青。
学校的辅导员老师倒是没跟着头脑发热,晚点名时说了一通,大意是只要有一点点身体不适都别去。潜台词是别给大家添麻烦。
照惯例,游离肯定第一个报名缺席,但这次有点犹豫。反正被辅导员分配了任务,统计自己院系不去拉练的人数,所以就看情况吧。如果不去的人多就混在里面凑个数,如果少了就还是勉强去参加。把选择权推给别人,也是从小到大谙熟的心理。
结果是,即使游离反复强调着拉练的难度和艰苦,全院系还是没有一个人不去。将全勤的统计表上交的时候,特别想苦笑。这次是被逼上梁山了。
“唉,如果早知道十公里的路程这么长,昨天一定踊跃报名缺席。”刚随着大部队一阵狂奔才气喘吁吁停下来的敬亭转过头冲游离说道。
身后的女生面无表情:“如果早知道--这种假设还是最好不要提出,以免遭打。”
“我不来的话,游离一定也不会来吧?”
“哈?”为什么要用“一定”这个词?
“以前每次都是这样啊。就连课间休息的时候,如果我不去,你也从来不会去上厕所,宁可等到下一个课间。”
“是么?”其实自己也心知肚明。游离略带尴尬地看了敬亭几秒钟,突然兀自冒出一句,“……去哪里了?”
“啊?”怀疑是耳朵出问题漏听了什么,其实没想到是游离并没有说出来。
--我的勇气,去哪里了?
甚至连问出这个问题的勇气都不具备。
敬亭茫然地看着游离泄气的表情,险些撞上前面同学的背。转身往前才发现,因为火车就要来了,长得望不到头的拉练队伍终于在离自己不远的前方被截成两段。
停了下来。
之前走过的每个十字路口都因为教官会拦下两旁的汽车而畅通无阻没有停下过。
游离拧开水壶喝了口水,由于队伍停止,得到宝贵的休息时间,聒噪的女生们七嘴八舌起来。
班长站在铁轨上愣头愣脑地问连长:“要拦么?”
连长翻了翻白眼:“你拦得住你就拦。”
男孩知趣地退后几步远离了铁轨,女生们嘻嘻哈哈地笑起来。
队列里只有一个人不仅没笑,而且似乎紧张得脸色苍白。
游离捏紧了水壶,右手指甲不自觉地掐进左手食指,然后听见了远处传来火车的声音。
砰咚--砰咚--砰咚--
好像是非常缓慢,可是行至面前却分明是一边轰鸣一边急驰飞奔。
不可能拦住。不会为任何人停下。如果,你错过了的话。
十七岁时,游离第一次一个人出门远行,从北京坐火车去新疆探望身为军人的父亲,遇见了刚回家探完亲返回部队的京翔。那个把一点一滴每个细节都铭刻在游离记忆里的少年,就是因为这样的前提,坐在了她身边的位置。
倘若母亲没有请不到假,倘若游离没有早早放寒假,倘若父亲不是刚刚胃出血,那么,这段旅行就不会存在。也不可能听命运这样安排,与他这样相遇。
如果错过了,着实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砰咚--砰咚--砰咚--
火车驶来,火车驶去,每一分每一秒,月台上,车厢里,有无数人相遇、错过或分离。为什么,我遇见了你?
为什么,我遇见你,却又如同列车一般借着惯性朝原有的轨迹急驰而去?
据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排除时光倒流的可能性,他说你可以试试看超越光速。
据说天体黑洞、星核辐射都是超过相对论光速的。在辐射弯曲处携带的粒子,处于衰竭而成为自由落体,因此质量为零,时间为零。
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