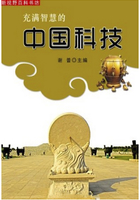更进一步,部分电视知识分子还要通过电视话语权力去推销自己的作品,倘若如真正的学者一样去分析自己的不足和局限性,他的作品在文化消费市场的受欢迎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那么在电视观众面前肯定自己的声音就多了些,自我批评的话语就留在非公开场合了。虽然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尤其是媒体常客们,言那么多怎么可能不失呢?但是,在这个话语囚笼里,电视知识分子只好硬着头皮自我表扬、漠视批评下去。所以,有学者说:"我本人是坚决反对学者成为学术明星的,因为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电视不像手中的笔,由不得自己,你在那里侃侃而谈的,只能是你既不想说,别人也不想听的话。人们反感学术明星,主要是这些,所以那些想为自己辩护的学术明星,我以为还是要虚心一些。在这点上,老百姓比我们清楚,你在一个不由你的地方谈话,不说假话才怪呢。"
2.同类肯定
如果把批评和赞成电视知识分子行为的人群划分为两大群体的话,可以发现与大规模文化生产场域联系紧密的知识分子坚决地站在了拥护者一方,尤其是电视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相互间的肯定更是经常出现的话语模式。
例如,身处大规模生产场域的陈丹青为电视知识分子辩解道:"中国知识分子动不动玩儿'清高',其实是世俗地位老弄不舒服,这才琢磨出来的花招,骂骂别人,骗骗自己,真清高的雅人,哪会去骂易先生,他家里可能根本不安电视机--想想孔夫子吧,道路颠簸,风尘仆仆,他老人家还俩手扶着车杠子,周游列国到处讲。孔子要是活到今天,绝对霸占电视台;胡适、鲁迅、陈独秀活到今天,坦然上电视。以易先生为代表的几个家伙,和春秋战国时代拿着竹简坐个牛车到处跑的古人,都是一回事情。当然,前提是勇敢,有关怀,有话说。这样的人如今太少了。"在这里,其显然混淆了易中天等与孔夫子、鲁迅等的区别,尤其是两者间的言说内容,以及前者是迎合后者是引领和启蒙的方式,对于社会的意义也许是完全不同的。更重要的是,陈先生还忘记了电视媒体的意识形态属性,面对只能按照它的模式进行宣讲,孔夫子等人的最大可能也许只是失语了吧。
另外,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电视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肯定,可以在电视节目和报端经常看到。如易中天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看了《百家讲坛》的《于丹〈论语〉心得》,不禁拍案叫绝。神闲气定,娓娓道来;古今中外,信手拈来。诚可谓妙趣天成,观之可以忘忧也!建议大家都去看看。"他用"于丹真棒"来抒发自己的万千感慨,然后又是在央视搞三人访谈(易中天、于丹、柴静),又是为于丹新书作序,一声感叹"好聪明的小妮子"发自内心、溢于言表,难以掩饰积蓄已久、恬淡深处的钦慕之情。又如在2007年3月11日央视《百家讲坛》的特殊节目中,易中天在与王立群交谈时说:"那我们就下我们的蛋,让别人说去吧。我们都是公鸡中的战斗机。"余秋雨在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时曾谈道:"易中天先生的历史讲述受到民众的欢迎,可以说是文化大众化的一个有益尝试。"
2005年9月19日,在凤凰卫视的资助下,李敖飞抵北京,展开为期12天的"神州文化之旅"。对于李敖此行,人们众说纷纭,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对李敖持批判立场的以学者为主,持支持立场的则以媒体知识分子为主。学者主要批评李敖在不同时代、不同场合的"变身",朱学勤、朱维铮、余杰、谢泳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不赞同拔高李敖此行的意义;媒体知识分子更为看重李敖在威权时代的"前身"以及此次在大陆的"现身说法" 。虽然媒体知识分子赞同的理由具有一定道理,不过,如果从同类肯定的角度,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看得更清楚些。
即使不得不要将自己和别人作出对比时,电视知识分子也十分注意言语分寸,尽量对两方都作出肯定。例如,前面提到的傅佩荣由于在凤凰卫视中经常推出国学讲座,而被人称为"台湾版于丹"。傅佩荣听了倒不以为意:"可以到台湾去问问,看大家怎么说我。做学问和谈心得完全是两回事情,她有她的贡献,我有我的作用。"
中国电视知识分子间的相互肯定已经不同于学术场域内部的某些类似于"圈内认可"的现象,是一种对电视权力撮合下的游戏规则的确认。一方面,电视知识分子人群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学术场域和电视场域的夹缝中生存,利益的一致导致认识方式的趋同,今天对你的认可,也就意味着明天你对我的肯定;另一方面,同处于大规模文化生产场域而又没有进入电视场的知识分子群体,也不会选择去批评拥有电视话语权、大众话语权的电视知识分子(除非为了快速成名或把自己的作品炒作为畅销书,即使类似于《余秋雨批判》之类的编者或作者也用的是笔名),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布尔迪厄所说的"互搭梯子"或同伙认可。
四、保守
无论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文死谏",还是西方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都强调知识分子话语的批判特征。但是,"古典的知识分子具有批判精神和个人主体意识张扬的特点,而媒体知识分子则具有谢绝批判和淡化自我意识的特点"。
在清华大学教学的加拿大学者贝淡宁在分析于丹现象时指出:"但是有必要关心一下于丹努力把《论语》去政治化的政治原因。她的阐释并非像表面上那样与政治毫无干系。通过告诉人们他们不应该抱怨太多,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关注内心幸福,弱化社会和政治承诺的重要性,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评性传统,于丹实际上转移了造成人们痛苦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以及导致人们生活巨大改善所需要的种种集体的解决办法。比如,如果我缺乏工作机会,我应该反思自己的失败而不是思考社会和经济结构及财产所有权模式。实际上,她倡导安于现状,其观点是保守的,支持保持现状的。孔子的在天之灵一定十分不安。"这里贝淡宁谈到的于丹的问题,也是中国电视知识分子话语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淡化意识形态、去批判化的保守模式。当然,这是一位外国学者从西方知识分子理念和视角来进行认识的结果。
为什么去批判色彩的保守特征会成为中国电视知识分子话语的常态,我们也应从现实的社会环境中来阐释:第一,媒体的官方意识形态色彩,使其中的知识分子只能在建设的意义上行使批评的话语权,这是一种对社会主义和谐舆论的建构,而不是解构或制造杂音;第二,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已经进入大学、科研机构等成为所谓的特殊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是一种服务型人才,他们的话语也自觉地带有为政治、经济等"保驾护航"的作用;第三,电视媒体的强大社会影响力促使电视知识分子在话语表达时,保持一种谨慎的心理状态,任何过于偏激的言行都可能被电视画面扩大化,他们也难以为所造成的负面后果负责;第四,在广大电视观众面前,他们采取的态度是迎合而不是挑战,为了被大众认可和肯定,必然要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意识和话语模式,那么就必须剔除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先锋、批评话语特性。
中国电视知识分子话语特征虽然存在着个体差异,但是其整体上的表现可以看作在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场、经济场、媒体场和知识分子场中形成的特殊话语模式,是一种权力和话语协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