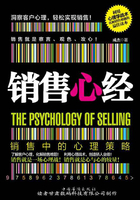第46章审判
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法兰西共和国成立第二年的正月23日,即当时人们说的旧历1793年10月14日的那一天,一群好奇的人在大清早便涌进审判大厅,革命法庭将在那里开庭。
大厅的走廓,附属监狱的巷道内挤满了好奇心切的听众,他们互相传递信息和感染情绪,就如波浪的泡哮声与泡沫不分先后,混为一体一般。
虽说好奇心使每一个观众激动不已,甚至也许就因为这种好奇心的驱使,人海里的每一个波涛在两个堤坝之间动荡、拥挤,外面的障碍把他们往里挤,里面的障碍又把他们往外推,然而在潮涨潮落之中,每个波浪大体上还是保持在原位上。因此,占据好位者很快就明白该让他人默认自己的好运;为平衡情绪,他们就向占位欠佳者传递他们看见和听见的信息,这些人又把原话传给了其他人。
在法庭门口,一群人挤轧着,他们在激烈争夺十平方的空间,因为宽一点则能越过一个脑袋俯瞰整个大厅,以及被告的面容。
不幸的是,这条从走廊到大厅的通道太窄小了,一个男人的宽肩和弯成弓形的肘几乎把它全占了,他挡住了晃动的人群,如果这个血肉壁垒抵挡不住,那么整个人群就会坍倒在大厅里了。
挡在法庭门口的这个不可动摇的人既年轻又漂亮,人群撞击着他,一次比一次猛烈,他每次只是甩了甩厚松松的、像狮鬃一般的秀发,秀发下闪烁着忧郁而坚定的目光。他像一个活的堤坝用眼神和身体阻挡住听众一次次的冲击,挡住了人潮,同时他又聚精会神地在专注着什么。
有好多好多次,密集的人群见他身材高大,自己不可能顺利通过,便试图撞倒他。不过,正如我们所说,他像岩石一般坚定,不可动摇。
在人海的另一头,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还有另一个男子汉正凶猛地一个劲地为自己打开一条通路,他逐渐移近,那些被他撇在后面的人的拳头、被他挤压的人的咒骂声以及妇女的呼喊声,都阻挡不了他,值得提一句的是,在人群中有许多女人。
他以拳头对付拳头,以凶狠狠的目光对付咒骂,在他的逼视下,再勇敢的人也会退避三舍;而对那些大呼小喊的人,他则不理不睬,近乎于蔑视了。
他终于移到了那个堵住大厅门口的强壮有力的年轻人后面。每个人都想看看在这两个粗野的对峙之间会发生什么,于是怀着很大的兴趣等待着。我们说,就在人们热切地等待之中,后来者又用他一套老办法,即在两个听众之间像楔子那样用臂肘插进去,然后用身体当劈刀劈开紧紧挨在一起的躯体。
这个人是一个矮个儿小伙子,脸色苍白,四肢瘦小,这说明他的身体很虚弱,然而他那对炽热的眼睛则蕴含着坚强的意志。
他的臂肘刚刚擦到前面那个年轻人的胁部时,那个人对这次侵袭十分惊讶,飞快地转过脸去,举起拳头,正想落下去打扁这个胆大妄为者。
这两个对峙者面对面站着,继而同时惊呼了一声。
原来他们彼此认识。
“啊!莫里斯公民,”瘦弱的年轻人以难以形容的痛苦声调说道,“请让我过去吧,让我看看;我求您了!以后,您再把我杀掉!”
此人果然是莫里斯,他被对方永恒的忠诚和不可摧毁的意志所感动,感到由衷的钦佩。
“是您!”他低声说道,“您在这里,好不谨慎!”
“是的,是我在这里!可我已经用尽力气了……啊!我的天主啊!她说话了!让我看看她!让我听她说!”
莫里斯闪开,小伙子从他面前走过去,由于莫里斯站在人群的最前面,于是挨了那么多拳头和谩骂才到达的小个儿便一览无余了。
这一幕以及由此引起的絮叨声引起了审判官们的注意。被告也向这边看,她看见并认出站在第一排中的骑士。王后坐在铁椅上,刹那间,她全身哆嗦了一下。
庭审由庭长阿尔芒主持,公诉人是富纪埃-坦维尔,辩护人是王后的律师肖伏-拉加尔特;整个审讯一直延续到审判官和被告体力不支为止。
在整个这段时间里,莫里斯在原位没挪动一步,然而在大厅和走廊上的听众已一批又换了一批。
骑士靠在一根廊柱上,他的脸色与他倚靠的大理石一般苍白。
沉沉的黑夜替代了白昼,法官的桌子上点燃了几根蜡烛,大厅壁上的几盏灯在冒烟,昏暗泛红的弱光照着王后那张高贵的脸庞,往昔,凡尔赛宫节中的灯火熠熠生辉,她那时是多么美丽动人啊。
她孤单单地坐着,对庭长的审问简洁而随意地回答几句,时不时地也倾下身子向她的辩护人耳语一阵。
她那张白皙光滑的颜面丝毫未失去往日的傲气,她仍穿着那条黑色条纹的裙袍,自国王死后,她一直穿着它。
审判官起立,退庭讨论;庭审结束了。
“我是否显得过于轻蔑了,先生?”她向肖伏-拉加尔特问道。
“哦!夫人,”那人答道,“您保持本色时,总是非常得体的。”
“瞧,她是多么高傲啊!”听众席上一个妇人大声说道,仿佛她在回答王后向她的律师提出的问题似的。
王后向这个妇人转过脸去。
“嗯,是的,”妇人接着说道,“我说你高傲来着,安托瓦内特,正是你的高傲把你给毁了。”
王后的脸泛红了。
骑士转过头去看说这话的妇人,轻声提醒道:
“她曾经是王后。”
莫里斯抓住他的手腕。
“行啦,”他对骑士说道,“克制些,别毁了自己。”
“啊!莫里斯先生,”骑士说道,“您是一条好汉,您知道您是在与另一条好汉说话。哦!请告诉我,您认为他们会定她死罪么?”
“我不认为,”莫里斯说道,“我敢肯定。”
“啊!是一个女人啊!”红屋骑士呜咽着大声说道。
“不,一位王后,”莫里斯纠正道,“您刚才是这么说的。”
这回,骑士抓住了莫里斯的手腕,并且以超乎寻常的力量,逼使他向自己俯下身子。
时间已到凌晨三点半,观众已很稀少。四处有些灯火已经熄灭,大厅的一些角落已黯淡下来。
骑士和莫里斯所站的地方是最阴暗的,莫里斯想听听骑士要说什么。
“为什么您来这里,来干嘛?”骑士说道,“您,先生,您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吗?”
“唉!”莫里斯说道,“我来这里想知道一个不幸的女人现在怎样了。”
“是的,是的,是那个被丈夫推进王后监牢里的女人吧?是在我眼皮底下被捕的那个女人吧?”
“热纳维也芙?”
“对,热纳维也芙。”
“这么说,热纳维也芙已成了囚犯,是她丈夫出卖了她,把她杀了?……啊!现在,我什么都明白了,明白了。骑士,请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告诉我她在哪儿;告诉我,我到哪儿能找到她,骑士……这个女人是我生命的全部,您听明白了吗?”
“嗨,我看见她了;她被捕时我在场。我当时也是去劫救王后的。可是,我们两个计划事前没有通气,结果非但没有互补,而是互毁了。”
“但您没去救她,救您那热纳维也芙妹妹?”
“可能吗?我们之间隔着一道铁栅栏。唉!假如当时您在场,假如您我拼足力气,那可诅咒的栅栏就会断开,我们便可以把这两个女人都救出来了。”
“热纳维也芙,热纳维也芙!”莫里斯喃喃道。
接着,他带着难以言述的狂怒表情问道:
“迪克斯梅呢,他怎样了?”
“我不知道。我们各自逃脱了。”
“哼!”莫里斯咬紧牙关说道,“假如我有一天碰到他……”
“嗯,我能理解!不过,救热纳维也芙并不是没有希望,”红屋骑士说道,“而在这里,对王后来说……啊!听着,莫里斯,您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强有力的人;您有许多朋友……啊!我求求您了,如同我向天主祈祷一般……莫里斯,帮助我救出王后吧。”
“你觉得可行么。?”
“莫里斯,热纳维也芙也会这样恳求的。”
“哦!请您别说出这个名字,先生。谁能知道您不像迪克斯梅那样把这个不幸的女人抛出去。”
“先生,”红屋骑士自豪地答道,“倘若我忠于一个事业,我只会牺牲我自己。”
还没等莫里斯作答,辩论大厅的门已重新打开。
“别出声,先生,”骑士说道,“别出声!审判官回来了。”
红屋骑士面色发白,身体晃动不止,莫里斯感觉到他放在他胳膊上的手也在颤抖。
“啊!”骑士喃喃道,“啊!我的心停止跳动了。”
“坚强些,控制住自己,否则您就完了!”莫里斯说道。
庭审人员各就各位,宣判的消息在各个过道和走廊上不胫自走。
人群又蜂拥着涌进大厅,灯火在这庄严的决定性时刻仿佛又重放光芒。
王后又被带上来,她的腰板挺直,一动不动,神态高傲,目不斜视,双唇紧抿着。
有人向她宣布判决书,定她死罪。
她听着,神色镇定,泰然自若,面庞没有表现出任何沮丧的神情。
接着,她向骑士掉过脸,向他送去一个意味深长的目光,仿佛向这个她从未谋面,而对她却像岩石一般忠诚的人表示感谢似的;然后,她依傍着指挥法警的胳膊,安详而端庄地离开了法庭。
莫里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感谢天主!”他说道,“在她的供词里没有一句牵连热纳维也芙的,还有希望。”
“感谢天主!”红屋骑士喃喃说道,“一切都完了,斗争结束了。我也精疲力竭了。”
“坚强些,先生!”莫里斯轻声说道。
“我会的,先生。”骑士答道。
这两个人握了握手分别向两个门口走去。
王后又被带回到附属监狱,她进去时,报时大钟敲了四点。
在新桥上,莫里斯被洛兰的两个胳膊拦住了。
“停住,”他说道,“别走了。”
“为什么?”
“首先你上哪儿?”
“我回家。我现在可以回家了,因为我知道了她的下落。”
“好极了,不过您回不去了。”
“为什么?”
“因为在两小时之前,宪兵上门来抓你。”
“哦!”莫里斯大声说道,“好嘛,我更该回家了。”
“你疯了吗?热纳维也芙怎么办?”
“言之有理。现在我们去哪儿?”
“当然去我家啦!”
“但我会连累你。”
“那就更该去啦;走吧,来吧。”
说着,他把莫里斯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