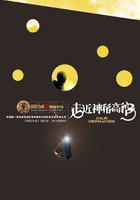多谢了,南老!
南老是我最敬重的一位东方文化大师,儒、道、释无不通达,着作等身。于佛学,尤有独到之心得。
还是那句话,灭高人有罪。
南先生的可贵之处,并不止于他是东方文化的通家,而且是一位身体力行者。这就使他与大量学者型的东方文化通家们大不一样。
学者们的书,妙也是妙,但大半有隔靴搔痒之嫌,大本大本读完了他们的书,却如何也找不到一个人生入手处,似乎是谈天说梦。
我以为,东方文化的根本处,恰不在于其体系的博大,哲理的精妙,真正的妙处在于他总是很恳切地给你一个人生入手处。
南老的书总是力求做到这一点,解经说法无不落于实处。读他的着作、文章,恰如同看见了他一生的为学为人。这是一切热爱东方文化的人都应好好学习的。
南老的《金刚经说什么?》开宗明义第一节的标题便是(佛学)是“超越宗教的大智慧”。这对于一切还迷恋在迷信中的学佛人不啻是一声警钟。在我见到的学佛人中,不管是出于迷信,出于气功,出于好奇,出于做学问……其内心深处,总是或多或少地认为,在我们世间人生活之外,还有一个我们无法认识却又左右着我们的神秘的彼岸世界,尤其是一些出于宗教目的学佛的人最严重。捧佛经览佛相,无不是战战兢兢,似乎稍有冒犯,便永世不得超生。佛,于他们不是慈悲而是恐怖。
这种迷信意识,深入中国人心太久、太久,几乎成了一种痼疾。
我的友人贾平凹写了一本《废都》。内中孟云房的故事,几乎是照搬了一九八五——一九九二年我的全部生活情节。正如《废都》所写,那时的我真如一只没头苍蝇,到处乱碰。算命先生、气功师、和尚、尼姑、道人、巫婆……全是我家的座上客。对于这些人我从来是恭而敬之,对于他们的说法,我是理解的也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若以一般人看来,我真是一个迷信头子。平凹与西安的一些文人朋友都嘲笑我,平凹在他的《废都》中对我极尽嘲讽之能事。
其实,我并不是太信任这些江湖客,不过在没有明白他们的来龙去脉和他们满口所说的佛学、道学的来龙去脉之前,我决不轻易否定他们,我要把他们教我的东西放在我的生活实践中去检验检验。我宁可人们说我迷信。我在实践这些江湖客的指导时,坚持不怀疑、不折扣、不思考,一切有令必行。愚昧,非是自己愚昧过了之后,才会知道人为什么会愚昧。
愚昧总有愚昧的合理性,不然就无从说起还有什么愚昧。愚昧自有其合理的因缘。
在如是人中,我以为平凹还算是真有几分神通的。他在《废都》的结尾处, 说我瞎了一只眼,这大概是隐喻我有眼无珠,上了江湖客的当。书中同时又说我与儿子一起去云游天下了。其实在他写《废都》时,我还没有出家的愿望,而在《废都》出版之后,我确实是与儿子一起出家为僧了。
多年来,我们一头扎在东方文化中,却终是未沉沦为一个迷信的宗教徒,这是应该感谢南老的。
我接触南老的作品还是八十年代的事。《废都》中写到我与一位比丘尼交好,这是实有其事。不过这个尼姑的形象,后来被平凹作了大大的变形,这完全是他创作的需要,和我认识的那位比丘尼毫无关系。我认识的这位比丘尼至今还严持戒律,痴心不改。平凹对这个人的变形不无道理。一个宗教徒若真能如平凹说的那样“潇洒走一回”,东方文化的改造便太容易了。平凹笔下的那种尼姑,在我的生活中几乎是找不到的。
平凹不太了解真正宗教徒的虔诚。
但我以为这“虔诚”中包含了一层更深的悲剧,也未必合于释迦的初衷。就是这位比丘尼给我送来了大量的台湾佛学杂志,那上面多有南老“禅学讲座”刊登。初得南老着作,我欣喜若狂,如饮醍醐。南老比我接触的那些江湖客高明得太多了。
我以为我此时的心情是当代许多学佛人共有的。不少人到如今还对我说,他们唯一尊重的人便是南老。
现在回忆起来,八十年代的东方文化实在是极有意思的,各种奇说异论漫天翻滚,各类“神功”、“神说”如雨后茅草。一夜之间,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蹦出无数的神仙、佛子、仙姑……比今天的歌星影星还名噪一时,时至今日还有人在鼓噪不休。
我们中国有多少人作过气功热的追星族?
我不敢想象,当时的世间若没有南怀瑾先生等明眼人的着作问世,我们这些追星族真不知会闹多大的笑话。
出家了,不少师傅们告诉我,南怀瑾是“外道”,是“魔头”。还告诉我一则故事:说南老在南方某名寺主持禅七,参加禅七的皆大陆名宿,享誉一方的“禅合子”。其中有位高僧愤然离席扬长而去。他回寺后命他所有弟子一定要把南怀瑾的着作全行销毁。其原因是,南老在主持禅七时在禅堂抽烟了!
我对这位高僧该说什么?
我更敬佩南老了。
出家多年,高僧见过不少,然而令我不敢恭维者更多,更多……许多僧人……我不说了,免得有谤僧之罪。但是,心中怎么能没自己一本账呢?我毕竟是个活人。
我还是没有抛弃南老的着作。
在寺庙里,我还是按一名僧人该做的都做了。戒酒、戒烟、念佛、行脚、乞讨、闭关,一天磕上千个头等等,我做了,比一般的僧人做得不差。
但还是读南老的书。
还是我当年对待那些江湖客的态度,先按他们说的做下去,虔虔诚诚地做,老老实实地做,绝不先怀疑。
这也不妨碍我一本本地读南老的着作。
我以为我一生有一个最好的习惯:我没有完全弄明白的事,绝不简单地事先否定。虽然为此我吃尽了苦,但心里很踏实。我以为一个人真想搞懂点什么?总该是这样才好,死了也是明白鬼。
还是那句话,愚昧怕什么?怕的是不知愚昧为何物,不知愚昧起自何种因缘。这得先尝尝“愚昧”的滋味才行。
我不知是我多年的愚行起了作用, 还是南老的作品起了作用, 或是我诵《金刚经》多年起了作用。
我诵《金刚经》到底有多少遍,不记得了,反正是极熟的。我曾逼着我九岁的儿子背《金刚经》。他早已熟诵如流了,而且是一背就是八年。时至今日,我们很庆幸,没有完全陷入迷信的泥坑,是不是真的走出来了?不知道,起码是开始可怜那些还在迷信彼岸的神灵的人们了。
我以为这便是我们诵《金刚经》得到的“感应”吧?
我以为,为求感应而诵《金刚经》,怕是难有感应的;即便有了,也未必是合《金刚经》之理的。 不求感应而诵《金刚经》, 怕是真会有感应的,只要你不把“感应”神奇化便好。你懂了《金刚经》的道理,哪怕只是字面上的道理,不也是一种“感应”吗?
所以,我欣赏南老《金刚经说什么?》一书开宗明义第一节的标题,(佛学)是“超越宗教的大智慧”。
我记得我第一次悟到“佛”之一字的本义的时候,浑身的汗毛孔都炸起来了,满身的鸡皮疙瘩两天也未消下去。
什么是佛?当时什么也说不清,只是恐怖一切全没有了,这是“空”吗?不知道,我还活着,一切全没空,只是觉得这世界、这人生,尤其是“死”后,什么也没有了。转世、轮回……功、罪、善、恶、美、丑……全是一场笑话……什么也找不着了。什么成仙,成佛,全是废话。
不过,我劝一切学习东方文化的人,一切学佛学的人,莫作神秘想,莫作神奇想,这是很实在、很实在的心理感受。一种很有意思的“知”。
这一切怕是要多谢南老的着作的。但是,佛学并不在这里止步。一念空、念念空都不是佛学的最后归宿。佛学的真正归宿,还在这个繁华似锦的人间,除了这个人间,除了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历史,“宇宙—生命”大系统的流程, 佛学什么也不关心。——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
我们从这里展开我们对《金刚经》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