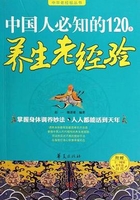对中国了解越深,斯诺对中国的感情也就越深,他曾在1931年的日记中写道:“今后,我必须重新适应美国的生活。然而,无论适应得有多好,我的青春,生命中最好的年华,毕竟留在了东方。青春应该充满富有挑战性的探险,激动人心的经历和不寻常的刺激。”
但同时,在中国的斯诺也越来越绝望。本来,他只不过是一个喜欢冒险的年轻人,并不准备在这里久留。选择中国,也不过是因为渴望到世界上最遥远而渺无人迹的地方去寻求新奇和刺激。但是,在上海以及后来在萨拉齐灾区等地的见闻,让这个活泼、开朗、浪漫的年轻人,变得心事重重而又老练成熟。
“可怜的中国,它的悲剧简直看不到头!”1932年初,斯诺在写给父亲的新年信件中说。
斯诺、蒋介石与毛泽东
如果孙中山能够活到现在,“他肯定早就和现在的政府公开决裂了”。
本来,斯诺曾是国民政府的座上宾,他所乘坐的VIP车厢即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这位没有带任何政治目的、偶然来到中国的美国年轻人,拥有一个坚定反对日本侵略、支持国民党的老板——《密勒氏评论报》主编和发行人鲍威尔(John Bill Powell)。在鲍威尔眼中,孙中山的民族解放事业非常伟大,而蒋介石的南京政权则预示着“新中国”的诞生。
南京方面自然对这位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洋报人予以高度的评价和热情的支持。当时在上海英文报纸《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Post and Mercury)任编辑的兰德尔·古尔德曾透露,20世纪30年代,南京政府是《密勒氏评论报》的大客户,每期大批购进,寄往海内外。
在经验丰富、业务娴熟而又诚实正直的鲍威尔影响下,斯诺也成为“亲华派”,支持国民政府,认为它能带领中国人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由于《密勒氏评论报》与南京当局的特殊关系,在这家报社供职的斯诺也获得了令其他记者羡慕的机会。1928年10月,他到南京采访,见到了蒋介石及其他高官。那时,他还没有想到,八年之后,自己将获得另一个足以令其他记者嫉妒至死的机会,采访蒋介石的终生对手——毛泽东。
第二年,斯诺又获得了一次千载难逢的采访机会——也就是本部分开头所提及的,促成他与路易·艾黎首次相遇的铁路沿线采访。
这次采访对斯诺的触动很大。随着对中国的了解渐趋深入,斯诺不再信任国民政府,也彻底放弃了对国民党及其领导人蒋介石的幻想。那位陪伴斯诺旅行、拒绝艾黎共同乘坐VIP车厢的交通部胡姓官员即是南京当局腐败昏庸的一个例证。他凭借裙带关系谋得职位,对铁路事物一窍不通,但却傲慢自大,认为当官的职责就是吃喝玩乐、养尊处优。
深入中国内地,目睹了官员与百姓生活的巨大差异之后,斯诺对国民党的态度发生了逆转。在写给父亲的信中,他甚至对蒋介石能够继续执政感到惊讶。在他看来,蒋介石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缺乏人格魅力,目光短浅,无恶不作”。这位不称职的领导人之所以还能够掌权,是因为他的敌人没有同心协力地反对他。
他日记中记载的这样一件事充分显示了他的失望——有个准备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美国人,和中国人一起讨论在哪里修铁路。
但是,他提出的每一个地点都遭到了否决,因为他所提到的地方,不是俄国、日本的“势力范围”,就是法国、英国的“势力范围”。最后,他勃然大怒道:“那么,中国究竟在什么地方?”
不过,斯诺和鲍威尔并未因为对国民党的不同态度而决裂。他认为,自己和鲍威尔依然有相当多的共同之处,都出生于美国中西部,都同情和支持中国人的民族解放事业。
两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都推崇孙中山。但不同之处在于,斯诺认为,蒋介石掌权的国民党已经违背了孙中山的主张,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狂热的个人崇拜——这种反感或许是斯诺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天性使然,很多年后,他也跟后来手握大权的毛泽东谈论过“个人崇拜”的话题。此乃后话。
当时,斯诺还认为,孙中山的“训政”思想被蒋介石政府用做挡箭牌,以避免真正实行宪政民主。
“谁能领导政府,领导人民,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其他军阀知道什么是民主政府吗?我想他们不知道。”胡适的这段话深得斯诺之心。
在广州——那里曾是孙中山革命的大本营——目睹国民政府统治下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状况之后,斯诺沉思,如果孙中山能够活到现在,“他肯定早就和现在的政府公开决裂了”。
实际上,对国民党从寄予希望到彻底失望,正是不少“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们的共同特征。也正因为此,他们转而关注在当时还相当弱小的共产党,并将希望寄托在这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力量身上。
甚至,当1937年2月中旬至7月中旬,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林伯渠等人代表共产党与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蒋介石、宋子文、顾祝同等人进行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准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斯诺还曾私下里担心共产党“准备投降”。
见证国民政府的腐败
“你是一个外国人,你永远不可能了解中国。中国一向喜欢闹洪水,而且还要一直闹下去。你看,中国人这么多,淹死一些不要紧。”
国民政府的腐败生生将许多支持者和中立者推向了它的对立面。
1932年末,路易·艾黎认识了比他大5岁的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艾黎称她为“天生的鼓动家”。史沫特莱的性格从她的衣着就可以看出一二:“你要是见到她,无论在盛夏或严冬,她的穿戴都离不了一点红色——深蓝衣服上的一朵康乃馨,帽子上的一只红鸟,红色的运动衫。这似乎是艾格妮丝的颜色,她格外喜爱这颜色。”艾黎曾如此描写。
不过,艾黎和史沫特莱刚相识的那会儿,艾黎也没少用自己的所见所闻来“鼓动”史沫特莱。
认识史沫特莱之前,艾黎曾在遭受洪水灾害的湖北省参与赈灾修堤工作。在那里,他亲眼见证了国民政府的腐败。艾黎曾要求一位基层官员带自己去看他所负责的堤坝,但这位官员甚至在下属的协助下都找不到堤在哪里。
腐败已经到了根子里,国民政府的官员们对民众的生死漠不关心,官民矛盾十分严重。艾黎清楚地记得,当洪水冲决谌家矶的堤坝时,国民党的省主席正同一些朋友在电力公司经理家吃饭和赌博。“当他们听说决堤的消息后,只是笑笑,说还有铁路的路基可以挡水嘛,接着继续玩乐。”
愤怒的艾黎曾向负责赈灾的领导人何键反映问题,要求他协助制止贪腐现象,但他的反应很冷漠。“你是一个外国人,你永远不可能了解中国。中国一向喜欢闹洪水,而且还要一直闹下去。你看,中国人这么多,淹死一些不要紧。”何对艾黎说。
当然,国民党当局并非全然不关心灾情,但他们关心的点令人心寒。
对于基层政府而言,他们关心的是怎样依靠水灾捞钱,怎样虚报救灾预算再将大部分款项鲸吞。
对于高层而言,他们关心的是怎样在已经建立了共产党政权的洪湖地区与之作战。何键甚至亲口对艾黎说:当前的主要问题不是赈灾、修堤之类,而是维稳——“如何镇压共产党,拥护蒋委员长,扩充军队,使国家安全,好让全世界的人都来这里做生意。”
“我知道在城里较穷地方的居民中,一定有共产党,所以,我的士兵把他们统统赶进阴沟里,像老鼠一样把他们杀死。”何键向艾黎描述他领导的镇压活动,“当然,有些好人也和坏人一起被杀了,但我们这里干得彻底,把他们一网打尽了。”
艾黎愤而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史沫特莱,还带她去参观了上海“模范租界”里的血汗工厂。
耳濡目染之下,史沫特莱看到了中国社会内部的严重不公。1930年4月,她在给老朋友的一封信件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我现在是为一种思想活着,这比什么都令我吃惊。我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了,越来越理智化了……在这里我每天工作18小时,即使不干活,也不得安宁,因为亚洲的贫困……从四面八方向你扑来……有一小撮阔绰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就同难以描述的近在他窗下的贫穷毗邻而居——许多国家的大战舰 在江中停泊,许多国家的持枪的士兵和水兵‘保卫’着一小撮最富裕的外国人。这儿,有阔绰又有贫穷,还有一个干间谍的、搞暗杀的、搞拐骗的、处死理想主义的以及干其他各种罪恶勾当的庞大的网。……我总想在我死去以前,我一定要再写一本书——多少年以后我将在书中揭露资本主义制度,连同从它发展出来的帝国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它怎样把人变成了狼。只有已变成了狼的非人动物才会愿意让这个制度永存下去,正是这个使亚洲落到了今天的地步。”
艾黎对史沫特莱说,他对旧制度下进行改革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只有根本的变革才是唯一的出路。
这番话令史沫特莱十分激动,她的一双大眼睛紧紧盯着艾黎,然后倾过身来抓住他的手腕。
“那就让我们投身到这场变革中去吧!”史沫特莱说。
这位鼓动家的鼓动显然奏效了。之后,他们都义无反顾地加入了这场变革,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其实,在那个时候,艾黎已经思考成熟,史沫特莱的鼓动想不成功都不太可能。通过与共产党及马克思学说的几次接触,他已经被深深吸引。
也是那一次在湖北洪湖的赈灾过程中,艾黎第一次见识了共产党人的“洪湖精神”。他看到,在红军领袖贺龙的领导下,人民正奋力重筑大堤,以免武汉再遭洪水淹没——而这正是国民政府的官员们不屑于去干的事情。
“一幅鼓舞动人的画面在我面前,男女老少在被洪水冲毁的旧堤废墟上努力修建新堤,工程进度之快是我从没见过的。”艾黎被眼前的场景深深触动。尤其是与国民政府的昏庸腐败对比之下,更衬托出共产党人的高大。天生亲近底层民众的艾黎觉得,只有共产党人才是真的和广大民众在一起。
爱憎分明的艾黎决定支持洪湖人民的救灾行动,他不顾南京方面的阻挠,冒险亲自运送大批救灾物资到洪湖革命根据地。
直到31年后,贺龙与艾黎再次见面时,还再三感谢他当年的“雪中送炭”。
洪湖人民也为之写下歌谣:
辛未洪湖闹水荒,艾黎送来衣和粮,腥风血雨同舟济,红缨所向势无挡。
来自西方的革命者
亲近马克思主义,并亲近声称要在中国传播、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便成为水到渠成的选择。
“逮捕、拷打、监禁和处死的厄运,威胁着每一个人,他们从浅粉色到深红色,即从普通老百姓到真正的共产党员。”
这段话出自斯诺1935年发表的一篇严厉抨击国民党政权“***化”的文章,他生动地描述了红色在中国的土地上蔓延开来的一项重要原因。
对那些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来到中国的老朋友们而言,他们中的大多数虽然不至于被逮捕、拷打、监禁、处死,但他们的所见所闻,依然令国民政府渐渐失去吸引力。与此同时,许多人接触到了正暗流涌动的红色浪潮。
1932年圣诞节,埃德加·斯诺和第一任夫人海伦·斯诺结婚。当时,海伦的工作是给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埃德温·S·克宁翰当私人秘书。她热衷旅行和写作,乘船蜜月旅行时,这对新婚夫妇轮流读书给对方听,他们随身携带着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和剧作家萧伯纳的不少书——前者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自称“从学生时代起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后者曾认真研读过《资本 论》,公开声言自己“是一个普通的无产者”,“一个社会主义者”。
不过,他们对于这两位同属“费边社”(Fabian Society)成员的作家提出的观点却不尽认同。费边社是19世纪末出现在英国的一个社会主义派别,主张务实的社会建设,倡导建立互助互爱的社会服务,通过渐进温和的改良主义方式来走向社会主义,而非通过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阶级革命,并强调通过教育的途径让权力回到知识精英的手中。
“我们认为,那是典型的英国方式,进展太缓慢了,就像12月份的冷糖浆。”海伦评价说。
于是,亲近马克思主义,并亲近声称要在中国传播、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便成为水到渠成的选择。
另一些外国人的思想也正逐渐从“浅粉”变成“深红”。
路易·艾黎是在1929年接触到马克思和列宁的着作的。理论的滋养,再加上他在工作中对工人悲惨命运的所见所闻,使得他越来越相信旧的世界制度的罪恶——所谓“旧的世界制度”,就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是一个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
后来,志同道合的外国人们开始聚在一起讨论政治。聚会的发起者是德国人海因茨·希普,《太平洋事务》
杂志的撰稿人。参加者还包括“鼓动家”史沫特莱、奥地利女青年鲁斯·韦斯(中文名“魏璐诗”)、英籍电气工程师亚力克·坎普林(中文名“甘普霖”)、左翼时代精神书店的荷兰籍经理艾琳·魏德迈等等。
参与讨论的还有一位名为乔治·海德姆的美国医生,他在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听说上海流行一种疫病,就跨越重洋来到中国开设诊所。但他到 了上海才知道,这里并没有发生什么“东方热病”,只是因为天热,有些人生了皮肤病而已。这种病也并不像他之前担心的那样可怕。不过,海德姆发现当时上海的性工作者特别多,性病一度泛滥成灾,因此他决定把性病作为那一时期研究的主要疾病,并给予了很多人免费的治疗。
后来,海德姆的诊所还为地下工作者提供了许多方便。
乔治·海德姆另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马海德。1937年,他跟随周恩来到宁夏工作,看当地大多数回族兄弟姓马,便依此取了自己的中文名。
“我们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和《雇佣劳动与资本》等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以及其他关于剩余价值学说、土地所有制问题、社会发展史、亚细亚社会革命道路的论述。我们讨论中国及国外时事,特别是上海的形势。这类聚会,根据各成员的意见,不定期地在不同地点举行。每当使用史沫特莱在法租界的小套房时,我们就找另一个人进入伯尔尼公寓,先上屋顶,再下楼梯进屋。她完全相信她家的大门是被人监视的。有时,也使用其他人不大知道的房子。”艾黎在自传中回忆说。
必须指出的是,这群人并不是彼时在华外国人的主流,大多数人将“亲华”“亲共”视为贬义词,甚至有《赤祸》这样的册子在流传——这也是为什么这批老朋友被中共如此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海伦·斯诺就曾遭到警告:“你可千万不要同斯诺这样的人来往,他是亲华分子。”斯诺还上了日本人开列的外国记者“黑名单”。不过,这并没有吓倒海伦。
这个圈子的外国人还有一位德国朋友叫王安娜。她的本名是安娜·利泽,因为嫁给了赴德留学的共产党员王炳南而改姓王。王安娜是柏林大学的博士,精通德语、英语和法语,在 校期间就积极参加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两次被捕入狱,与王炳南志同道合,并于1936年随丈夫来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