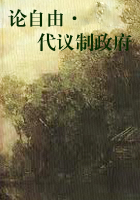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来到中国。
他们结识了中国人,接触了中国共产党,并且站在了当时还很弱小的红色力量这一边——这成为他们后来被称为的主要缘由。
这份友谊伴随着共产党的成长壮大,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
这份理想指向一个独立、民主、没有腐败、没有压迫的新中国。
站台的一次偶然相逢
两人都没有想到,日后他们会因为中国而结为毕生的忠诚朋友和合作伙伴,并且被赋予一个相同的重要称呼——“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不过显然,在他们相逢的1929年夏天,这两位“老朋友”还是两个世界里的人。
1929年6月,张家口。
一列火车正从这座位于河北西北部的城市缓缓驶出,一路向西,沿平绥铁路开往绥远的萨拉齐。
乘坐这趟火车是件苦差事。连年的军阀混战导致民生凋敝,人们营养不良,就连火车也跑不动了——因为机车和车厢保养不善,行驶速度极慢。从北京到张家口短短200公里的距离,竟花了一天一夜。从张家口开出后,前方的旅程还有三个昼夜。
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这趟火车虽然是载人的客车,用的却是无顶的货车车厢,旅客们都坐在地板上。途中不巧遇上大暴雨,盖在车顶的破篷 布完全无法抵御雨水的入侵,车厢内又湿又闷,拥挤而肮脏。
这些车厢就像是彼时中国的一幅缩影——潦倒破败的环境中挤满了饥肠辘辘的穷人,正驶向一个目的地,但速度极其缓慢,叫人看不到希望。
中国的西北部更是如同人间地狱,天灾频仍,人祸不断,连年的旱灾导致的饥馑已经夺去了不少人的生命,而已经成为家常便饭的土匪抢劫、军阀混战、税吏横征暴敛、地主巧取豪夺更让人失去最后的希望。在列车行驶的目的地绥远,1929年开始的一场大饥荒正吞噬着200万条生命。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生活得如此不堪。这趟火车驶离张家口时,挂上了一节环境舒适、设备齐全的专用车厢,里面只坐了两个人。用今天的话来说,那是一节“VIP车厢”。
这趟同时挂着最破旧车厢和最豪华车厢的列车在铁道上走走停停。如此怪异的情景,也好似贫富差距惊人的中国。
火车在一个小站长时间停车时,破旧车厢里的旅客纷纷下车透气。32岁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随人流走向站台,他想下车吹干自己被雨水淋湿的衣服——那皱巴巴、湿乎乎的卡其衬衫和短裤让他看起来狼狈不堪。
24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也下了车。站台上的人群中,他完全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异类,这不光因为他是外国人,更因为他乘坐的是那节VIP车厢,因此衣物十分整洁服帖,神情也与那群愁苦的以农民为主的旅客全然不同。
两位外国人都发现了对方,走到一起寒暄起来。
这是艾黎与斯诺的第一次见面,但他们只匆匆交谈了几句。两人都没有想到,日后他们会因为中国而结为毕生的忠诚朋友和合作伙伴,并且被赋予一个相同的重要称呼——。
不过显然,在他们相逢的1929年夏天,这两位“老朋友”还是两个世界里的人。
当时,斯诺的身份是《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的助理编辑和记者,这份报纸由美国人在上海创办,读者包括在华外侨和海外关心中国的外国人,影响力颇大。南京国民政府的交通部邀请斯诺在中国铁路沿线进行旅行采访,通过他的报道宣传中国的旅游,让西方人相信到中国旅游是可行、安全和舒适的。
不论这样的宣传是否属实,起码,斯诺的铁路之旅是安全而舒适的。他不仅享用了VIP车厢,还有一名姓胡的官员专程陪同,担任向导和翻译。
但斯诺感兴趣的不仅仅是沿途的旅游风光,否则他不会选择去绥远。这位天生具备强烈好奇心的记者不希望成为单纯的传声筒,他想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一切,当他抵达张家口后,发现西边正遭受着可怕的灾难。在他的坚持之下,他们的VIP车厢才得以挂在艾黎乘坐的那列载人货车后面,一起朝受灾严重的旱区进发。
在站台相遇后,斯诺邀请艾黎去他的VIP车厢坐坐,享受享受舒适的设施,但那位姓胡的官员看了一眼艾黎,便傲慢地拒绝了他的要求。
艾黎丝毫不感到愠怒,他很高兴地回到农民伙伴中间,坐在地板上摇晃到了萨拉齐。在那里,他将参与国际赈灾委员会的救灾行动,修筑一条灌溉渠。
和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斯诺比起来,艾黎与底层民众走得更近,他并不认为自己返回那肮脏的货车车厢是什么羞辱。
这与艾黎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有关。艾黎的父亲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认为只有国营工业化农场才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出路。他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尊重教会,但他却摒弃了教会。他不让自己的孩子上主日学校,说这是因为他不愿在孩子自己能作出决定或理解人生之前把信仰强加于他们。
“我相信宇宙间有神主宰着生命与演变,但我不信基督是上帝生的儿子,他只是人类一位伟大的领袖。我喜欢进教堂去唱和听美丽的圣诗,却不会背教义,不过我还是信基督的教导的。”艾黎的父亲说。
艾黎的母亲则不仅治家有方,还是早期在新西兰争取并获得女性普选权的妇女之一。正是由于他母亲等人的努力,1893年,新西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批准妇女享有普选权的国家。
这样的家庭背景似乎注定了艾黎的一生将要献给社会运动,也注定了他与底层民众具有天生的亲密感,关注农民和工人的生存状况。
另一个有趣的细节是,艾黎的名字“路易”带有反抗帝国主义的意味——那是他的姑妈根据一个名叫路易·曼尼亚波托的毛利族首领的名字起的,此人在19世纪60年代毛利人的土地战争中奋力抵抗英国军队,最终成为传奇人物。
艾黎和斯诺最终也将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彼此的友谊将愈来愈深;同时,他们也将愈来愈深地卷入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被中国改变,并改变中国。
31年后的1960年,作为中美恢复外交关系的前奏,斯诺重访中国,那一次的访问,他的身份正是定居中国的路易·艾黎的私人客人。1929年夏天小站站台上的相遇只是一个开端,波澜壮阔的画卷正缓缓铺开,为艾黎,为斯诺,也为中国。
路易·艾黎是个古怪家伙
谁能想到,中国人迎接这位日后将成为老朋友的新西兰人的第一件“礼物”居然是唾沫!
在1929年的那一次站台相逢中,斯诺对艾黎的印象是“古怪的家伙,但很有趣”。
艾黎的确有些古怪。比如,他终身未婚,不少人对此也曾有过种种猜测。他的秘书吕宛如则透露,艾黎并非有意选择独身生活,“多少不同国籍的女性仰慕他的品德和才干,大多因志虽同而道不合,最后止于做终生好友。他自己也并非没有中意的人,但年轻时他认定,在革命中,一个人不该有家室之累,有家室而不能给家人带来幸福,会有愧于心。一年又一年,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如果吕宛如所言不虚,那么另一个问题又来了:艾黎为何会执着于中国的革命,并因此放弃成家,在所不惜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后文中再逐渐揭开。
其实,对于那些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来中国的外国人来说,他们在自己同胞的眼里或多或少都有些奇怪。尤其是艾黎这样自告奋勇、只身一人来中国的,就更少见了——起码,像斯诺那样的记者来华时肩负着采访报道的使命,更不用提来做生意的商人,来传教的传教士了,而艾黎来中国,并没有受到任何组织的委派。
1927年4月21日,这位古怪的30岁青年抵达上海。此前,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经历了生死考验。战后,这位老兵回国办牧场,每天要花上16小时砍灌木、架围栏、修公路、赶牲畜,还要自己种菜、挤奶、烧火做饭。由于战后新西兰经济形势恶化,他的生活十分艰苦。
就在牧场经营无以为继,不得不关闭的那一年,艾黎经常从报刊上读到关于中国的消息,获悉革命的情况。那时,中国的事态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革命的消息也吸引了艾黎,行事风格雷厉风行的他立马决定去中国。
本来,他只办了为期6个月的签证;结果,他却在这个遥远的国度生活了整整60年。很多年后,当路易·艾黎步入晚年的时候,他说,是中国给了他生活的目的,一个值得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和内容日益丰富的岁月。
的确,如果没有来中国,艾黎也许会在新西兰的乡间度过一生,偶尔在某个闲暇的午后回忆一战时期的峥嵘岁月。
但是因为与中国结缘,他的晚年被荣誉所笼罩。艾黎赢得了众多的荣誉头衔,包括作家、诗人、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教育家、中新关系架桥人、英女王社会服务勋章获得者、北京市荣誉市民、甘肃省荣誉公民以及各种荣誉学位。他还得以与中国最高层的领导保持密切联系,成为许许多多中国人尊敬的对象。
不过,如果将这些荣誉简单理解为“幸运”,归结于年轻时代的一次“撞大运”,显然是不公允的。来中国的外国人绝不止路易·艾黎一个,为什么命运如他的人少之又少?
最重要的原因,是少有人像这位古怪的新西兰人一样,身上流淌着亲近底层民众和厌恶侵略、破坏的血液,对中国与中国人怀有如此浓厚的好奇心和同情心;更少有人像他一样,凭着老兵的坚韧和老农的踏实,为中国无私工作几十年,试图改造这个积弊已深的古老国家。
改造的前提是理解。对于外国人来说,理解中国和中国人,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艾黎抵达上海时,遭遇的第一件事就让他费解。
当时,他先去了澳大利亚,然后坐了6个星期的船抵达香港,再从香港出发,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下了船,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他惊讶地发现,这个中国最大的港口居然没有海关,也没有边防检查,不用办任何手续,外国人可以随意在这个国家通行。
更离奇的是,艾黎在码头独自行走的时候,一个码头工人看见他,便面露愠色。当他走过这位码头工人身旁时,工人忽然站起来,朝艾黎脸上吐了口唾沫!
好在艾黎并没有发作,他只是在心里想:“这可是件怪事!这个国家可真特别!”他擦掉唾沫,快步离开了码头,住进了四川路的一家小客栈。
后来他才明白,当时上海有许多外国军队,中国工人因此具有强烈的排外意识。
虽然艾黎日后逐渐被中国人所接纳、信赖、喜爱,但这一幕一直留在艾黎的脑海里,也成为他理解中国的一个入口。
谁能想到,中国人迎接这位日后将成为老朋友的新西兰人的第一件“礼物”居然是唾沫!此后,艾黎遭遇了更多超乎想象的事情,这位古怪的年轻人开始与这个古怪的国家深入接触。
上海见闻
“他们在无盖的铬缸旁操作,周围没有排除含毒水汽的装置。
伤口腐蚀到肉里,手脚上有一个个‘铬孔’。”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五方杂处,华洋共居,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
艾黎却敏锐地发现,这座乐园是畸形的。在很大程度上,它只不过是为富人、权贵以及拥有特权的外国人所享受而已,普通民众的生活极其悲惨——这部分人的生存状况恰恰是艾黎最关心的。
上海的贫富悬殊令艾黎感到吃惊。在市区几条主要的道路上,车水马龙,建筑高大宏伟,一派繁荣的景象,但一旦深入城市的“毛细血管”之中,很快就会发现那迷宫般纵横的里弄狭窄,拥挤,臭气熏人,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乞丐。
“那里每个人都吐痰——上海95%的人似乎都患慢性黏膜炎。”在回忆录中,艾黎这样写道。
艾黎生活的地方有着豪华的俱乐部,时髦的汽车,训练有素的仆役。但是,他却将时间和感情大量投入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居住的街巷里。
起初,艾黎在公共租界的消防处工作,他不喜欢跟单位的官员们谈话,唯独喜欢检查工厂,因为这样可以深入拥挤、发臭的陋巷里的车间,直接接触工人。他的同事们不明白,为什么艾黎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学中文,甚至还学上海话?
1932年,消防处所在的工部局成立工业科,艾黎调任工厂安全督察长,专门负责检查租界内工厂的安全设施。
这一新职位算是彻底发挥了艾黎的特长,也符合了他的兴趣。然而,这项工作却让艾黎极其痛苦,因为他亲眼目睹了太多残忍的场景。
由于工厂的安全措施很差,事故经常发生。农村来的青年工人经常穿着肥大下摆的裤子和宽袖口上衣干活,他们的衣服时常被卷入摆得过于密集的机器。因为疲劳过度,许多工人的手指不慎被冲床切断。还有一次,橡胶厂因为硫化器引起爆炸,460名女工受害。
最让艾黎感到痛苦的,是童工们在“黑工厂”里的遭际。
在当时的缫丝业体制下,许多孩子不过八九岁,却要每天在煮茧的大槽前站上足足12个小时。他们手指红肿,两眼因睡眠不足而布满血丝,眼皮沉得像铅。工头手里拿着铁丝做的鞭子在一排排童工背后来回走动。如果童工把一根丝理错了,工头就用开水烫他瘦弱的胳膊作为惩罚。
其他工厂的劳动条件不见得比缫丝厂好。搪瓷厂里普遍发生锑中毒,制作电池铅板的工厂则盛产铅中毒。
“我还记得那些日夜站在抛光盘前的孩子,他们疲惫不堪,手脚上沾满了金刚砂粉、汗水和金属粉末,真是可怜!”艾黎后来回忆说,“他们在无盖的铬缸旁操作,周围没有排除含毒水汽的装置。伤口腐蚀到肉里,手脚上有一个个‘铬孔’,在那种糟糕透顶的劳动条件下几乎是治不好的。孩子们无可奈何地操作,劳动时间之长令人难以相信,根本谈不上最起码的人权。
他们瘦小的躯体为活命而挣扎,好让老板有暴利可图。在国民经济已经崩溃的情况下,各种工业使得为谋生而挣扎的青老年工人更加困苦……”
作为工厂安全督察长,艾黎能做的却非常有限,他只能从技术上对工人们的劳动条件稍加改善。比如,他曾去嘉定的一家工厂参观那里抄袭来的日本式总煮沸系统,并将其带回上海,在所有的缫丝厂里推广使用,以减少工房里的蒸汽,降低室温。
但更根本性的东西是艾黎无法改变的,比如包身工制度。在艾黎看来,工业就像是一场战争,胜利的总是工厂主。
这样的经历和这样的看法为艾黎后来的人生道路埋下了伏笔。因为渴望看到工人境况的改变,他开启了“工合”计划,而他与共产党人的惺惺相惜更是顺理成章。当时,上海的工人们已经受到延安正在组织进行抗日战争的鼓舞,一些工人出走,参加了革命军队。
当艾黎正为工人们的安全奔忙时,斯诺也在上海——作为当时的外国在华政治经济中心,上海是外国人聚集的地方,甚至在根本上更像是一座外国城市。在斯诺看来,上海是“迷人的、令人销魂的老所多玛和蛾摩拉”。
上海的罪孽在哪里?这位年轻的美国记者与艾黎所见略同:巨大的不平等,残酷的剥削,工人们惨淡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