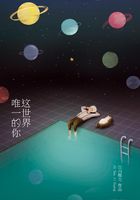阎:所以,你写一个人也好,一块土地也好,一个村庄也好,一个民族也好,他们都有其整体的内心。一个人的内心、一个村庄的内心、一个城市或土地的内心,这个内心和你自己的内心要是相通的、相连的,不然,你的作品从意义上讲就小了许多。可惜,我们很少能把一块土地的内心和世界的内心表达出来。很难写出作家与一块土地血肉相连的情感来。其实,这种表达是相当困难的,每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都梦想能表达一种面对土地的情感和思考,表达土地的内心世界,可你能否表达出来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具体说,你所要表达的这块黄土能否像一个人一样活起来,就像屠格涅夫笔下的森林、梭罗的瓦尔登湖那样。这不是简单地说是对大自然的感受,是把土地写成一个活生生的人。这块土地在你的笔下能否像一个人一样有生命,有血肉,能呼吸,有和你一样的喜怒哀乐。只有这样,才算是土地的情感。
张:你还是想通过一系列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小说世界。这个世界不光是人的世界,还是有山水万物的世界。无论是中、短篇,还是长篇,你都是沿着一条道路往前走,直抵人类的某一存在现场。现在有的人说,我们是“后社会主义时代”了,或者是消费主义时代了,那你是不是在寻找一个任何时代都需要有的乌托邦?关于《受活》,王鸿生写过一个《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叙事》,我觉得他进入你小说的角度也是不错的。你也是在找一种东西,在《受活》中试图建立一个“后社会主义时期”的东西,虽然包括退社、茅枝婆、整个受活庄的人,包括柳鹰雀们所做的一切,他们试图要建立一种什么。买遗体、弄魂魄山、成立绝术表演团,他们不惜自己的一切在建立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问题是这个乌托邦是由一群弱者、残疾人来建立的。包括柳鹰雀最后也要把自己弄残了,到庄子里来,他认为这里是他生存的所在。我觉得这个很荒诞,也很滑稽,但是我还感觉到,像《受活》这样的作品,你还是想建立一个非常理想的世界。你说你不知道为什么写作,但是隐隐地植根于作品中,从作品中渗透出来的一种东西还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说你的精神主体上还是想建立一种东西,只不过这是一个由文字建立起来的梦想世界,一个荒寒的梦想的家园。也许等待我们的就是乌托邦的幻灭。
阎:是啊,既然荒寒为什么还要活着和写作,而不去停笔和自杀?就是你心中还有那么一点梦境的存在。我一直以为,梦境是引导我生命向前的动力和向导。没有梦境的存在,我的眼前就会一片黑暗。梦经常会成为我活着的理由和活着的意义和趣味。比如说我总幻想我母亲能够活到一百岁,儿子会成大才,有很多的钱。知道这些不可能,又总有这样的梦。比如我自己,身体不好,看NBA时总幻想自己在场上跳投三分球百发百中,看拳击时幻想自己跳上拳台如泰森样横扫天下。梦想,是我们活着并拥有希望的理由。你想,无论是一个人、一个民族、整个人类,如果没有梦境,没有梦想,那我们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就是说,没有乌托邦的存在,就没有社会发展的理由了。实质上,我们历朝历代都在为梦境而奋斗,为乌托邦而奋斗。恰恰是一个乌托邦的破灭和另一个乌托邦的建立在引导着人类向前的精神。乌托邦是人类诗意的存在。
张:关于这一点,你能具体说说吗?
阎:讲我的那个大伯吧。他没有什么文化,不识字,活了八十多岁。可总结他的一生,你发现他从来就没有对生活失去过信心。他是一个理想接着一个理想,一个梦境接着一个梦境,一个乌托邦接着一个乌托邦地生存在生活里。我记事的时候,我大伯最大的梦想就是把家里都盖成瓦房,这是他最大的梦想,像《李顺大造屋》中的李顺大一样。可这个梦想在他那样一个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他就为此奋斗了半生,吃尽了艰辛,也没实现这个梦想。到后来,他的七八个孩子大了,他的最大的梦想是要给每一个孩子成家立业。当这些孩子都一个个结婚成家之后,他就老了,他就梦想自己能活成是村里最年长的人。我们村有人活到过九十二岁,我大伯希望自己活到九十岁。在他年老之后,他每次见我回到老家,给我说的永远是他死了之后希望如何如何。从我大伯七十多岁以后,他感觉他的身体不行了,一天不如一天,他就开始梦想自己死后身后最少要有一百个孝子,浩浩荡荡,一片白色,很气派地把他送入祖坟。我大伯活了八十二岁,他艰难的一生,就是被梦想和梦境牵着行走的一生。这就是我的大伯。他的一生活得传奇而又有激情,从来没有对什么失去过希望和信心,直到最后的死,他都怀有死后的希望之梦。
张:他是很重视死亡的仪式。难道死亡后的送别方式也成了他最后的生命的乌托邦了吗?这同样是很荒寒的一件事。
阎:不是重视死亡的仪式,是沿着另外一种梦境和希望继续他的人生。梦,是我大伯人生的明灯,之所以活着,就是他的人生不断有着梦境的存在。我想,我会以我大伯为原型,写一部小说来。我从来没有以人物原型写过小说,这一次,我想在合适的时候试一试。回到乌托邦的话题上来,那么,乌托邦是不是我们人类的梦境呢?试想,如果没有一个共产主义那样的乌托邦之梦,这样一个乌托邦理想,我们这个民族如何会那么乖顺地度过“文革”,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社会几十年的发展不是都被共产主义这个“明灯”引导向前吗?我们在八十年代初不是又迅速开始有了小康、中康、大康的梦境吗?不是又有了大国富国之梦吗?这是不是一个新的乌托邦的梦想?都在说我们民族没有信仰,没有宗教,可一个一个的乌托邦是不是我们全民族的信仰呢?乌托邦其实是人的发展中的一环又一环的梦中的明灯,是人类为生存建造的诗意的精神之园。前一段时间我在家看陶渊明的诗和陶渊明的传记。仔细去想,陶渊明是多么了不起,他不仅是诗人、文学家,他应该还是个哲学家、精神建造学家。一千多年后,《桃花源记》成了我们现代文明多么好的一个后花园啊。“桃花源”这块净土不是我们整个繁华社会的乌托邦吗?
五、独有的情感,是现实存在的艺术标码
张学昕阎连科
张:我越来越清楚了,你仍是依赖梦想写作,依靠心灵的真诚写作,所以,我们永远要直面现实和自身,远离矫情,蔑视虚伪的情感。请你谈谈“伪情感”这一点。
阎:你说的“伪情感”,是指作家在创作中不使用自己的心灵写作,不讲真话。巴金说的“讲真话”,在这里是判断伪情、真情的最好的标尺和试金石。试想,你在写作中使用的不是自己的情感,不从现实、存在出发,而是放弃自己的写作立场,使用“社会意识情感”进行文学创作的话,那么,你的作品即便感动了自己,打动了人心,这也一定是暂时的,而非长久的。我们以路遥的《人生》为例,以今天的眼光去看《人生》,可以从小说艺术上找到许多不足,但二十多年后,今天去看《人生》时,它仍然是感人的,仍然是打动人心的,为什么?就因为路遥在写《人生》时,倾注了自己的心灵、自己的情感,而非“社会情感”。“自己的情感”非常重要。你的写作,只需要你的心灵去为人物的心灵忧虑和欢乐,不需要你为别的担忧和欢乐。反之,就是你写作时泣不成声,也还有“伪情感”存在。我是读这些小说长大的,具体说,就是读五十年代的革命小说长大的。你能说这些小说中没有情感吗?他们每个作家都是一边哭泣一边写作的,都是到了不写就夜不能寐的地步去写的。可以说,他们的情感是真挚的、无私的,但今天我们去看,去重读这些小说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情感不是你独有的,而是革命的、大家的、阶级的。这就使这样一大批小说的艺术高度有了折扣,太不尽人意。加之他们的小说中放弃的艺术元素太多,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一大批前辈作家时,一边对他们表示着应有的尊敬,又一边感到许多惋惜。在我早期的创作中,有许多这些小说的影响,但没有多少艺术的含量。千辛万苦的努力,也就是仅仅会“讲故事”而已,凭借对生活的一些别人也有的庸常情感来写作,而不是独有的情感。咱们有句老话,叫“子不教,父之过”。因此我常说,那时我的小说之所以写得不好,除了我的悟性不高外,前辈作家也应该负些责任吧。
张:这怎么讲呢?
阎:马尔克斯最初学写小说时,看的是《变形记》,所以,马尔克斯的成功有着前辈作家卡夫卡的功劳。我最初学写小说时,看的是这些小说,所以,我的失败,前辈作家也不能“不负一点责任”呀。这是一个写作的继承和传统的问题,当然,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前辈作家如柳青这样的人,有那么好的艺术感觉,而没有写出理想的作品。谁应该为他们负责呢?
张:显然,他们无形之中就压低了你最初写作或者说审美判断的起点。一个作家的早期阅读和他后来的创作有很大的关系。最早读到的作家很可能影响他一生的写作走向,甚至看世界的方法和叙述的方法、个人情感与存在世界的关系。
阎:是这种情况。马尔克斯在读大学时,看完《变形记》拍案而起,惊呼:“天呀,小说是可以这样写的。这样的故事我外婆不是早就告诉我了嘛!”我写小说的时候,看的是另外一些东西,而且老师们也告诉我这些都是好东西,说小说就是要有大众的情感,没有说在创作中独有的情感更为重要,没有说独有的情感才是现实存在的艺术高度与标码。当你需要独有的艺术情感的时候,比较一部作品和另一部作品谁好与谁更好的时候,你没有别的作品可以比较,可以做参考的坐标。但这些前辈作家,我觉得首先有一点,他们在写作中都尽力写作了,都倾注了自己的“真实情感”。我们应该看到他们所受到的强大的政治和体制的束缚,这是一个意识问题。但另外一个问题是,面对这样的政治、体制的束缚时,作家无法发出自己独立声音时,作家的写作立场、人格力量、情感力量是否部分丧失和完全丧失?是否应该多少保有一些自己的写作立场和世界观?仔细去想《诗经》的创作,《诗经》里几乎一半的作品也都是相关政治生活的,比如里边那么多宫廷乐曲等,那怎么会不是政治生活呢?怎么不是体制的产物呢?然而,我们今天去研究,去看它的时候,仍然觉得它有意义。这个意义并不是说它是两千多年前的作品,而是说它有文学的价值。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有作家的写作立场和个人情感——独有的情感体验。我们再去看陶渊明的作品,除了《桃花源记》和他大量的田园诗,陶渊明也还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作品是那种抒怀诗、咏怀式的写作,可为什么这些作品也会有那么强的文学性?就是他写作时倾注的是独有的情感和个人的心灵,倾注了真挚的个人情感。前一段时间,我偶然还看到了一本当年叶圣陶编的小学课本,小学课本里也有宫廷传奇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仍然比我们今天的课本有情感,有趣味,有意义。问题在哪里?就在于作家去观照这些社会、政治问题的时候,完全用的是文学的、审美的眼光,并且在写作中有着作家鲜明的写作立场。用审美的眼光去看待社会,看待政治,看待体制,把自己个人独特的情感融入社会这一个部分,或者是让社会内容、社会问题进入自己个人独有的情感,这是后类作品最大的成功之处,是所谓“红色经典”这类作品最大的缺憾之处。
张:这里就有一个美学的问题在里边。一个好的作家会以自己的方式,也就是以自己的作品的结构、语言、人物、故事等建立一个独特的文本的存在。一个作家眼睛里的世界,他诉诸了很复杂的个人情感、思考在作品里,这完全是一个审美的目光,越过了诸如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具体的表象的边界,直接进入人的内心,进入人性的深处。面对这个文本世界,我们以一种什么样的接受方式和角度进入作家为我们提供的世界,这关系到个人的文化、文学素养,当然也关乎一个时代的审美环境。我想,一个伟大的时代一定是个有审美存在的时代。
阎:简单说,就是以你的心灵去观照时代,以你的真实情感去抒写时代。
张:一个作家要用心灵去体悟自己民族的东西。这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长河中有种种复杂的情绪、情感,需要作家去抒写和表达。无论是历史的矛盾,现实冲突的原委,还是内心的隐秘,值得张扬的、令人鼓舞的精神,都会在优秀的作家、诗人的个人独有情感里强烈地涌动出来。故事也好,一两句诗句也好,它蕴涵的常常是民族和个人情感的历史。写什么题材不重要,问题在于个人独有的情感是否得到了有效的表达。
阎:对,你个人的作品,投入的不应是集体的情感,他人的情感。回到最初话题,所以我觉得,在对“十七年文学”进行评价时,我就是那句话,“文学史的意义,远大于文学的意义”。
张:它们作为一些资料,作为一些问题可以存留下来。文学史能记住或应该记住哪些作品,只有时间才会解决这个问题,尤其面对我们所在时代的这些汗牛充栋的作品。我在给学生讲当代文学史的时候,每一次我都把要讲的作品找出来翻一翻,我真是很打怵,我怎么才能把它仔细地再看一遍,然后认真地梳理一下,脑子里都充斥了自己以往对这些作品的认识,已经根深蒂固了,觉得有些作品我真的有些看不下去。像《红旗谱》、《创业史》,我觉得这里边也有作家的那种困惑、那种复杂的情感的焦虑,但作家的头脑还都是围绕意识形态在转,审美的意识是很薄弱的。这是与那个时代有着直接关系的。
阎:在这批作家里,我觉得最有才华的应该是柳青。其余的,去分析他们的作品,在那些长篇中,它们的结构是一样的,塑造的人物是大同小异的,语言个性也是一致的,没有任何作家表现出自己“独一无二”的情感和写作个性。“独一无二”非常重要,我以为“独一无二”不仅是作品的风格,更是作品的生命、作家的情感和生命。
张:你说这个我就在想啊,现在的孩子们看了这些“红色经典”,慢慢的,他们渐渐地也会和现实接触得越来越多,“十七年文学”给他们提供的想象,在他们心里面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那些生活已经完全出现在他们的想象里了,变成他们想象的一部分了,他们会觉得像他们的童话一样。他们是不能想象的,不能想象他们的爷爷们、曾爷爷们是这样的一种叙述,或者说,他们叙述的是这样一种生活。他们为什么这么叙述?他们还会想中国革命史吗?还会想象中国当代史吗?他们会怎么用这种文本提供想象的依据?对照孩子们自己所处的生活、所处的环境,他们怎么想象他们的未来?包括怎样建立起他们的情感的、精神的维度?
阎:要相信,孩子们的眼睛是亮的,内心是敏感的,文学的是非也会逐渐在他们的心里明确和坚定。
张:所以,一个伟大作家,他也就有责任依赖他对生活的独特情感去判断,去思考和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