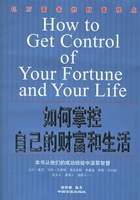阎:没有宗教的民族,的确会使我们的文学在谈尊重人、爱“人民”时显得有些无力,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民族没有宗教就对文学失去信心。《红楼梦》写的同样是我们这个没有宗教的民族的事情,也同样是我们民族无可替代的伟大文学作品和文化遗产。我想,我们没有宗教是与生俱来的,但作家的宗教情怀却是可以一点一滴养育的。比如说,我们说“人民”、“人民性”的时候,最根本的东西是让我们去爱世界,爱世界上的一切,爱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爱我们的敌人。当我们尝试、努力在文学中去爱一切的时候,是不是就有了一点宗教情怀呢?我想,面对我们民族没有宗教时,重要的不是我们文学如何去面对,而是我们如何表现我们对所有的人和世界的爱的胸襟。
三、时间,是艺术的无刃之刀
张学昕阎连科
张:我们知道,贾平凹在写出《废都》以后,心灵和精神上也遭到了一个很大的打击。就像你前面提到的,你在这几年里经历了一些写作、工作变故以后,面对你自己的“现实”,必然会不断地思考“我为什么写作”的问题。也许有时候,一个作家的判断、意识与一个时代的现实生活,有可能是错位的。
阎:毫无疑问,《废都》是贾平凹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作品,甚至有可能是他最有价值的作品。今天去考察贾平凹的作品,实事求是地讲,不管有多少人骂,我想你还必须承认《废都》在当代文学中的价值。一部超出读者想象的作品的出现,必然伴随的是与作品同在的不断的争议。
张:可能是阅读习惯、阅读心理不正常,有问题。那么,作家的写作心理也是一个需要分析、研究的重要问题。作为一个作家,当他发现了自己的内心与现实、存在的种种和谐或悖谬时,他的写作姿态、写作心理是否端正合理,是否积极健康,这也同样重要。
阎:更重要的是一些人的阅读心理要健康。当年劳伦斯的小说一直被禁,一直是被作为淫秽文学而存在,但今天去看,它不同样是经典吗?我们没有觉得《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淫秽的,它仍然是一种非常美的东西。我想《废都》就可能也是这样一种情况。情况就是这样,当某一种文学走得超越、极端的时候,甚至连它“行走的姿态”都会遭到非议和不解。这是正常的,时间会平息、证明这一切。今天我们来谈《废都》的时候,人们不是显得从容、平静多了嘛。时间让读者平静,让文学平静。只有平静,才能看清一切,如深湖之水,我们试图看清湖底的东西时,必须要让湖水变得平静。平静湖水的唯一工具,就是时间。时间让我们逐渐认清许多作品的意义和无意义,而写作也是如此。时间让我觉得写作没有意义,没有理由,可也许有一天,时间也会让我觉得写作有意义,有理由。一切,都需要等待,需要一些等待中的经历。
张:不管怎么说,作家的写作总有一个文学功能和情感担当的问题。就是一个作家和一个时代的现实有可能会是处于某种错位状态,那么,他也应该从世道人心的视角,从对世道人心的悲悯、同情视角来切入生活。实际上一个真正的作家是要表现自己的良知的,把自己的良知写在里面,是同情的或是悲悯的。比如后来我读到了你的《天宫图》、《年月日》,特别是那篇《耙耧天歌》,那个母亲为了她的不圆全的孩子们,去挖他丈夫的骨头来给他们熬汤喝,后来她自己也为了让她的孩子幸福,自杀了,实际上也是为了把自己的骨头贡献出来,特别是她刨那个骨头,和她的二女婿一起啊,我觉得这样写真是太残酷了。揭示苦难,呈现时世的艰难,呈现生存的苦难,实际上就是探究生死的冲突,这是一个作家的责任。但我感到你那里面有一种很深的焦虑啊,一种不安,更让我们感到你表达的那种残酷有些难以接受。我一直觉得,余华的那种残酷是另外的一种残酷,跟你的残酷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他的《现实一种》,包括后来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活着》里面,福贵的亲人一个个从容不迫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死去,到后来《许三观卖血记》里一次次卖血,把人卖晕,我觉得他够残酷的。但他是一种缓慢的进行,而你是非常激烈的,这种残酷是超出伦理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我觉得你简直是“残酷大师”。为什么要这样写?当时我阅读这些作品时,我感到意外、震惊,比起《许三观卖血记》,这似乎让我对残酷更是一时无法接受。如此想象生活,想象现实和存在,令我非常震惊。
阎:不是我残酷,是我看到的现实残酷。很多新时期的小说,包括那种新探索小说,它们写的那种暴力、死亡不残酷吗?但大家不太争论,因为它离我们的现实比较远。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采取的姿态是温情暖意、微笑的忧伤,故事讲得不缓不急,慢慢道来。而我小说中的残酷,近乎一种冷酷的残酷,或者就是冷峻的残酷。这是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是两种面对现实的写作姿态。
张:是两种写作风格,包括你和莫言。我看到过王德威写你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莫言的小说里呈现的是朝气蓬勃的、那种欢腾的东西,而你阎连科的小说呈现的恰恰是一种死寂,是一片死亡后的静默。我觉得他这话可能说出了某种东西,这也是你和莫言的个性不同所致。
阎:小说的风格、性格、个性,这种东西说到底,它不是简单的你的小说和别人小说在语言上、叙述上有什么差别。什么是个性?个性即作家的内心。内心即风格。一个人内心中包含有什么样的文学世界,他的小说必然呈现什么样的文学样式。风格不仅是文学观的表达,也是世界观的表达。反过来,他看待世界的目光,认识世界的方式会左右他面对文学的姿态,会使他的创作表现出不寻常的个性。余华对世界暖意的同情,莫言对世界是欢腾的希望,而我,是一种近乎绝望的态度。这些在小说中以“风格”的样式表现的是作家的最有代表意义的复杂的内心,回过头来都会影响你的读者。余华的小说为什么卖得那么好?最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中国人其实不喜欢莫言小说中呈现的那种狂欢式的写作,我们的传统阅读中没有接受狂欢的习惯,你看我们的四大名著中有多少狂欢、欢腾的写作?莫言给读者的是背离传统的东西。那么,我小说中的死寂,你说谁会喜欢?如同说我们去一个乡村游览,人们自然会到有青山绿水的地方,而有谁会愿意到一片坟墓里去走走看看?道理就这么简单。再说,余华小说中的暖意的悲悯,疼痛中的抚摸,这正符合我们传统的阅读习惯。去想想我们传统的舞台戏剧,最受欢迎的总是那些悲情而有暖意的作品。比如《牡丹亭》、《西厢记》、《白蛇传》、《天仙配》、《大祭桩》、《陈三两》、《梁祝》、《黛玉葬花》等等,哪一出,哪一部,不是在风格上表现那种忧伤的温暖?所以,对于读者多少,我已经早就不去想了。你的读者多少,是哪样的读者群,这是你的内心世界决定的事情,不是你的写作技术决定的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因为读者多少去改变我们的内心。反过来,能够被改变的内心也就本来不称其为内心。
张:这恰恰是问题的所在,他们呈现的可能是一片青山绿水,而你呈现的是乡村的荒漠、坟墓、光秃野岭。一个人内心潜藏着什么样的理想,就会发现和写出什么样的现实。也许,时间会最终证明你写作的深厚与独特。
阎:希望时间会让人们逐渐适应或接受我小说中的死寂吧。时间多么厉害哦,它是一把钝刀,又是艺术的无刃之刀。它会穿越时空,要么慢慢杀死你的小说,使你的小说再也没有生命,再也没人阅读;要么慢慢拉长你小说被杀死的时间,让你的小说永生或者有较长的生命,有不算太多却是不断线儿的读者。无论是你小说的被批评、争论、褒奖,最终都得经过时间这把钝刀之刃。比如鲁迅的小说《药》,写到了吃人血馒头的残酷,那血淋淋故事才真是一片死寂。还有阿Q的死、祥林嫂的命运,够残酷的吧,可直到现在人们不是依然地接受嘛。不怕写得残酷,就怕残酷不出独到的艺术;不怕你小说中个性与阅读习惯的不符,就怕你小说通不过时间这把无刃之刀。
四、存在的荒寒与乌托邦的诗意之灯
张学昕阎连科
张:我记得是在1986年的时候,北京大学的陈平原、黄子平和钱理群他们写过一篇文章,叫“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这篇文章里,他们提出要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的问题,从作家的创作姿态,从小说的美感特征,从文学史的角度等诸多方面,讲到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和中国文学,主要谈到二十世纪小说的美感特征,他们将其美感特征描述为悲凉。特别提到,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鲁迅创造了一个高峰,以他为代表的中国作家,以及在他之后有几代中国作家,都沿着这条道路在叙写着一个相互接近的东西。文章特别提到了这样一句话,“悲凉之物,遍及华林”,用它表达中国作家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沧桑感、悲凉感。我觉得,你的写作中生成的美感特征就是属于这一脉的,是从鲁迅这一脉下来的,总体上是悲凉的。实际上它的这个“悲凉”只是指鲁迅这一脉的,不是沈从文那一脉的。从这种意义上讲,这种悲凉,就是刚才说的那种残酷,那种冷硬,或者是荒寒,是对现实、存在的绝望与虚无的反抗和搏斗。小说对现实和存在的思考已经进入哲学的层面。
阎:对,他们说的悲凉很能概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这种很大的气场,是小说精髓的一种东西,它是指一种从美感角度去认识世界和描绘世界的东西。
张:那后来到余华这里,多多少少接续上了,当然包括伤痕文学时期的一批作品,还有后来的知青小说,王安忆的“三恋”,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韩少功的《风吹唢呐声》等。他们那批作品,就是略微有那么一点类似清冷、荒寒的东西,但不是整体美感的东西。所以,我们只能讲,就是一直到九十年代,余华的写作稍微接续下来了。我感到从你的《日光流年》开始,包括你的一些中短篇,这种接续非常鲜明。基本上就是我刚才说的几个词,是冷硬的、荒寒的、悲凉的。
阎:说“荒寒”比较合适。我自己经常想,你为什么写作?找不到理由,可又不得不写。这种心境最能体现荒凉的写作情态。史铁生说:我写作,就是为了证明我还活着。这种心境是多么的荒凉啊。可是人家的荒凉是有其出处,那么我的荒凉到底来自哪里?是现实生活?生命?家庭?社会?还是世态人情?都是,又都不是。就像你每天烦乱,又不知为了什么;每天失眠,又毫无理由。这是一个无敌之阵,不见刀枪的围困,写作一旦进入无敌之阵,就会非常痛苦,非常荒寒无奈。这种景况是我最不愿经历的,又是最必需的。
张:这是存在对精神的围困,而你又必须面对。当年萨特写过一个小说叫《墙》,萨特想以此形象化地凸显他的存在主义哲学。墙,就是指人心之墙啊,就是人和人之间无法沟通,那种生存的悖论。这个里边还是有很多哲学的东西,冷硬、荒寒,人们之间这种悲凉、冷漠,它其实就是一个存在的问题。
阎:哲学家都是了不起的,他们能把人们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几句话说得清清楚楚,可是作家却注定是那些永远把问题扯不清的人。注定是要把小问题说大,把简单的说复杂,把说得清的搅糊涂的人。你说荒寒,你荒寒什么呀,年龄早过了不惑之年,家里日子也好,孩子也好,身体情况也好,你要面对的世事人心也好,都不需要你有荒寒的内心。还有老家的事,农民、土地、村落,你说你有必要为这些去想这想那吗?有时候我经常说,阎连科,你贱呀,操那么多闲心干啥呢!可是,你还是忍不住要想,要写;忍不住对生活要感到荒寒而无奈。
张:读你的小说,就能感到你对人的存在的落寞和无奈,你小说中有一个人类整体性的孤独的问题。
阎:也许是孤独。也许这份荒寒就是来自你的孤独。很多时候,你似乎有很多话要和人说,可真有机会和投缘的朋友聊天了,你又发现你什么都无从说起,什么都无法和人说,说出什么都有酸溜溜的味道,都有杞人忧天的感觉,都无法让人理解。你发现,有的话永远无法和人讲,它只能永远在你的内心储存,唯一让这些储存到一定时候的话见到阳光的机会,就是通过笔端向稿纸的流淌。到头来,你就不得不又去写你的小说。为什么写作?也许就是想把那些无法和人说的话说出来吧。可又一想,如果这是你写作的理由,这理由又是多么的脆弱啊。说不清,道不明,反正就是一个无法和人说清的烦乱、荒寒,感到什么都没有意义,只有写作使你感到某种温暖,有可能减弱你内心的荒寒,使你荒寒的内心不至于到了死寂、死亡的程度。
张:孤独大多是来自于生命无意义的想法。你《日光流年》里三姓村是孤独的,《受活》里受活庄是孤独的,从这个角度讲,《丁庄梦》是一种极度荒寒的孤独,其实这就是人类的一个缩影。你在写作中,是如何意识到这种存在的整体的荒寒?你是有意要在文字中张扬这种美感特征吗?
阎:我知道自己经常有神经病似的荒寒的感觉,但没有意识到世界整体的荒寒,也没有有意地在文学中整体地张扬这种荒寒。我就是感到荒寒到一定时候,到了不能给人说、又特别想说的时候,就动笔去写小说。孤独也好,荒寒也好,我会去做那样的比较:一个单身,无论他如何地快乐,和一个温暖的家庭比起来它还是孤独的,荒寒的。一个幸福的家庭,和一个兴旺的家族比起来是孤独的,荒寒的;一个兴旺、发达的家族,和一个繁荣的城镇比起来是孤独、荒寒的。如此类推,小城市和大城市比,大城市和北京、上海比,北京、上海和东京、纽约、巴黎比,小国家和大国家比,比如巴勒斯坦、塞尔维亚、冰岛、塞黑和中国、美国、印度比,还有穷国家和富国家比,如朝鲜和日本、美国、欧洲国家比。还有,把这个人类放在宇宙里比,这个星体是多么的小啊,它是多么的不堪一击哦。这样一比,就觉得怎么都没有意思了,无论你是一个人、一群人、一个民族,有谁不孤独,有谁不孤寒?其实,我们人类有一个同样的不被发现的内心,那就是荒寒和孤独。
张: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也是整个民族的一个缩影啊,当他面对世界的时候,马尔克斯感到的也是孤独,所以他内心所承载的东西也是巨大的、相当沉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