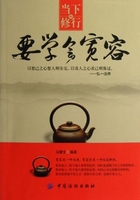结构不能单单是叙述的另一种方法,它必须是小说内容的组成部分,必须成为小说的血肉,也是小说内蕴的灵魂。它的存在,是小说内蕴的必然要求。
你知道一个故事和它相适合的语言只有一种,但对你来说,一生要讲十个故事,一百个故事,可最适宜你讲故事的语言也是只有一种。
一、结构:小说内蕴的必然要求
张学昕阎连科
张:我一直对想象力和小说的结构、语言之间的微妙关系有着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在你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以来的写作中,我日渐感觉到你小说强烈的结构力量。关于长篇小说《受活》,我们以前曾谈了很多,但是却没有谈到《受活》的结构问题。我曾看到你和李陀先生的一个对话,你谈到这部小说的结构就仿佛是一个中国式的盒子,你说的这个东西,指的是不是那种一个一个从里到外套在一起的小人一类的东西,很多人去俄罗斯旅游带回来的就是这种东西,很好玩儿的一种叫套盒之类的玩具。
阎:是“中国套盒”,不是俄罗斯的人套人的玩具,它的年代非常久远,至少有一两千年的历史。中国套盒是大盒套着中盒,中盒套着小盒,小盒套着更小的盒子的一种木制器具。这种器具精致而神秘,有许多贵族夫人经常用它来做首饰盒。拉美作家略萨有一本谈小说艺术的书,书名就叫《中国套盒》。我说的中国套盒,是指《受活》的故事是一个套着一个再套着一个的讲述方式。
张:你指的是不是《受活》的注释和絮言?
阎:是的。但不单是指《受活》的絮言,而是指整部小说。因为絮言是套在整部小说中的一大部分。整部小说是最大的盒子,絮言是第一层盒子内的第二层盒子,里边还有第三层、第四层,甚至第五层、第六层。
张:我早就注意到,在《日光流年》里,注释就已经作为正文的方式出现在各个章节里面了,已经变成了叙述的一个主体和重要内容了。那么到了《受活》,可以说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变成了一种叙述方式嵌在叙述里,已经与叙述融为一体。但是我们作为读者阅读来讲,无论是专业读者还是业余读者,就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那种尾注,放在后面,不应该把它和正文放在一起。可后来我发现你的注释和絮言,在《受活》里竟然不断地膨胀起来,已经膨胀到和我们所习惯的正文并驾齐驱了,所以说让人感到有些不习惯,觉得这是你有意在表达什么或是追求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在做一种对于传统叙述结构的大破坏、大冲击。正文和“注释”、“絮言”,已经不是简单的互文的关系,而是浑然一体的整体。你可能还记得我在2000年曾写过一篇关于当代小说中的寓言问题,特别提到你的寓言结构的问题。后来我就想,你在结构上是“时光倒流”也好,絮言也好,注释也好,毕竟还是在追求一种“陌生化”的东西,你作为一位作家,自己怎么从小说结构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阎:我想是这种情况,中国有白话小说以来,长篇小说发展的时间更短一点,白话小说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有结构意义的传统,我们去谈老舍也好,巴金也好,茅盾也好,包括最早的《倪焕之》这样的长篇小说,都是我们说的传统的结构方式。所谓形式,就是讲故事而已,没有任何新鲜的结构可谈。但是,小说结构实际上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中是非常重要的小说元素。我们仔细去想所有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尤其长篇,凡是经典的,在结构上都有相当大的不同凡响之处,甚至出现了像略萨这样一些结构主义的大师。结构对于小说的发展,不是偶然的叙述变化,已经到了没有结构就没有小说的地步。而我们今天的文学,必须放在世界文学的平台上去重新考察和写作,不能单独放在我们中国文学的范围之内来说、来写。所以说,结构这个问题,一个成熟的作家就不应该不去考虑,不去实践。尤其到了九十年代的中后期,中国已经有许多作家非常明显地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莫言、韩少功等。当然,像《日光流年》这样一个结构的产生,它是有一个过程的,而不是一梦醒来,就有了一个非凡的小说结构。我之前写过一个长篇叫《最后一名女知青》,我想这部小说是我在结构和语言上的一次尝试,在我们的整个长篇创作中,这部小说没有多少意义,但在我个人的小说创作中却非常重要。因为是它使我完成了后来几部小说语言和结构上的尝试。《最后一名女知青》的结构,完全是咱们说的人鬼之间的时空交错,叙述在人鬼之间自由穿梭。现在看来,小说中的城市与乡村,现实与虚幻,阴界与阳界的置换,也许在结构上显得有些僵硬,但到了《日光流年》,这样的置换和结构,就已经比较的流畅和自然了。
张:它更像是一次实战演练,正是它的粗粝和“僵硬”换来了《日光流年》的流畅和自然。
阎:可以说,是《最后一名女知青》,成全了《日光流年》和我后来的小说创作。
张:那么现在我们来谈《日光流年》。《日光流年》是一部关于死亡和恐惧的故事。对死亡、对濒死的人的人性的呈现,仿佛正慢慢地从时间的缝隙中款款溢出,那些文字让你能够从中听见死亡的声音,惊悚和战栗,同时生出一种煎熬感。时间,成为你这部小说的一个结构的关键,它既是结构的重要元素,也是叙述的具体内容。
阎:对。这就是我经常讲的,我特别渴望把作者自己从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你会发现用这样一个“索源体”——这是评论家王一川对《日光流年》结构的命名。这样一个索源体的结构,使这个故事丰富起来了。《日光流年》结构上的成功,给予了我以后小说创作结构上极大的支持和信心,也给我了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没有结构,我就不会去写小说。尤其在长篇创作中,没有一个我认为全新的、好的、理想的结构,我的确无法进行创作。就《日光流年》而言,这个关于时间、关于对死亡的恐惧、关于把作者自身从死亡中解救出来的故事,必须是一天天、一年年地由死写到生,否则,要从一个人出生那天写到他的死亡,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所有关于死亡的小说,都是这个样子的。人——怎么出生、怎么成长,最后怎么成熟、怎么变老、怎么死亡,这就是我们通常的故事和通常的讲述方式。那么,《日光流年》恰恰相反,它把故事完全倒过来,把生命从死亡那一天开始写起,四十、三十九、三十八、三十七、三十六、三十五,一直倒退到他一岁,半岁,最后回到母亲的子宫。这样,这个关于生命消失的故事,就由死转化成了生的故事。它对我们的生命、生存和永生有非常大的意义,甚至我觉得在生与死这个问题上,它更进一步了。你会发现,其实死就是生,生就是死,故事就这么复杂起来了。
张:我想,这就是结构在小说中的作用和魅力。一个成熟的作家一定会仔细地考虑一部小说的形式,我认为,在很大的程度上,形式会创造出价值和意义来。你甚至可以说《日光流年》的结构,也就是我们说的形式大于内容,但这样的形式创造出的内容具有难以想象的美学意义。
阎:在这一点上,《日光流年》之所以今天大家还这么津津乐道,我想这就说明了结构的意义。好的结构,在小说中是一种力量,也是小说的血肉。
张:是这样。但《日光流年》的故事本身,其令人震撼的力量也的确在同代作家和小说中实属罕见。故事、结构构成了文本的双重的震撼力。
阎:这也得益于结构。小说中除了你说的语言的张力,故事的惨烈,细节的惊人和人的生存的触目惊心外,除了大的“索源体”的结构,它的细部的结构也有一定的变化。如:小说全篇分五卷写成,而每一卷的叙述方式又都有不同,第一卷是你刚讲的注释叙述,第二卷是通常的章节叙述,第三卷在叙述上再次有了变化之后,第四卷就是《圣经》“出埃及记”的叙述。这些变化,都给读者带来阅读上的不同效应,都加强了阅读的震撼,所以,我说“结构是一种力量”。那么,到了《受活》,在结构这一点就非常坚定了,你会忽然想到,《受活》的故事其实是两条线索,两个故事的分分合合。两条线索,一条是现实的,是我们今天改革开放这么一个年代,县长需要把列宁的遗体从俄罗斯购买回来,但又缺少这样一笔资金,正好可以让“受活庄”组成“绝术团”去演出,去挣回这笔钱。这是现实的故事,今天的故事。但昨天的故事,历史的故事,你怎么能穿插进去?因为这个故事牵涉着太为复杂的历史,我们这个国家、民族今天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人民”为什么是这样的生存方式、而不是别的生存方式?我们今天的社会形态是从哪里来的?将来要到哪里去归宿?,甚至是世界上百分之四十,或是百分之五十的国家,它们昨天从哪里来?明天要消失到哪里去?这种消失也是必然的吗?如此等等,你的思考如何在我们的历史书写中体现?而《受活》的结构却恰恰帮助你解决了这一切。这就再次证明了结构的力量和魅力。
张:这种结构,也让我们强烈地感到一种社会形态的内在变化。现实和历史交集在一起,故事和故事之间都产生相互影响的巨大的文本张力,一种事物的来龙去脉由模糊到清晰。在“絮言”中,历史,也就是过去的故事直接对现实构成了强大的文本压力。它与所谓正文一起实现着对生活世界、存在的某种“解构”。与《日光流年》相比,《受活》给予我们更多的来自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敏感。在这种敏感的压力之下,你的叙事就呈现一个极为特殊的结构,尤其面对乡土世界,你在表现、追踪他们的时候,也是费尽了心思。我非常理解,你在拼命地寻找一种结构的力量。
阎:对。结构不能单单是叙述的另一种方法,它必须是小说内容的组成部分,必须成为小说的血肉,也是小说内蕴的灵魂。它的存在,是小说内蕴的必然要求。
张:《受活》如果不是今天的结构,它要在叙事上造成那种时空跳跃、穿梭、闪回,通过回忆,那是很麻烦的,而且在形式上也不会给我们一种冲击力,也不会让我们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流、碰撞中产生什么新鲜的感觉。但现在,它通过结构完成了这一点。的确可以说,《受活》和《日光流年》、《坚硬如水》、《丁庄梦》的结构,都实现了你的预想,完成了你的结构是小说内蕴的灵魂的理想。就《受活》而言,它实际上是一个有关今天人类的来龙和去脉的大问题。由此可见,一个故事的讲法,或者说一部小说的结构,实在是太重要了,它直接决定作品本身可能制造出多大的能量。但我有一个疑问,在小说“絮言”的注释中,像“社教娃”、“入社”、“退社”和“黑罪”、“红罪”这样的方言词语,在生活中真的存在吗?
阎:“社教娃”、“入社”、“退社”等,这样的方言在我家乡的生活里是没有的。但在小说中,每一个读者能感觉到它的存在,都不会对它的存在产生怀疑,这在写作中给我对语言的使用带来了很大的乐趣。而且,当你经过进一步的“注释”,你会觉得这些词语包含的意义非常丰富,这就使得结构完全有了内容上的意义。比如《丁庄梦》这样一个小说结构,其实仔细想,如果《丁庄梦》最初就叫《丁庄》也许不错,但是叫《丁庄梦》,就有了一种文体的意义。小说里边有一部分是黑体字,一部分是正常的字。所有的黑体字,你会发现都是亦真亦幻,是真正的梦境或者是白日之梦。我觉得今天来看来这部作品,它的结构不算多么的新奇,但它同样有着结构的力量,同样使结构有了内蕴灵魂的意义。可惜,这个小说的发行受到限制,缺少了很多的讨论和争论。
张:现在看《丁庄梦》这部长篇,其中的“黑体”是依靠印刷解决的,完全是靠纸介质的平面媒体来呈现出这种感觉和意识等方面的潜在变化和面貌。梦和梦境,在这里就是黑色的,恐怖的、死亡的、无望的。无论是人物,还是叙述人,都仿佛在两个迥异的世界间游弋,这也进一步地加剧了作品形态上整体的惊悚感,荒寒感。小说叙述的层次感就呈现出来了。你书写了小说叙述的另一种可能性。
阎:是的,你想没有这样一个梦境,没有这样一群的几十个梦在小说中存在,你会觉得这部小说完全是一部日常化的小说,就是拿艾滋病来讲一群艾滋病人的故事而已。就小说的艺术性而言,它会大大削弱。所以,“梦”,是故事,也是结构。有评论家专门为《丁庄梦》的梦做了统计,说单是真正的梦就有三十多个,他还专门为梦在小说中的意义写了两篇论文。在《丁庄梦》中,比如开头讲到的《圣经·旧约》上的三个梦,结尾讲到我们中国的民间传说,其实那也是我们祖先做的一个巨大的梦:就是女娲造人那样一个人类消失和再生的梦。除此之外,故事中间还有许多虚幻之梦、现实之梦,如书中写到的很多农民卖血变富裕的梦境,那样一些亦真亦幻的描绘,其实都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
张:最精彩、最具现实批判和讽刺意义的梦可能是现实中的那个“白日梦”,就是“地面开满鲜花,地下结满黄金”的那个美梦。我觉得,将梦写到一定的层次也是很了不起的。梦境,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生存结构。
阎:其实,这和《圣经》上写的犹太人要去寻找那块充满“奶与蜜”的“美妙地方”是一模一样,是另外一种翻版。他们所谓寻找的“奶与蜜”和我们梦中要去寻找的那一块“地面是鲜花、地下是黄金”的意义是完全一样的。你看我们今天的社会如此繁荣,如此发达,如此的疯狂和令人痴迷,说白了,每个人渴望的都是“眼前是鲜花,脚下是黄金”的美梦。这就是今天我们所有人生活的一个最大的梦想。所以,我觉得《丁庄梦》没有这些梦,没有这由梦而起的结构,对我来说,小说就无法进行叙述和写作。再比如,你和许多评论家都说到《坚硬如水》的语言。实际上,《坚硬如水》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结构,就是内容。如果没有那样一些“文化大革命”的“红色语言”,这部小说就没有今天的意义。这个语言的意义,包括有些人说的语言的泛滥,其实也是一种意义。
张:泛滥?简直可以称得上是语言的肆虐了,咆哮而出,势不可当。无论是密度还是强度,都是我读过作品中极为罕见的。这也可以说是对那个时代一种全新的言说方式。语言的肆虐当然也和“文革”时代的语境、生活形成某种同构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狂欢”,一种语言的狂欢。而且,不仅是语言上的,更是精神等内在品质上的狂欢或是肆虐,因此文体的意义就在语言上呈现出来了。语言本身,也能折射出一个作家背后的思想意识。我们后面还要深入谈到语言的问题。
阎:对,你说语言肆虐也算恰当。但是,它是这部小说内容的重要部分。恰恰是这样肆虐的语言和我们“文革”的那样一些社会形态、社会内容建立了对应关系。
张:具体讲,还有意识形态,包括人的形态,人的状态等等方面,在一种特殊的语境里形成与众不同的“话语暴力”。语言与现实和事物构成强烈的错位,在一个新的话语维度上,诗意就产生了。
阎:我曾经试图在那次再版《坚硬如水》时去看看语言是否多余泛滥,如果多余就坚决删掉,可是,我仔细看的时候,确实没觉得有什么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