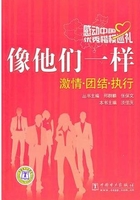张:你的小说关注现实,又有非常强的形式感。当然,你对形式的认识和追求会不会破坏了你的文本形态,让你的形式看上去显得“坚硬”,你似乎并不在意。我记得还曾和苏童讨论过这一点,他毫不讳言地说,形式上太坚硬,一定会影响小说的诗意和意蕴。
阎:这是每个作家的文学观的差别。我以为我的形式正是我说的插入现实的文学的楔子,是我踏入现实的途径。没有这样的楔子,这样新的途径,我将无法进入现实。或者说,就没有我理解的区别于别人的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这是其一。其二,无论你是怎样的文学观,就思想来说,我觉得一个作家彻底不关注当下的现实、他人的命运不能说是不对的,但至少可以说你的现实主义是狭隘的。反过来,如果现在的中国作家都来关注中国现实,现实主义也会显得特别单调和简单。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所有的作家都不关注现实的时候,现实主义就一定出了大的问题。我想,中国有一两个鲁迅足够了,但如果没有一两个鲁迅,你说我们的现实主义会是什么样子的呢?这里,我并不是说鲁迅就是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我们今天去说张爱玲、沈从文、汪曾祺都非常了不得,也可以说他们也都是现实主义作家,是另类的现实主义作家。但无论如何,现实主义文学中不能缺了鲁迅那种现实主义的精神。再有,你刚才讲到中国现实的迷乱、混乱,而《受活》又在相当的程度上表现了我们的现实和历史,表现了我们今天现实和历史的某种混乱。那么,你说《受活》不是现实主义吗?《受活》就是现实主义吗?其三,我理解今天的现实主义,就应该是我一再重复的话:“面对现实和历史,用你的形式,发出你的声音。”这才是我所理解的现实主义,我所试图追求的“现实主义”。
张:对。一个作家,他与普通人看待社会生活的目光和对事物的判断是不一样的,他必须越过既有的一些价值观念,发现现实中左右人们内心和灵魂的东西,洞悉到一个民族文化、性格、品质等方面的变化,细腻地深入到生活和人的精神肌理。就是说,一个作家对民族的爱和忧虑,得用心灵去体察,去表达,这是对现实主义作家的起码要求。
阎:说实在的,我以为我关注现实、关注民族问题时是有偏颇的,并且我经常说,我关注得不够准确、深入和直接。但是,对我来说关注是必须的。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我的长篇小说,一定要有一种现实的疼痛感。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疼痛感,就不要把自己和现实主义扯到一块儿。如果这种疼痛不存在,写作对于我就可能失去了激情,失去了意义。但是有一点,就是刚才提到的,你用什么方式去关注、去写作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张:写作的方式,就是一种打量生活的方式。我们会在作品中注意到,你所看到的生活是温暖、灿烂的,还是凄凉、沉重的,抑或是极其荒谬、荒诞的。这不仅决定了现实主义作品的底色和基调,也决定了作家叙述的方向。在这里,一个作家的审美判断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阎:比如说小说中的荒诞性,我以为荒诞性恰恰就是现实性,是现实主义,可惜大家不这样认为。你觉得这种现实的荒诞有些生硬,可我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以为是大家太固守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太固守于生活现实主义。是这种新的现实主义元素在我们的作品里、视野里出现得太少,你才会觉得它来得太突然、坚硬,在阅读上没有准备。比如《受活》中要购买列宁遗体,让残疾人组成“绝术团”出去演出这些情节,大家一时可能接受不了,可我写作的时候,就觉得它是现实的、发生的。当然,这个“发生”与“不发生”是相当复杂的,它是作家的一种写作观、世界观,别人不认同时你也没办法。再比如,日本翻译这本小说时,他们一再说:你这样写残疾人是对残疾人的不尊重。而我一再讲,不是我对残疾人不尊重,是生活对残疾人不尊重。可他们就觉得这也表达了你作家的不尊重,你怎么和他们解释也说不清楚。
张:哦,是这样啊。这里,不是作家的道德感发生了问题,而是生活本身的道德体系发生了混乱,作家如何表现这种现实则非常重要。另外,大家对于你的这种“现实主义”的不理解,可能还因为对你的小说形式一时还有些不大适应吧?
阎:我一直都没弄明白,大家指的《受活》形式“生硬”,具体表现在哪儿呢?
张:比如,它“腾”一下蹦出来个“注释”、“絮言”,包括我一会儿想专门问到方言、俚语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汉语写作”的问题。这种写法不就是我们说的“陌生化”问题吗?
阎:对,这部小说因为它的荒诞性决定它的陌生化会特别多。但现实主义就不需要陌生化吗?也许这部小说的形式,我是有些过分讲究了,比如为什么要出现“一、三、五、七、九”这样的章节形式。其实,我要讲究的是在乡村里存在的“阴性文化”问题,因为在民间奇数都是不吉利的数字。再有一个,就是讲究到所有的人名、地名都是植物名、动物名,而没有我们现实意义上的人名。后来我想这些可能都不是特别有必要,反而把它过分复杂化了。可是,为什么我们要固守的现实主义一定就必须是这样子,而不能是另外的样子呢?如果这样,那我就只能说“现实主义——我的墓地哦!”那样的话。
张:我也准备与你探讨“现实主义墓地”这个问题,像《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这三个文本,可以说给批评家和理论界提出了一个难题。因为他们以往习惯于用某种固定的眼光来看任何一部作品,所以这三部作品你就很难去说它像什么,是什么主义。显然它们不是用我们能够理解的现实主义可以解释的。那么,马上就有人提出这是“魔幻现实主义”、“狂想现实主义”,又有人说它是“超现实主义文本”和“黑色幽默”等,总之,不会是我们所理解和认识的那个传统的现实主义。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你在《受活》篇首的题词:“现实主义——我的兄弟姐妹哦,请你离我再近些。现实主义——我的墓地哦,请你离我再远些!”这是一种对现实主义的纠缠不清的作家感情。实际上,你也在不断追问你自己,我怎么来面对现实,怎样面对现实主义的问题。所以,这还是一个文本和现实的关系问题,这是你对现实主义的理解的问题。
阎:我说《受活》是地道的现实主义,大家不满意,因为大家认为“不真实”。可《丁庄梦》呢?它是现实主义吗?大家同样不满意,同样不会说它是现实主义,因为它太“真实”了,真实感太强了。大家一方面不满意《受活》中那种“不真实”,另一方面又不满意《丁庄梦》的“真实”。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困惑,也是文学发展到今天“现实主义的困惑”。我觉得,在有些批评家那里,关于“现实”和“现实主义”,已经是一个混乱得理不清的概念了,是一笔糊涂得不能再糊涂的糊涂账。现实主义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而不是传统的、单调的。如果把现实主义这样偏颇地去理解,其实我是宁可不要现实主义,不要主义的。
张:那么让你对你的小说进行新的现实主义命名时,你会怎样命名呢?
阎:没想过。
张:为了区别传统现实主义,区别现在大家“公认”的现实主义,一定要让你对你的小说命名呢?
阎:这应该是我来问你的话。是应该由作家来问批评家的话,如果让你来为《受活》、《日光流年》、《耙耧天歌》和《年月日》这样的小说命名时你会如何命名?
张:我可以命名你的小说为“反现实主义”或“民间现实主义”。
阎:其实什么主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作家要写出好的小说来。
二、作家,应该表现出对“人民”的厚爱
张学昕阎连科
张:我记得你和李陀的一次“对话”里面有一个说法,讲现在的文学是一个“小人时代”的文学。实际上这个“小人”,好像你们指的就是中产阶级,就是一座房子、一幢别墅、一瓶香水、一顿很美的晚餐就极为满足和骄傲的一伙人。我觉得这个时代的很多东西确实让人振奋不起来,有点琐屑的感觉,时代缺少那种能让你觉得为之一震的东西。这不由得让我们注意到“人民”和“人民性”的问题。这也是近年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当代现实的一个重要方面。
阎:这是个太大、太容易受人嘲弄的话题。现在的文学,谈论人可以,但你谈论“人民”,就像一个疯子说我想当皇帝一样,易于遭人讥笑。
张:但是,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永远也离不开它的人民性。这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不能不面对的现实。
阎:我以为,说人民时一定要把文学中说的“人民”和我们长久以来文件、报纸、领导讲话中说的那个“人民”的概念区别开来。应该把我们说的人民加上一个引号。前者说的人民,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的成分,有一种阶级性,有另一种意味,就像文件中说的“我们要领导人民……”如何如何;而我们谈的“人民”,少有阶级性,或说根本没有阶级性,它更多的是指“所有心怀良善而普通的人们”,包括那些怀有善心的有罪之人,是指那些千千万万被人领导的人。这其中只有一种“爱”的思想,而没有别的什么。可惜,现在你分不开这个“人民”和平常所说的人民哪个概念更准确。因为“人民”这两个字,是非常精确地用汉语概括了“公民”那样的一种东西,但现在通常说的人民,已经被意识形态通俗化,其中没有了崇高的意味。而我们在文学中谈“人民”、“人民性”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说文学是神圣的、崇高的。如果文学没有了神圣、没有了崇高,那就不要去谈文学的人民性了。现在,我们的时代正处在一个漫长的转型期,在这个转型期中,过去的“阶级”没有了,但新的“阶级”——准确地说是有阶级性的“阶层”,又凸显出来了。这个时候,谈文学的“人民性”,我的理解就是希望文学的格局要大,关注点要大。什么“中产阶级”,什么“白领”,什么“底层文学”,什么“农民工小说”,如此等等,这是文化、文学中的新阶层论、新阶级论。而谈“人民性”,关注“人民”,这不仅使文学具有的崇高的品性,也是因此才有可能使文学摆脱新阶层论、阶级论的约束,进入大的格局。“白领”、“底层”、“中产阶级”、“农民工”等,对于文学来讲,你说他们有谁不是“人民”呢?不在“人民”之中呢?
张:谈到时代的转型期的现实中的“人民”,你觉得文学需要或者应该在这个所谓“转型期”中对人民承担什么吗?
阎:我不知道该承担什么,只知道在这个时代文学不能两肩空空。也许,社会转型期本来不需要文学去承担什么,但是有一点,文学对此不能没有反映,没有丝毫的思考。对转型期中的“人”、“普通人”、“人民”的精神和情感要有细腻、深刻的描绘。就是前面我们讲的,社会价值体系如此混乱,文学难道不应该去反映和思考一些什么吗?在混乱的价值和道德中,所有的人都异常迷茫,文学或多或少是可以对人们的精神、情感有所梳理的。你说,今天我们的小说,把关注点放在现实生活中的“底层人”身上,这非常值得尊敬,表达了作家的社会良知,可仅仅如此就够吗?比方说,你关注妓女就等于关注了社会,关注了农民工进城就是叫关注社会的话,那么,我关注白领和有钱人的生活,就不是关注社会吗?我关注上层就不是关注社会吗?不能这么绝对化。转型期的社会是需要关注,可这个时期的精神、情感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人”,表达你对“人民”的爱和尊敬。通过你笔下的人,体现你的情感思考。透过白领,你思考的就是一辆小车、一瓶香水、一幢别墅;透过底层,你思考的是打工者被拖欠的工资,进城的农民没有房子住,儿子没有学校读书。这不是文学最应该关注的现实的问题吗?
张:这些都是很浅表的东西。但作家一定要找到或发现这些东西背后的现实和存在的问题,无论是现实的美好,还是存在的破败,作为社会存在的主体,人民的存在现状及其背后的精神性问题。
阎:是的,作家应该思考的是透过这样一些日常生活,更深刻地表达你对这一时期人的关切,对文学中“人民性”的表达。
张:好多年前,张承志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得很清楚,他说:“我热爱人民,但蔑视庸众。”你刚才讲到的“人民”,我觉得和张承志说的这个“人民”很接近。这是不是一个作家心中的人民的概念?
阎:庸众也是人民的一部分。张承志“蔑视”庸众,表明了他的世界观和文学观,表明了他鲜明的写作立场,这非常可敬。现在,我们写作都已经没有写作立场了。不过,我以为作家写作要保持恒久的对人的尊重,这里说的对人的尊重,自然应该包括我们说的“庸众”。
张:对于许多作家来说,大众、人民、民间、公仆都代表着或象征着文学和写作的真正方向。但在你的“人民”里,应该说具有着一种神圣性的东西。这来自现实中的“活生生”的人民一定是神圣的。
阎:“人民”,一定要有一种神圣性,这是一种对人的尊重和深深的敬意。说我们的小说格局小也好,说作品不够大气也好,归根结底,就是我们的作品中缺少一种“人民性”,缺少对现实中“人民”的那种崇敬感。在小说创作中,一部作品气象的大小,不在于结构,不在于风格,不在于语言是细腻还是粗犷,而在于你对人尊重的深度,对“人民”爱的深度和广度。你的写作情感在你的笔端流露出的爱只是爱某一群人、某一类人,那你的小说即便有最好的结构,最独特的语言,最超常的故事,那也是小气、小格局。可你流露的爱是深刻的,爱是有着“人民性”的爱,即便你的语言、结构,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那你的小说格局仍然是大的格局。同样是经典,同样是名著,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还有托翁的《复活》、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比起卡夫卡的《城堡》、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就小说的气象、格局来说,后者还是不能和前者相比的。为什么卡夫卡、福克纳、博尔赫斯这么容易被学习,模仿?而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等就不能被模仿?因为我们可以模仿别人的故事、语言、风格,但最不能、最无法模仿的恰恰是一个作家对人的爱,不能模仿的是他小说的“人民性”。还有张承志的《心灵史》,你说你如何去模仿?为什么我们现在写不出荡气回肠的作品?除了我们站得不高以外,确实我们的出发点太小、太低。我们的作品中没有大的格局,没有对“人民”的理解和厚爱。
张:也就是说,还是缺少一种带有宗教感的、一种悲悯的大情感和大情怀。这里的爱超出了我们日常所理解的关怀、尊重等等,它是一种非常博大的东西。作家不能从俗世中超拔出来,就很难有大作品。
阎:这个不知道怎样理解,我们中国人没有宗教或者说没有宗教情怀,那我们的文学是不是就永远上不去了呢?如果是这样,我就觉得特别悲观。没有宗教,也会有对人的深厚的尊重,对“人民”深刻的厚爱。
张:宗教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另一种形式,在本质上,是人面对自己的生存境遇,在精神的深层表现出的“终极”关怀,我想知道,作为一个作家,你如何面对一个缺少宗教感的民族?还有,你认为宗教情怀对于一个作家能否写出大作品是很关键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