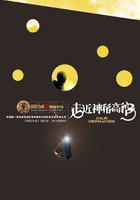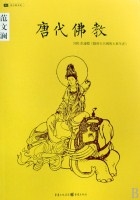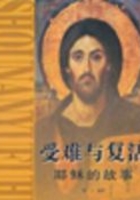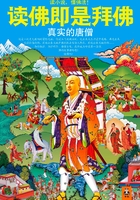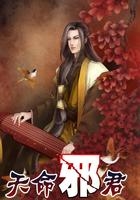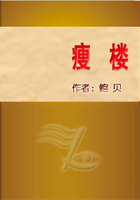天台宗人把三谛、三观和三智圆融起来的基础是“一心”,认为在成佛的境界里,三谛是一心中照,三观是一心中发,三智是一心中成。这样就在意识活动中实现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的融合为一,泯灭了主体和客体的对立。这是一种脱离客观实践的、脱离客观现实的宗教性思维活动,是一种神秘的宗教精神境界。从人类认识史来看,天台宗人的这种学说,反映了在探讨事物的多重性质和主客体统一问题上的尝试和成果,也反映了人类追求无限的、绝对的认识的困惑和努力。
四、真妄心观自慧文以来,经慧思直至智,一直十分重视一心三观法门,其所观的对象是一切事物的真实本相,即空、假、中三种实相。智又把一心三观说发展为三谛圆融说,宣传三谛在一心中得。由此在佛教修持上就要求主体一方面心观照三谛,一方面观心自身。智在《金光明经玄义》广本中提出“观心”,要求心在观照三谛的同时,还要对自身进行反省。这样心又成为了观照的对象。观心是“以心观心”的反观心源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形式。
天台宗人非常重视观心,智强调观心的必要性说:
心是惑本,其义如是。若欲观察,须伐其根,如炙病得穴。今当去丈就尺,去尺就寸,置色等四阴(蕴),但观识阴,识阴者,心是也。(《摩诃止观》卷五上)人由色受想行识五蕴和合而成,其中识蕴即心是迷惑之本。为了观的方便,略去色等四蕴,但观心识,这是最便捷的方法。这样众生就能从根本上整治自身,由迷惑转为悟明。这里智说心就是识蕴,也就是主体的意识、认识,这显然是着眼于自我意识的反思,以调整意识流向,转变意识内容,即由惑转明,由染转净,从而洞照三谛圆融的中道实相。智还规定了观心的十门法观心十法门是:一观不可思议境,二起慈悲心,三巧安止观,四破法遍,五识通塞,六修道品,七对治助开,八知次位,九能安忍,十无法爱。见《摩诃止观》卷五上。,十种境界十种境界是:一阴入界境,二烦恼境,三病患境,四业相境,五魔事境,六禅定境,七诸见境,八增上慢境,九二乘境,十菩萨境。见《摩诃止观》卷五上。。在他看来,观心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观照活动,十种境界是依修行者观照的深浅而呈现出的多种心理变化。
到了宋代,在观心问题上,天台宗内部又衍化成两派的异说和斗争。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作为修观对象的心,是清净的真心,还是染污的妄心?一派称为山外派,主要是晤恩(912—986)的学说。晤恩认为要观照一切事物的实相(法性),应当直接去观照,不必通过观心。另一派称为山家派(自称本宗),主要是知礼(960—1028)的学说。知礼反对山外派的观点,认为观心就是要把所观的道理集中在心上来观,只讲观实相,不讲观心,不把道理集中到心上来观是不对的。后来山外派也承认有观心,但认为实相就是心,观实相就是真观心。实相就是心,所以心是真心,真心是无性恶的。由于观照的对象是真心,因此也称真心观。山外派认为,观照了真心,就不必再观照妄心了;像山家派那样离开实相讲观心,是妄心观,是不对的。山家派则认为,从世俗的“初心”到神圣的“佛心”,中间有着若干阶段,要直接观照实相(真心),这只有在成就佛果时才能达到,或者只有像智那样的“超人”才有可能,对于芸芸众生来说,有着无数的妄惑、执迷,不就这种妄心进行观照,是根本不可能证悟实相的。此派认为,观照俗人的心,就是妄心观。取消妄心观,就是取消观心,是违背止观并重的原则的。
山外派庆昭(963—1017)在争论中逐渐改变了“真心观”的看法。他说:“不独约真心说唯心,亦不须约妄心论唯心,盖约真妄合论说唯心义。”(《四明十义书》卷下)认为心既有真心和妄心之分,就应把两种心合起来论唯心,主张“真妄合论”。山家派知礼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这会混淆真心和妄心的界限,是不正确的。他认为世俗人的心是一体两面,一面是“不变之性”,即佛性;一面是“随缘之心”,即妄心。前者是普遍的、客观的理性方面,是不变的,后者是特殊的、主观的感情方面,是随条件而不断变化的,具有随机性,这两者是不同的、不能调和的。知礼认为应当通过观照妄心,以发现真心(佛性),成就佛果。
真妄心观之辩,主要涉及观照的对象——心的性质问题,实质上是人性善恶的问题,这是在中国古代人性善恶之辩的影响下形成的争论。同时,它也和佛教内部宗派之间的影响直接相关。华严宗主张一心开心真如和心生灭二门,并以如来藏为真心,这就形成真心妄心说,影响到了天台宗人产生真妄观心的分歧。
天台宗人的观心活动,是一种带有道德理性的意识活动,是一种神秘直观。这种直观的特点在于将主体意识设置为观想对象,然后以主体观照功能去审视主体意识,这是一种自我内在心灵的反省活动,是自我超度的活动。应当承认,这种观心活动也是宗教道德修养的一种形式,是在内在心灵展开的去恶从善的修炼。虽然这种善恶有其佛教的特定含义,但是它在消除各种欲念和妄想,改变意识状态,重建主体意识方面确能发生特有的妙用和效果。涅槃、成佛(人格神)是虚幻的,而精神、心理的解脱都是可能的,甚至是现实的。
§§§第五节禅悟
唐代慧能创立的禅宗是我国佛教内部独特的一支,它标榜“教(其他各宗)外别传”,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宗旨,以追求理想人格和人生境界为目标,推行一套排斥语言文字、“以心传心”的,即直观思维的禅悟成佛方法,构成了一种别有风采的直观认知方式。
禅宗的禅悟有一个历史的演变发展过程。慧能首先提倡性净自悟,追求主体对于自身内在本性的复归,以求得主观精神的解脱。慧能《坛经》用中国语言,通俗地阐释了禅悟思想,在中国禅宗史上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后来禅宗大师的主张都是慧能思想的发展变化而已。在慧能以后,禅宗荷泽系禅宗荷泽系,指慧能的晚年弟子神会开创的一系,因神会住河南洛阳荷泽寺而得名。此系经数传后即趋于衰落。宗密主张“知之一字,众妙之门”,而南岳系则加以批评,认为“知之一字,众祸之门”。南岳、青原两系都高扬不立文字,尤其是南岳系马祖道一和青原系石头希迁分别高唱“触类是道”和“即事而真”的禅道,成为禅宗的典型宗风。此后沿着直指心源的道路前进,越来越趋向于舍弃经论的文字,扫除玄句,大辟机用,以求顿悟成佛。青原系下形成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南岳系下形成沩仰、临济两宗,各宗都发挥了各式各样的、丰富多彩的接化方法,如“四照用”、“五位君臣”、“三句”等教学模式,机锋棒喝、超佛越祖甚至呵祖骂佛的教学手段,洋洋大观。到了宋代,禅宗又出现了文字禅、看话禅和默照禅,各呈异彩。
历代禅宗学人经长期禅修实践,形成了大量的“公案”,这些公案表明禅师的基本修持方法是顿悟渐修,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渐修到顿悟,再渐修。也就是说,各种条件没有成熟的学人要在平日重视渐修,准备、创造开悟的条件。对于条件成熟而还没有开悟的学人,要提出疑难问题,或用棒喝手段,猛击一掌,大喝一声,引导学人紧张寻思,激发开悟,寻思时可以和日常行事、感性活动结合起来;开悟后仍要经过严格的勘验,继续渐修,对随时遇到的问题都要作出真切的解释,从实际生活中去锻炼自己的功夫,塑造理想人格,进入新的人生境界。这种禅悟涉及教学方法、认识途径和思维形式等一系列问题,是佛教认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无念、无相、无住禅宗实际创始人慧能倡导的自识本心、自见本性、自成佛道的学说,是以认识、返观众生主体的本心、本性为成佛的根本途径的,因此慧能竭力排斥对外界事物的思维、执著,提出“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敦煌本《坛经》)的三项禅修要求,构成了慧能顿悟说的基本内涵。
(一)无念为宗慧能说:“无念者,于念而不念。”(同上)“无念法者,见一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处,不著一切处。”(同上)“念”,本指记忆,此泛指分别、认识,即思维活动。“无念”的含义有两个要点:一是就主观方面说,心体要离开念,即认识本体,远离一般的思维活动;二是就客观方面说,见一切现象(“一切法”)而又不执著。这就是说,思维时不执著主观思维和客观现象,为无念。其中第二重意义尤为重要,“于外著境,妄念浮云盖覆,自性不能明”(同上)。妄念是执著外境的杂念,无念就是无杂念,强调排除一切杂念。“悟无念法者,见诸佛境界。”(同上)只要悟解这种无念法门,排除一切妄念,就能见佛的境界。无念对于众生成佛具有关键性的意义,所以要以“无念为宗”。“无念”是从否定角度讲的,若从肯定角度讲就是提倡“正念”。“真如即是念之体,念即是真如之用。”(同上)这里所说的念就是正念。真如指万物本性,即众生的本心,本性,佛性。正念是真如本性(体)的自然显现(用)。正念时能使众生的内在本性顿然发露出来,此时也就由迷转悟,成为佛了。无念是对外不执著境,所以要竭力排除世俗的分别、认识,也就是世间的各种概念、判断、推理都应排除净尽。正念是以心念心,直观本心,人在自身内部设置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进行观照活动。在慧能“无念为宗”的命题里,排除一般的感性经验、理性思维与提倡神秘的内在直观是相辅相成的。
(二)无相为体慧能说:“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敦煌本《坛经》)“相”,指一切现象的相状,以及由认识相状而产生的表象、特征。所谓“无相”,是指在接触外界形相时能够离开,即不执著形相,这就是主张在接触客观世界时,不形成感性认识,以免产生对外界的贪恋执取。所谓“离相,性体清净”(同上)。离相就是无相,众生若能做到无相,就能在思想上得到升华,达到性体清净,所以“无相为体”。慧能认为,相是建立在主观心的虚妄分别上的,是人们主观分别的结果。所以“无相”也就是要看到一切现象的无分别性、无差别性。后来有人提出无相讲不通,说释迦牟尼佛就有三十二相,禅宗人解释说释迦牟尼佛三十二相也是人心主观的虚妄之见,佛与众生的差别相、佛相、众生相都应破除,强调众生的自心就是佛,众生的本心与佛并没有区别。
(三)无住为本敦煌本《坛经》说:“无住者,为人本性,念念不住。”“无住”,是指人的本性。
印度佛教讲无住是指一切事物都没有凝固不变的性质,这是一切现象的共性。后来《大乘起信论》以无住为万物本原“真如”的属性,慧能把无住视为人的本性,强调在一切事物上念念无住,不能把意念定住在任何事物上,亦即不把原来的性空的事物执著为实有,这样思想就不会受束缚,而获得解脱。慧能认为,万物都由自心生,如果悟解事物的真性——空性,自心就不会定住在事物上;这种不在事物上定住,不把事物执为实有的心,是从万物中洞察空性的一种智力。这是通过禅修从感性世界中获得的精神超越,是从世俗现实感性经验中得到的思想解脱。
慧能《坛经》所说的“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是禅宗悟道的基本途径,这三者是密切相连的统一整体。其中“无念为宗”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它主张排除一切杂念;排除杂念的根本要求是不能执著一切事物的相状,即“无相”;排除杂念,还要求不在任何事物上定住,执为实有,为“无住”。从认识论来看,就是主张排除世俗认识,排除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或者说,通过直观把握万物的性空和主体的本性,从感性经验中获得升华、超越,进入新的人生境界。
二、触类是道与即事而真慧能提出“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宗旨,要求众生排除杂念,不执著事物的相状,不执著事物为实有,返归自性,顿悟而成佛。慧能所说的众生的自性就是佛性,佛性作为众生的本性,归属于宇宙万物的真如本性,佛性与真如本性是相等相通的。众生体悟宇宙万物的真如本性,也就返归众生的本性,觉悟成佛。这样众生顿悟成佛就集中归结为这样的问题:众生的杂念、执著、行为和万物的本性的关系如何?众生的日常行事与众生的佛性关系怎样?这也就是如何通过禅修顿悟众生和万物的本性问题。围绕着这个主题,慧能门下衍为南岳怀让、马祖道一和青原行思、石头希迁两大系的禅修方式,南岳一系倡导“触类是道”
胡适说,马祖道一禅法的宗旨是“触类是道,任心为修”。见其所作《中国禅学的发展》,载北平《师大月刊》(18),193504。,青原一系主张“即事而真”。
(一)触类是道“触类”是指人平常生活的各种行为、表现,“道”是修行,佛道,佛理。“触类是道”是说禅修者在生活中的任何行为都是修行佛道,都是佛理的自然流露、表现。马祖道一禅师(709—788)是“触类是道”禅法的主要倡导者。道一原主坐禅,怀让特以磨砖不能成镜为喻说明成佛不必坐禅,使他顿然开悟。参见《五灯会元》卷三《南岳怀让禅师》:
“开元中有沙门道一,在衡岳山常习坐禅。师知是法器,往问曰:‘大德坐禅图什么?’一曰:‘图作佛。
’师乃取一砖,于彼庵前石上磨。一曰:‘磨作什么?’师曰:‘磨作镜。’一曰:‘磨砖岂得成镜邪?’师曰:‘磨砖既不成镜,坐禅岂得作佛?’一曰:‘如何即是?’”道一虚心向怀让请教,怀让给以开示,并作偈曰:“心地含诸种,遇泽悉皆萌。三昧华无相,何坏复何成?”言下道一开悟,心意超然。他继承慧能的思想,提倡“即心即佛”说,认为众生心性与佛性没有差别,人的自心即是佛心,自心就是佛。因此人的一切行为也都是佛道、佛性的表现,是一切皆真。马祖高第南泉普愿禅师说“平常心是道”,众生的平常心本来就是佛心,只是因为众生没有觉悟到这一点,随着名言,执著外物,以为实有,形成迷惑;若能一旦回光返照,停止向外追求,返本归源,那就全体都是佛心、佛道,没有别的什么东西;若能了解、觉悟本心就是佛心,那么大道只在目前。禅道触目皆是,行住坐卧、应机接物都合乎佛道,都是佛道的体现。马祖认为,修行成佛的关键在于悟得本心,只要小心护持本心(佛心),使其不受污染,那就不需要另外一些特别的修持,不需要有意识地去做从善止恶的事,只要“纵任心性”、任运自在就是了。如扬眉、动目、哈欠、咳嗽这些小动作,都是佛事。所以,马祖在接引前来禅修的学人时就采用奇特古怪的教学方法。他不用言语文字来讲佛理,而是用打耳光、口喝、脚踢等动作,刺激、诱导门人,教人去思索,返归本心,悟得本心,求得自我解脱。
马祖道一的禅学思想和禅修方式对后世禅宗的影响极大。黄檗希运继承道一的思想和风范,进一步主张“心即是佛,更无别佛。……即心是佛”(《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