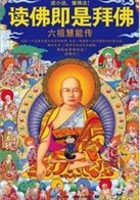不仅如此,“此法即心,心外无法,此心即法,法外无心。……心即是法,法即是心”(同上)。心不是“见闻觉知”,而是“本源清净心,常自圆明遍照”(同上)。也就是宇宙万物的清净本体。希运排斥人们通常的感性和理性的活动,主张直指心源。希运弟子义玄又创立临济宗,形成峻烈的宗风。他提倡大机大用,棒喝齐施,把种种机用和一切言句都安措在剑刃口子上,逼人顿悟。临济宗是在禅宗各派中对修持方式作了最大变革的流派,影响也最大最久。马祖后形成的另一系是沩仰宗,创始人之一沩山灵,也主张“以思无思之妙,返思灵焰之无穷,思尽还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五灯会元》卷九《仰山慧寂禅师》)。强调借寻思的方便以触发顿悟,重视事理并行,识心达本。
(二)即事而真“即事”是不离开日常行事,“真”,真实,本性、道、理、空。“即事而真”是指在禅修时从个别的事象上体悟、显现出性、理、空来。这种禅法和境界是青原行思门下石头希迁(700—790)提出的。相传希迁读僧肇《肇论》中“会万物为己者其唯圣人乎”句,深受启发,于是仿照道家《参同契》,也作《参同契》来发挥禅法。希迁所讲的“参”,指参差互殊的万物各不相犯;“同”是讲万物虽然殊异但又是互相渗透、统一的,是“名异体一”;“契”是说修禅者在日常行事中要体悟、契会万物既异又同的道理。这个理是众生本心所具有的,由此理也就是心、本心。理与事并不相同,理是本,事是末,是有区别的。理与事又不分开,是统一的,要互相联系起来看。修禅者在禅观时要善于从具体的事象上体证全体的理,会末归本,返归本源一心,也就达到“即事而真”的境界。希迁倡导的这种禅法,开辟了青原一系的宗风。
希迁经药山惟俨再传云岩昙晟,又提出“宝镜三昧”法门,主张在禅观时观照万物应当像面临宝镜一样,镜外是形相,镜内是影子,形影对显,形怎样影也就怎样,镜里的影子就是镜外形相的显现,影即是形,这是通过具体事象以显现出理的形象比喻。昙晟用这个比喻来说明希迁倡导的由个别体现全体的境界。希迁禅法的流传,导致后来曹洞、云门和法眼三宗的成立,这些派系的禅法都是“即事而真”宗旨的阐扬。
“触类是道”和“即事而真”是慧能以后禅宗内部的两种禅法、两种宗风。“触类是道”侧重于从道、理着眼,主张理体现到个别的事象上,所见的事象也无不是道。“即事而真”则从客观的事象出发,强调从纷繁复杂的个别事象中看出全体理,所见的各种个别的事无不是理。
从认识论来说,这两种禅法的实质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共同达到理事圆融的境界。这两种禅观涉及认识中的个别与一般、殊相与共相的关系,揭示了不同的认识途径,包含着辩证法因素。
三、四料简、四宾主与四照用临济宗创始人义玄(?—867)继承道一、希运的“触类是道”的思想,进一步宣传一念心觉悟当下就是佛的主张,强调真正修禅人并不着意追求佛果,而是随缘任运,不为外物所拘。他接引学人就从这种根本宗旨出发,棒喝兼施,机锋峻烈,单刀直入,为学人解除所受外物的束缚,以证悟触类都是道的禅理。义玄确定了接受学人的原则、重点、方式、标准等一系列设施,以破除学人对“我”、“法”两种偏见的执著(“我执”、“法执”),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四料简”、“四宾主”和“四照用”。
(一)四料简“料”,度量。“简”,简别。“四料简”,四种简别。这是根据修禅人的不同主观条件(“根器”)和迷悟情况,而采取的有针对性的教授方法。义玄说:“我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人天眼目》卷一)“夺人”,指出人无真正实体,否定对人生的世俗见解,破除众生的“我执”。“夺境”,指出外界事物是空的,破除“法执”。根据学人“我执”和“法执”的情况,对于执著我见为实有的人,着重破除“我执”;对于执著外物为实有的人,着重破除“法执”;对于人生和外物都执著的人,两者都破;对于那种人生和外物都不执著的人,两者都不破。
(二)四宾主“宾”,参学者。“主”,禅师。宾主,即师生,或者说是通禅理者和不通禅理者。“四宾主”是禅师和学人问答的四种情况和结局,区分参禅迷悟的四种类别。区分迷悟的标准是看对人生、外境是否执著,这也是是否体悟禅理的分界线,不执著是主,是悟,执著是宾,是迷。具体说,“宾看主”,禅师不懂禅理,学人懂得禅理;“主看宾”,禅师懂得禅理,学人不懂禅理;“主看主”,师生双方都懂禅理;“宾看宾”,师生双方都不懂禅理。四宾主全面地区分了师生答问的四种类型,是有意义的,但它以否定主客体的客观实在性为禅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片面的、颠倒的主张。
(三)四照用“照”,观照,指对客体的认识。“用”,功用,指对主体的认识。“四照用”就是针对学人对主客体的认识情况而采用的四种不同方式,以分别破除“我执”和“法执”,破除对主客体执为实有的观点。具体地说,“先照后用”,对于执著客体为实有的人,先破“法执”;“先用后照”,对于执著主体为实有的人,先破“我执”;“照用同时”,对于主客体都执著为实有的人,同时破我、法二执;“照用不同时”,对于主客体都不执著为实有的人,给予肯定,不用再破除了,这类人已经获得禅悟,应机接物,触类是道,只要注意修持就是了。
四料简、四宾主和四照用,都是临济宗人接引学人的说教模式,其中四料简和四照用是相近的,都是着重于对主体和客体执为实有的观点的破除。四宾主的区分也以是否破除对主体和客体执为实有为标准。这些做法的目的在于启示学人排除世俗见解,返归本心,见性成佛。这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心性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具体方法因人而异,区别对待,带有鲜明的针对性、灵活性,反映了方法论上的某些规律性。此外,临济宗人的四分法思维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认识的类型、标准和方法的某种特征。
四、曹洞五位与云门三句(一)曹洞五位曹洞宗创始人良价(807—869)和本寂(840—901)继承石头希迁的“即事而真”的观点,吸取《周易》阴阳八卦组合的方法,从事(个别)理(全体)及其交涉关系出发,提出多种五位的说法来接引学人,通过事以显理来指导禅修。曹洞宗的这套说法,世称“曹洞五位”。“五位”,就是五种形式。曹洞五位包括功勋、正偏、君臣等五种形式,其中功勋五位“向、奉、功、共功、功功”,是用以判断禅修的深浅的,而正偏五位、君臣五位则是显示理事关系的,是正与偏、君与臣分别互相配合而构成的形式,也是五位中最为重要、最具有认识论意义的。
正偏五位和君臣五位是:
正中偏君位偏中正臣位正中来君视臣偏中至臣向君兼中到君臣合“正”,指体、空、真、理、净、黑;“偏”,指用、有(色)、俗、事、染、白;“兼”,指非正非偏,亦即中道。“君”与“臣”,是以封建等级称谓喻指正与偏,即君为正位,臣为偏位。正偏、君臣都是中国语言,正、君和偏、臣分别代表事物的主次。从哲学上看,正、君是指世界万有的本体、本性,代表理,偏、臣是指世界千差万殊的现象,代表事。曹洞宗人认为宇宙万有的本原是理(真如、佛性),事(现象)是理的显现。他们根据这种理事关系,运用正偏、君臣互相配合而构成了五种认识形式和教学形式。教学时有敲有唱,要学人从中听出偏正、君臣的区别及相互关系。正偏五位和君臣五位的具体内容是:
“正中偏”,是正中之偏,正位的体具有偏位的用。体是能具,用是所具,能具的体定为君臣五位的君位。习禅者悟解体中的用,从体起用。
“偏中正”,是偏中之正,偏位的用具有正位的体。用是能具,体是所具,能具的用定为君臣五位的臣位。习禅者悟解用中的体,事中的理,觉知一切现象都是真如、空性,摄用归体。
“正中来”,是指一切现象如理随缘而起,是君臣五位的君视臣位。习禅者在此位是由体起用,按照理去修行。
“偏中至”,谓用全合乎体,从现象到本体,是君臣五位的臣向君位。习禅者于此位是终日修而远离修念,终日用而不见功用。
“兼中到”,非正非偏,体用兼到,理事并行,内外和合,是君臣五位的君臣合位,是习禅者的最高果位。
正偏五位和君臣五位是由理与事、本体与现象的回互交错关系而定的,前两位是禅修的初步阶段,三、四位是禅修的较高阶段,第五位是禅修的最高阶段。这也就是习禅者在修行上由浅入深的功勋五位。
正偏五位和君臣五位是对理事、体用关系的五种认识程序和认识模式,依次是体起用,理起事;用具体,事具理;用归体,事归理;用合体,事合理;体用双兼、俱泯,理事并行、同泯。前四种虽然逐渐深化,但都各有所偏。或偏于体、理,或偏于用、事,只有第五位体用兼带、理事圆融,才是最高认识境界和最高解脱境界。曹洞五位体现了曹洞宗人由事见理的认识论观念,第二位“偏中正”,第四位“偏中至”,第五位“兼中到”,都程度不同地反映了这种理事不离、即事而真的主张。
从理论思维来说,曹洞宗的五位说抓住了本体与现象的重大哲学问题,能从本末的角度探索其种种关系,并主张体用合一、理事圆融,这是有意义的,作为一种引导认识逐渐深化的教学方法也确有其独到的细密深刻之处。曹洞宗所说的本体是真如、理、空性、佛性,其内容比较复杂,但就其基本点来说,不是指众生和事物的内在的体,而是指人们头脑中虚构出来的观念,由此展开的理事关系的内涵,也不可能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二)云门三句禅宗青原法系经数传又有文偃(864—949)创立云门宗。文偃上承石头希迁等人的“即事而真”的见解,创设了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这就是文偃的法嗣德山缘密禅师所总结的著名的云门三句:
我有三句语示汝诸人:一句函盖乾坤,一句截断众流,一句随波逐流。
作么生辨?若辨得出,有参学分;若辨不出,长安路上辊辊地。(《五灯会元》卷十五《云门宗·德山缘密禅师》)“函盖乾坤”句,后有颂阐释说:“乾坤并万象,地狱及天堂,物物皆真现,头头总不伤。
”(《人天眼目》卷二)“真”,真如,佛性。这是说,宇宙一切,包括地狱天堂,头头物物,都是真如妙体的显现,都有佛性。这也就是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云门匡真禅师广录》卷中),“一切现成”,不需任何改变。这是云门宗对宇宙万物的生成和本性的总看法。
“截断众流”句,是接引学人认识事物的方法。有颂阐释说:“堆山积岳来,一一尽尘埃。
更拟论玄妙,冰消瓦解摧。”(同上)这是强调纤尘不立,用一句话或一个字回答学人的提问,使之蓦地截断转机,不容拟议,体会真理不可名说,无路可走,转而向内心领悟世间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立,破除各种执著,径直地去体证真如。
“随波逐流”句,也是接引学人的教学方法,有颂阐释说:“辨口利词问,高低总不亏。还如应病药,诊候在临时。”(同上)是说对参学者要根据具体对象的不同情况灵活说法。
云门三句,又称“云门剑”、“吹毛剑”,喻其无比锋利,能斩尽一切妄念、执著,获得思想解脱。所以人称云门宗风是“孤危耸峻,人难凑泊”(《人天眼目》卷二),十分险峻而简洁高古。
云门三句,分别说明了对世界万物的看法和接引参禅者的方法(即所谓“机用”),可以说是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云门三句中贯穿着理事关系的思想。“函盖天地”,合天盖地,融摄一切,是真如,即理。“截断众流”,是一个断面,是事。理是全体,事是个别。通过“截断众流”,体证真如,就是“即事见真”。总之,所谓云门三句,实质上是通过极富特征的直观去体证宇宙本体,使主体返归本性、体悟宇宙本体,进而使主体与客体合一的学说和方法。
五、机锋与棒喝上面我们介绍了慧能以后禅宗各派的独特的认识方式和教学方法,在这些认识方式和教学方法中,禅师普遍运用了“机锋”与“棒喝”的形式,这些形式在晚唐时更发展成为各派的主要教学方式。
(一)机锋“机”,几微,动作之微妙,此指禅机。“锋”,锋利,尤喻语言的锐利。机锋是禅师和学人问答迅捷锐利,语言含蓄微妙,不落迹象,激人证悟的语句。禅师以锐利的语言开导学人,此种教学方法称为“机用”。禅师和学人用锐利语言表达的主题与境界,称为“机境”。
禅师开导学人的一言一行都被认为含有“机要秘诀”,给人以启迪,令人触机生解,称为“禅机”。随着机锋的广泛运用,逐渐形成了固定的师徒答问句式,这些句式的原始记录,不加文字修饰,就成为“语录”。由于这些问答句式的每一条都可作为教学的典型事例,因此后来又有了“公案”。“公案”本来是指公府判断是非的案牍,禅宗认为前辈祖师的问答机缘、言行记录,是一种典型范例,可以用作判断是非迷悟的标准,所以也称之为“公案”,相当于现在的档案。禅宗传灯录编集这类公案达一千七百余条,称为“一千七百则公案”。
后期禅宗学者往往以“拈花微笑”的传说,作为机锋的典范和来源。相传佛祖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说法时,有大梵天王献上金色波罗花,佛祖当即拈花示众,听众默然不解其意,唯独摩诃迦叶破颜微笑。佛祖“拈花”示意,迦叶“微笑”以表领悟,师生心心相印。于是佛祖宣布,这个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法门,付与迦叶。“拈花微笑”被禅宗奉为“以心传心”法门、运用机锋方法的根据,迦叶也被后期禅宗尊为始祖。
禅宗机锋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提问和回答的内容也相当丰富,当时比较集中和广为流行的是两个意义相近的热门话题:“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和“如何是佛法大意”。“祖师”指被奉为东土初祖的菩提达摩禅师。“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是问菩提达摩自西天来中国传授禅法,其禅意究竟如何。如果能了解“西来大意”,也就了解佛祖的禅的本义,修禅也就入门了。所以通常禅宗师徒见面,学人首先问的是这个问题,“公案”里大量记载着这种提问,但回答却是五花八门,没有雷同的。如“庭前柏树子”、“好大灯笼”、“一寸龟毛重九斤”、“破草鞋”、“屎里蛆儿”、“山河大地”、“西来无意”,以及反问“只今是什么意”等,都是“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的答案。
禅宗人修禅毕竟是为了成佛,所以“如何是佛”也是一个常被提及的问题。史载大梅山法常问马祖禅师:“如何是佛?”答:“即心即佛。”后来马祖又改说为“非心非佛”。法常指斥马祖“惑乱”人心,坚持“即心即佛”说。马祖得知后给予充分的肯定,说“梅子熟也”(见《五灯会元》卷第三《大梅法常禅师》)。又如长庆大安问百丈禅师:“学人欲求识佛,何者即是?”答曰:“大似骑牛觅牛。”(《五灯会元》卷四《长庆大安禅师》)意思是自心是佛,不必他求。后来禅宗语录有许多类似的“牧牛话”,如有的说死后要“作一头水牯牛”,有的还绘图拈颂,更有的还摩岩刻石,以广流传。
禅宗机锋语句的特点是含蓄、简短、形象,有的直接回答,多数并不正面回答,教人自己去体会、证悟。如对“西来意”的回答“庭前柏树子”,意在截断学人别觅禅法的思路,强调大道就在眼前,要在日常行事上用功。它重在启发、引导,重在问者内在的觉悟、体证,是一种颇有特色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