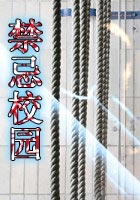罗莎一恢复知觉,刚才会面的全部经过便又浮现在她的脑海中,仿佛在她失去意识的时候,也都一直跟随着她,没有一刻离开过。怎么办呢?她吓得手足无措,只有一个念头是清晰的,那就是一定要远走高飞,逃离这个恐怖的人。
但是哪里还有她的容身之处呢?她又怎么逃走呢?除了海伦娜,她没有将自己对这个人的恐惧透露给任何人。如果她去找海伦娜,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她,这一行动可能会带来无法弥补的灾难,使得他把做出的威胁付诸行动,而她知道他是有这样的能力和决心的。在她的记忆和想象中,他的形象越为令人恐惧,她就感觉到自己的责任也越为重大,因为她明白,只要自己在行动上有任何一点小小的疏忽,或者迟疑,都可能会促使他对海伦娜的弟弟下毒手。
最近过去的这六个月中,罗莎的头脑非常混乱。一种还没有完全形成,更加无法充分说明的怀疑在她的脑海里翻腾,一会儿升到表面,一会儿沉入底部,一会儿清晰可见,一会儿又无影无踪。贾思伯在他的外甥活着的时候,对他关怀得无微不至,在他死后——如果他确实已经死了,又不断地追究死因,在当地闹得满城风雨,因此没有任何人会去怀疑他就是作案凶手。她曾经问过自己这样一个问题:“难道我的思想这样的黑暗,竟然能够想到别人都无法想象到的罪恶行径?”然后她又想到,这一怀疑是否来自事情发生之前她对他的反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恰恰证明它是毫无根据的吗?于是她又思前想后,进行推测:“如果按照我的指控,那么他的动机是什么呢?”她非常羞愧地在心中回答自己说:“动机是为了得到我!”她用双手掩住了脸庞,仿佛把谋杀的动机归结为这一点,与自己无聊的虚荣心不无关系,而这种想法哪怕只有一点影子,也是几乎与谋杀本身同样卑鄙的。
她将他在花园中的日晷旁对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在脑海中反复思考着。他坚持把德鲁德的失踪看做谋杀,这是自从手表和别针被发现以来,与他全部的公开活动相一致的。如果他担心自己的罪行被发现,不是应该支持那个自动出走的设想吗?他甚至宣称过,如果他与他的外甥之间的纽带不那么牢固,他会“甚至把他”从她的身边消灭掉。这是不是说明他真的这样做了?但是他还说过,他要把这六个月来为了正义的复仇所作的努力,丢弃在她的脚下。如果这些努力只是伪装的话,那么他会说这些话,会有这么强烈的感情吗?他会把它们跟他凄凉的内心和灵魂,跟他浪费了的生命,跟他的平静生活,跟他的失望,相提并论吗?他向她献上的第一个承诺,便是他对他那亲爱的孩子死后的忠诚。这些事实那么明确,无疑可以压倒她那几乎不敢触及的想象。然而他仍是这么可怕的一个人!总之,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她怎么会理解这种罪犯的心计呢,这是连专门研究这种问题的人也不甚了解的,因为他们总是试图把它与普通人的普通智慧视为一谈,而不是把它看做独树一帜的骇人心计)怎么也找不到通往其他结论的道路,只知道他是一个可怕的人,必须要躲开他。
在这整个期间,她都是海伦娜的支持者和安慰者。她经常告诉她,她完全相信她的弟弟是无辜的,她同情他的不幸遭遇。但是自从失踪事件发生以来,她就再也没见过他,海伦娜也从没提到过他向克里斯帕克先生所说的那些关于罗莎的话,尽管这件事作为该案中使人觉得兴趣盎然的重要内容,已经流传得众人皆知。对于她来说,他是海伦娜的不幸的弟弟,如此而已,别无其他。她向那个讨厌的追求者控诉的话,完全是真实的,虽然现在她考虑到,她要是当时不提到这点,也许会更好。她怕他,但她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弱小女子,当她想到他是从她自己的口中知道了这一点,又感到非常骄傲。
但是她可以躲去哪里呢?只说是他找不到的地方,这还不能解决问题,还是得找个具体的地点。她决定去找她的监护人,而且准备马上动身。在她与海伦娜第一次促膝谈心的那一晚,她说过她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觉得自己无法躲避他,连修女之家那古老结实的墙壁也不能阻止他像鬼魂一样跟着她,不论她怎样说服自己,也无法压抑心头的恐惧。长期以来,她认为只要自己坚决拒绝就可以,现在这种想法却失去了希望,她感觉,仿佛他有一种可以控制她的魔力。哪怕就在当前,在她起身穿衣的时候,她望向窗外那个他曾经靠在上面诉说心事的日晷仪,仍然令自己不寒而栗。她不敢看向它,仿佛他已经把自身的一些可怕的本质赋予了它。
她匆匆地写了一张纸条,留给特文科里顿小姐,说她临时有急事,要马上去见她的监护人,因此已经动身走了,还请那位好心的老师不必惊慌,因为她一切都平安无事。她匆匆地收拾了一些并没有什么大用处的小物品,装进了一只小手提包,把纸条放在显眼的地方,然后就轻轻地关上大门离开了。
即使是在修道城的马路上,她也是第一次独自一个人行走。但是她熟悉它的每一条小巷、每一个转角,于是便匆匆地径直赶到那个公共马车发车的街角上。这时,马车正要准备驶出。
“乔,请停一下,带上我吧。我得马上去伦敦。”
一转眼她已经上了车,在乔的保护下向火车站驶去。到了那里,乔帮她安全地坐进了火车车厢,还帮她把那个小小的手提包拎了进去,仿佛那是一只大皮箱,有一百来磅重,她自己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拎似的。
“乔,你回去以后,能不能去见一下特文科里顿小姐,告诉她你把我安全地送上了火车?”
“我一定做到,小姐。”
“请代我向她致意,乔。”
“好的,小姐。但愿你对我也能这么好!”不过乔并没有把最后这句话说出口,只是这么想想罢了。
刚才出门太仓促,罗莎没有时间细想,现在她正迫不及待地向着伦敦飞驰,便又有时间继续思考了。她觉得,他表白的爱意玷污了她,她需要用正直和真诚的精神才能洗清这个污点。她感到非常的气愤,这个思想目前支持着她,使她暂时忘记了恐惧,坚定了她匆忙做出的决定。但是当天色越来越黑,那个大都市越来越近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常有的疑虑又开始抬头了。归根结底,这是不是一个轻率的行动?格鲁吉斯先生会怎么想?到了目的地,她能不能找到他?如果他不在,她怎么办?在这么陌生而又人口稠密的地方,她孤零零地一个人会怎么样?如果她等一等,先跟别人商量一下,是不是会更好一些?要是她现在能够回去,她会不会乐于这样做?这许许多多令人不安的疑问越积越多,弄得她心烦意乱。最后,火车终于从层层叠叠的房屋顶上驶进了伦敦,下面是一条条的砾石路。在这炎热明亮的夏夜,街道上已经点起了还并不需要的路灯。
“伦敦斯坦普尔法学会馆,海勒姆·格鲁吉斯先生”。这便是罗莎所知道的全部地址,但是已经足够了。她又坐上了出租马车,摇摇晃晃地驶过荒凉的沙石街道,只见不少人正聚集在院子和小巷的拐角上纳凉,也有不少人在散步,没精打采的脚踩在炎热的铺路石上,发出单调沉闷的声音。总之,所有的人和事物,都显得那么苍白,那么寒酸!
有些地方正在奏乐,但是并不能给这些地方带来丝毫的生气。手摇风琴无济于事,大鼓也无法驱除心头的慌乱。有些地方还有教堂的钟声在此起彼落,但是也仅仅在砖瓦的表面上引起了一些回声,在那一带的地面上激起了一些尘土而已。至于单调的管乐器,由于对乡村生活的怀念,它们似乎已经变得声音沙哑,心灵空虚了。
她那叮叮当当的马车,终于在一道紧闭的大门前停下了。这儿的主人似乎很早就上床休息了,非常害怕有人会破门而入。罗莎打发走了赶车的人,胆怯地敲了敲门,然后拿着小小的手提包,由看门人带进了院子。
“格鲁吉斯先生住在这儿吗?”
“是住在这儿,小姐。”看门人说道,同时向院子的深处指了指。
于是罗莎朝院子的深处走去。这时钟声敲打了十下,她站在P.J.T.的台阶上,心里有些纳闷,不知道P.J.T.跟这大门有什么关系。
她靠墙上标示的格鲁吉斯先生的姓氏指路,走上了楼梯,轻轻地叩了几次门。但是没有人答应。于是她便随手推了推门把手,门开了。她走进了屋子,看到她的监护人正坐在窗口的座位上,窗户开着,一盏有罩的灯放在离他远远的墙角的桌子上。
罗莎在昏暗的灯光中向他走了过去。他看到了她,轻轻地喊了一声:“我的天哪!”
罗莎扑上去钩住了他的脖子,眼泪淌到了脸上。他也抱住了她,说道:“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还以为你是你的母亲呢!”接着,他用安慰的口气说道:“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亲爱的,你为什么到这儿来?是谁陪你来的?”
“没有人陪我来,我是一个人来的。”
“我的上帝!”格鲁吉斯先生喊道,“一个人跑这么远!为什么不写信给我,让我去接你呢?”
“没时间了。这是我临时决定的。可怜的,可怜的埃迪啊!”
“唉,可怜的人,可怜的人啊!”
“他的舅父开口向我求婚。我忍受不了了,”罗莎说着,眼泪又扑扑地掉了下来,小脚丫在地上顿了一下,“我一看到他,便会吓得全身发抖。我来找你保护我,保护我们大家,你愿意吗?”
“当然愿意,”格鲁吉斯先生喊道,突然变得神采奕奕,“这个该死的家伙!让我挫败他的阴暗伎俩,戳穿他的阴谋诡计!他竟然对你垂涎三尺?这个该死的混账东西!”
这么异乎寻常地发了一顿脾气之后,格鲁吉斯先生还是平静不下来,于是在屋子里跑来跑去,看样子简直不知道他是出于一片忠诚,从而愤愤不平,还是好斗成性,想找人吵架。
最后,他终于站住了,抹了把脸,说道:“请你原谅,亲爱的。但是请你放心,我现在好一些了。你暂时不必再跟我说什么,免得我又要大发脾气。你得先吃点东西,高兴高兴。你上一顿吃的是什么?早餐、午餐、正餐、茶点,还是晚餐?现在想要吃什么?早餐、午餐、正餐、茶点,还是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