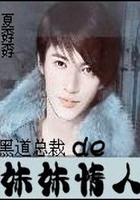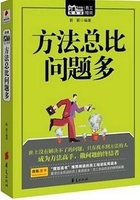他真是体贴入微,在她的面前跪下了一条腿,帮她脱下帽子,解开缠绕在帽子上的漂亮的头发,很有骑士风度。然而,从外表上看,谁会指望格鲁吉斯先生像是一个骑士,而且不是冒牌骑士,却是货真价实的骑士呢?
“还得给你找个安顿的地方,”他继续说道,“我可以替你在弗尼瓦尔会馆找一个最漂亮的房间。关于你的梳妆事务也得安排好,凡是不受限制的贴身使女——我是说,在费用上不受限制的——能办到的一切,你都得有。那是你的包吧?”他盯着看了一会,仿佛在说,在这间灯光昏暗的房间里,要使劲儿地看才能看清楚呢,“亲爱的,这就是你的全部行李?”
“是的,先生。这是我随身带的。”
“这个包可不算大啊,”格鲁吉斯先生坦率地说道,“不过用它来装金丝雀一天的衣食用品,确实绰绰有余了。也许你真的随身带着一只金丝雀?”
罗莎笑了,摇了摇头。
“如果你带来了,它会受到欢迎的,”格鲁吉斯先生说道,“我想,把它挂在外面的钉子上,让它跟斯坦普尔的麻雀比赛唱歌,它一定会高兴的。必须承认,这些麻雀唱得可不像它们指望的那么好。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也是一样!亲爱的,你还没有说要吃什么呢。我看不妨各种都来一点。”
罗莎表示了感谢,但是说她只想喝一杯茶。格鲁吉斯先生跑进跑出了几次,提出了一些补充项目,例如橘皮酱、鸡蛋、水田芹、咸鱼、煎火腿,然后没有戴帽子,便跑到对面弗尼瓦尔会馆去叫了菜。不久一切就送到了,餐桌也摆开了。
“我的天哪!”格鲁吉斯先生喊道,把灯放在桌上,在罗莎对面坐下了,“说真的,这对于一个冥顽不灵的老光棍来说,是多么新奇的感受啊!”
罗莎扬了扬富有表情的细眉,似乎是在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我有一种感觉,仿佛这间屋子已经被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刷得白白的,漆得亮亮的,糊上了壁纸,装饰得金碧辉煌,变得焕然一新了!”格鲁吉斯先生说道,“啊,真好,真好啊!”
然而他的感叹中含有一些伤感的成分,因此罗莎在用茶杯跟他碰杯时,还用小手碰了他一下以表安慰。
“谢谢你,亲爱的,”格鲁吉斯先生说道,“好了,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吧!”
“先生,你一直住在这儿吗?”罗莎问道。
“是的,亲爱的。”
“一直是一个人?”
“一直是一个人。不过白天的时候我有一个同伴,是位先生,姓白扎德,是我的办事员。”
“他不住在这儿?”
“是的,下班后他便走了。事实上,这几天他也不在本地,他出远门了。楼下有一个事务所,我与它有业务来往,它借了一个人给我。但是要想代替白扎德先生,那是很困难的。”
“他一定很喜欢你。”罗莎说道。
“如果他喜欢我,那么他的毅力一定不小,值得钦佩。”格鲁吉斯先生考虑了一下,回答道,“可惜我不相信他喜欢我。不会太喜欢我。要知道,他并不满意,这个可怜的人。”
“他为什么不满意?”这是自然要问的。
“因为他在这里是大材小用了。”格鲁吉斯先生十分神秘地说道。
罗莎的眉毛又发出了疑问,露出了纳闷的表情。
“他的大材小用,让我总是对他感到非常抱歉,”格鲁吉斯先生继续说道,“他也觉得(虽然他从没提起过这点),我应该感到抱歉。”
格鲁吉斯先生这时简直变得神秘莫测了,罗莎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她正在思考这件事,格鲁吉斯先生的情绪突然变得再度高涨了,他开口说道:“还是谈下去吧。我们讲到了白扎德先生。这是一个秘密,而且还是白扎德先生的秘密,但是我的餐桌上居然出现了一个可爱的小姑娘,这令我非常高兴,我觉得我应该毫无保留地把内情都告诉你。你可知道,白扎德先生都做了什么?”
“哎哟!”罗莎喊道,把椅子拉近了一些,心里想起了贾思伯,“他是不是做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他写了一个剧本,”格鲁吉斯先生郑重其事地压低了嗓音说道,“一部悲剧。”
罗莎松了一大口气。
“可是没有人赏识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出版它。”格鲁吉斯先生用同样的声调说道。
罗莎露出了沉思的表情,慢慢地点了点头,似乎在说:有这样的事,可是为什么呢?
“可是,你知道吗,”格鲁吉斯先生接着说道,“我不会写戏剧。”
“连一本蹩脚的也写不出来吗,先生?”罗莎天真地问道,眉毛又在活动了。
“写不出来。如果我被判了死刑,马上就要被斩首,忽然来了一道紧急命令:如果犯人格鲁吉斯能够写出一个剧本,可以免他死罪,那我也只得跑到断头台前,要求刽子手照杀无误,也就是说,”格鲁吉斯先生用手抹了一下脖子,“一斧子把这上头的部分砍掉。”
罗莎心中想到,要是她也碰到这种左右为难的事情,她该怎么办呢?
“因此,”格鲁吉斯先生说道,“在任何情况下,白扎德先生都会认为我不如他。可是现在我是他的老板,你应该能够想到,这种情况就分外严重了。”
格鲁吉斯先生认真地摇了摇头,仿佛觉得这对白扎德的侮辱实在太大了,尽管这是由他本人造成的。
“先生,那么他怎么会在你的手下做事的?”罗莎问道。
“难怪你要这样问,”格鲁吉斯先生说道,“让我们来谈谈吧。白扎德先生的爸爸是诺福克的农民,他的脾气急躁,手边经常放着桩枷、草耙,或者任何可以打人的农具,只要一听到他的儿子在写剧本,就会拿起这些家伙来打他。所以有一天儿子替父亲来交租金时(那片产业是我管理的),把他的秘密告诉了我,向我表明,他立志发挥他的天才,不过这有饿肚子的危险,他适应不了。”
“先生,适应不了发挥他的天才吗?”
“不,亲爱的,”格鲁吉斯先生说道,“适应不了饿肚子的生活。这是不容否认的,白扎德先生对饿肚子的生活不可能适应。因此他指出,我应该保护他,帮助他抵制这种他完全无法适应的命运。就这样,白扎德先生成了我的文书。他对此感触颇深。”
“听到他很感激你,我很高兴。”罗莎说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亲爱的。我是说,他感到非常委屈。白扎德先生后来又认识了其他的一些天才,他们也写悲剧,人家也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出版他们的剧本,于是这些生不逢时的人类精华,互相送上自己的剧本,写上颂扬的献词。白扎德先生也成了这样一篇献词的颂扬对象。可是你知道吗,还从来没有谁把剧本呈献给我呢!”
罗莎望着他,仿佛巴不得拿出一千部剧本来呈献给他。
“这自然也使白扎德先生非常反感。”格鲁吉斯先生说道,“他有时对我很怠慢,我觉得他一定是在想:‘这家伙不学无术,却是我的主人!哪怕判他死刑,他也写不出一部悲剧。绝对不会有人给他写一篇献词,祝福他在后人的眼中将会取得崇高地位的!’这种局面有些尴尬,非常尴尬。不过每当我请他做事的时候,总是会先想一想,‘也许他不乐意做这件事’,或者‘如果我要他去做,他可能会生气’。就这样,我们相处得还不错。真的,比我指望的要好。”
“那么这部悲剧有没有名字呢,先生?”罗莎问道。
“我只告诉你一个人,”格鲁吉斯先生回答道,“它有一个非常恰当的名字,叫做《烦恼之源》。但是白扎德先生希望——我也希望——它最后能够出版。”
他把白扎德的故事讲得这么详细,这是不难理解的,它不仅可以让他保护下的小姑娘分散一下注意力,忘掉那件驱使她来到这儿的事情,同样也能满足他向她表示亲切,跟她随意谈天的要求。“现在,亲爱的,”他言归正传道,“如果你不是太疲倦,能再告诉我一点今天发生的事吗——但是不要太勉强——我很乐意听你讲。如果我在睡前知道这件事,就可以躺在床上好好琢磨琢磨了。”
罗莎的心境平静了下来,她相当忠实地叙述了与贾思伯先生会面的经过。格鲁吉斯先生听她讲的时候,不时地抚摩一下脑袋,有些涉及海伦娜和内维尔的部分,他要求她又讲了一遍。罗莎讲完之后,他严肃地坐在那儿,一言不发,思考了一会儿。
“讲得很清楚,”这是他最后的评语,“我希望能把它清清楚楚地记录在这里,”他说着又抚摩了一次脑袋,然后带她走到打开的窗户旁边,“瞧,亲爱的,他们就住在那边。那边那个没有灯光的窗户。”
“明天我可以去找海伦娜吗?”罗莎问道。
“让我今晚躺在床上再想想。”他回答道,有些迟疑不决,“现在我带你去休息吧,你一定很困了。”
说完,格鲁吉斯先生帮她戴上了帽子,把她那个金丝雀用的小小的提包挂在自己胳臂上,挽着她的手(但是有些不自然,仿佛他准备跟她慢腾腾地跳小步舞似的),跨过荷尔蓬大街,走进了弗尼瓦尔会馆。在会馆门口,他把她交给了那个不受限制的使女头儿,让她上楼去看房间,他说他等在下面,万一她想更换房间,或者想起还有什么别的需要,可以再找他。
罗莎的房间空气充足,整洁舒适,几乎可以说相当华丽。凡是小手提包里缺少的东西,不受限制的使女都给她准备妥当了(那就是说,一切她可能需要的东西)。罗莎又蹦蹦跳跳地跑下了许多级楼梯,向监护人对她周到而又体贴的安排表示了感谢。
“不用客气,亲爱的,”格鲁吉斯先生非常满意地说道,“应该表示感谢的是我,感谢你对我信任,愿意前来找我。明天早上,你可以在一间整洁、精致而且优美的小起居室里(它跟你的娇小身材很相配)用早餐,我会在十点钟前来看你。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我希望你不会感到害怕。”
“哦,不,我感到很安全。”
“是啊,你可以放心,这楼梯是防火的,”格鲁吉斯先生说道,“失火的迹象一旦出现,守夜人就会发现,并且立即把它扑灭。”
“我不是指失火,”罗莎回答道,“我说我觉得安全,是指我感觉自己已经逃出了他的魔掌。”
“这里有结实的大门,门上有牢固的链条,他闯不进屋子。”格鲁吉斯先生微笑着说道,“弗尼瓦尔会馆是不怕失火的,有专人巡夜,灯火通宵不熄,何况我就住在对面。”也许他认为,这最后一点已经提供了足够的保障,她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他的骑士精神是坚定不移的。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他临走时还交代看门的:“万一夜间会馆里有人找我,到对面我的住处送信的,可以拿到一个克朗。”也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他在铁门外踱来踱去,走了将近一个钟头。他显得心事重重,还不时地从链条中间向门里窥探,仿佛他有一只鸽子栖息在狮子笼里的高处,因此老是担心它会掉下来,落进狮子的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