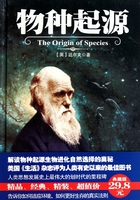五梅观是个小道观,一间正殿,两间配殿,两间舍院,殿前是月牙形的平台,平台正中央便是那棵大银杏树,连同一株五百年的紫薇,把观内遮蔽得阴凉寂静。
听说我要留宿,冷师傅先把我带到舍院,自去厨房烧饭。
舍院有两间,四张床铺。我选了最里面的一张床铺,放下包,摸了摸被褥,铺的和盖的都很厚实,颜色也很家常,淡绿的底子上撒着粉红的小花。只是床铺中央有块红布垫子,一米见方,我猜想是辟邪的,不由生出敬畏心,这儿是敬供神的地方,门上金黄的门帘,梁上的画,都在暗示我这里有着特别的意义。这里也不是稻镇的积觉寺,信和不信都可以进去。不过,我看得出来,稻镇的人并不把积觉寺的当家和尚和庙里的泥金菩萨放在眼里,否则庙前卖八佛经的姜婆婆怎么会在买佛经的人面前信誓旦旦说这佛是她念的,一转过头,咧着烧卖皮一样的嘴对我说,“姑娘,现在大骗子那么多,我这点小骗算什么?是吧?”
我想着姜婆婆鸡窝一样的头,随手拿起床头的小册子,翻到开头。
人心一死,道心自生。人心一动,道心自灭。
我琢磨着,似懂非懂,又翻到最后。
舍钱不如舍身,舍身不如舍心,舍心不如舍性。人能舍掉禀性,就算得道。
仍似懂非懂。听得门前簌簌作响,一头黑狗蹲在门口,如一朵乌黑的云突然降临。我心里一惊,掩上半扇门,然而它只歪头朝我望了会便跑开了。
我洗了脸,去银杏树下。这树真高,真大,平台上的一切都染上了绿色,没有人,只有树上的红丝带在风里轻轻飘着。我感觉自己就像在绿色的风里洗了个澡,突然很想给孔凤兰打个电话,告诉她我这会就在五梅观,就在五梅观的银杏树底下。我还想给王颂打电话。但是他一定会问,“什么事?说吧!”他这么一问,我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我没有事。什么事也没有。我享受够了这种毛孔舒展通体舒适的快乐,往正殿走过去。正殿里供着太上老君,手执仙扇,慈眉善目。要是他知道我此番上山,是为了见冷师傅,为了证明冷师傅不老,不残,心智正常,在山上呆了八年,会不会还这么慈眉善目?
出了正殿,往西走不多远有一尊石龟。别处的石龟都端庄严肃,这尊却是笑呵呵的。看久了,那笑又像含着悲意。我摸摸它,再往前走,已是尽头了,一道石级斜伸向上。走上去,又是一条路,蜿蜒着消失在一丛灌木后。听得冷师傅喊我,我下了石级,她站在石龟前,笑着招呼我,“吃饭了。”
小桌上放着一盘素菜包子,馅是山上的蕨菜,掺了切碎的核桃肉。
“呵,真香。”我说。爬了那一会山,肚子早饿了。
只有我和冷师傅吃饭,刘科长果然没来。
“你尽管吃。到了这儿就跟到了家里一样。”
我应着,有点想哭,这哭的感觉是突然到来的,我习惯了“家里”就是我,墙上挂着我的照片。很多人说我的照片和我本人不像,尤其是那些在“家里”和我共度夜晚的人。他们走的时候都会惊诧地说一句,“怎么跟你一点也不像?”只有我自己知道照片上的我是我的内心。内心和外在是不一样的,即使和我共度过夜晚的人也触摸不到。
我看着冷师傅,她也在看着我。她的目光很奇特,是纯净的,又是虚空的,是锐利的,又是善意的。
她是本身就明朗单纯,不适应山下的浮躁才来这里,还是装满了过去,来这清净之地消解忘怀?我冒失地问,“冷师傅怎么会来这里出家的?”
“我生了场很大病,哪里都看不好。我的师傅把我治好了。我就来了。”冷师傅坦然道。
冷师傅的师傅是另一个观的住持。可是冷师傅生的什么病呢?
“这里原来有一幅壁画。”她指着我身后的墙告诉我,是胶州一个姓宋的画家一生中最得意的画,取名“风竹和雨竹”,听说这两幅画几乎同真的一般,曾有飞鸟投画撞墙而死……
我讶异地回头看看身后悬着几幅字的白墙。想着那些鸟撞向画时,是不是只当自己投进一个风景绝美的地方了,那些绝美的地方并不存在,不,它是存在的,可是只能观赏,不能进入。
我也是那只分不清真相假相的鸟?在往一个不存在的地方飞?我因为找不到,去了稻镇,我在稻镇依旧找不到,又来了五梅观……我希望别人相信我,可又不相信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