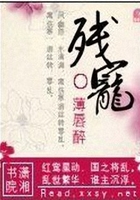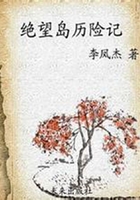落地,便看到已经起来的藤野在朦胧的雾气中练剑。
连忙奔去藤野身边,也不顾他的剑气。
藤野注意到凌泪的气,立马止住动作,等待她的靠近。
“师兄,我们得尽快走了,法拉利惹祸了!”说着将血布移到藤野眼前。
藤野不语,将剑入鞘点点头,随即回房拿来昨晚整理好的包袱。
站到凌泪面前,藤野已换下沾有露水和汗渍的衣衫,换以墨黑长衫。
而圣灵子,听到声响已站在门口,真正意识到他们马上就要离去,眼眶,微微红起。
凌泪与藤野在圣灵子面前端立好,朝着他跪地一拜,后站起身低首抱拳,“师傅,保重!”
“去吧,去吧!”圣灵子两鬓的白发随着清晨的微风扬起,他扭头撇向一边,不忍看到两个心爱的徒弟继大徒弟后又要离去。
以后,这山谷又要沉静了,习惯了他们陪伴的自己,能再度习惯寂寞吗?
凌泪与藤野站起,也不忍再看谷中一草一木,迅速提身离开。这次离去,相见之日在何年?
为法拉利的事着急离去的两人怎么也没想到,这次的分别竟是永别,再见圣灵子时,已是天人永隔。
法拉利见他们出来,对天长啸,两人敏捷地翻身上马,法拉利一窜而出,马蹄声渐渐远去,而他们,似未曾出现过,还这山谷以宁静、与世无争。
短暂的停留,一如,过客的无情。
白色天幕悄然挂上高空,雾气,也渐渐散了去。
可,清晨的凉爽未给他们带来丝毫的凉快,反有点焦躁。
过了那么久,那个人不会已经挂了吧!
要真挂了,法拉利可是欠了一命。欠的必还,她不会还要偿命吧?
而藤野,在思索那个人的同时,心神不宁地吸着鼻下的清香,那是独属于凌泪的体香。
终于,到了茅屋,远远,便见到一颀长的墨黑身体横躺在屋外。
还好,胸有起伏,看来还没完全挂掉。
两人翻身下马,快速前往查看。
男子满脸血污,但不是他自己的血,想必这男子也不是好惹的主,出手也不见留情。然,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为了自己的命,必须狠下毒手,且凭他的穿着物什,也必不会是普通人。
不假思索,凌泪猛地撕开他已然褴褛的衣衫。
没想,处在深度昏迷中的男子察觉到两股不平常的气,虽知没有杀意,但还是强逼自己醒来,迷迷糊糊地看着低首查看自己身子、后抬眼望向自己的凌泪。
凌泪暗自赞赏,这男子实在不一般,随即抬手在他身上“笃笃”两下点了男子的穴道,男子皱眉重新昏睡过去。
“师兄,你来。”凌泪起身,朝着一直站在身边沉思的藤野唤道。
藤野点头,旋即俯身查看。凌泪见势,闪身于一边。
男子身上刀伤剑伤纵横,许多都是旧伤,只是旧伤未好又添新伤罢了。
“心脉,无,重伤。”藤野用两指夹住羽箭,将其截去大半。
瞪了法拉利一眼,无视它委屈的眼神,允自进屋拿疗伤丹药、纱布和清水等。
将这些东西装到盘子里端到藤野身边放好,凌泪又默默回屋倒了两杯清水,一杯拿在左手上,另一杯拿在右手上悠闲地往嘴里送。
她凌泪是没什么良心,这男子死不死其实不关她的事,救过也就算是还了,踢他的是法拉利又不是她。
再说,虽然她的血液是剧毒,但不代表就懂得毒术,她是医毒皆不懂,所以这救命的事只能交给懂得些许医术的师兄了。
而藤野那张面具下的脸则毫无波澜,喂了一粒丹药给男子,迅速拔掉残留在他身体内的箭头,幸亏没射中心房,否则是大罗神仙也难救。
丹药很管用,能暂且止住血液的流通,所以藤野很简单就把伤口处理好了。
“师兄,喝点水。”见那支箭已经拔出,凌泪便将左手上的清水递给藤野。
藤野接过喝了口,将杯子递还给凌泪,将男子打横抱起,“其他,皮外,你,处理。”
凌泪认命地跟着藤野进屋,安分地打来水,用毛巾沾湿,一点点擦拭着男子的脸与身子。
水,换了好几盆,男子身上的血污也终于被擦拭干净。
男子面容姣好,白白净净的,本是一个柔柔的美男子,偏就被锋利剑眉打破这柔弱白面书生样,反显出些许英气和隐隐的霸气。眉轻皱而起,透着隐忍与不堪。
身上除刀伤剑伤外还有鞭伤,那纵横的伤痕让人不禁臆测他的身份。
是大户人家的仆人,或是公子小姐们的玩物?
再看他腹部的伤,啧啧,法拉利果然够拉风,竟然把人踢成这样,没个十天半个月的定是好不了了。
“师兄,这几日我们得守着这个人过了。”凌泪那张普普通通的面皮苦笑着对上藤野的青白玉面具,“我们就去摘些野菜打些野味来给这小子补补吧。”
藤野静默地点头,从怀里掏出丝帕为凌泪擦掉额前细密的汗。
凌泪暗忖:师傅做的这面皮透气性真不错。
看向藤野手中的丝帕,凌泪一阵愕然,这……是她在10岁的时候见藤野手被割伤用来为他包扎的,那四角的四叶草便是证据,他竟然还留着!
意识到不对劲,藤野迅速将丝帕藏在怀里,生怕凌泪抢回。
见状,凌泪笑了起来,“别藏了,都看到了,还藏什么!待会我拿去洗洗,放心,已经给你的我不会拿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