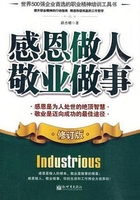厨房倒是干净,李长贵将我介绍给雷鹏,自己就离开了。
雷鹏是个漆黑阴郁的人,高高壮壮的,看上去也不过四十几岁的人,腰背却有些佝偻,一双手青筋暴露,他正在忙碌。
李长贵一走我就笑着打招呼:“雷大叔,您好,我叫秦静,以后请您多多指教了。”然后规规矩矩地作了个长揖。
秦静是我告诉他们的名字,我笑得很真诚,说的话也没错误啊,礼貌上更没差,我以为他也要顺便的客套两句,谁知他看也不看我一眼,将手里拿着的东西一扔,人就出厨房了。
这、这也太直接了一点嘛。
我愕然,反复回想我说过的话,没什么让人误会惹人讨厌的呀,再说现在也并没说有我在这里就解雇了他呀,两个人一起做饭不是减少了劳动强度吗?干嘛摆这脸子给我看,是怪我侵入了他的领地吗?
挥挥头,我对着门口无可奈何地耸耸肩忙我自己的去了。
我做了三菜一汤:一个回锅肉翘头是窝莴头,一个豆腐羹有些麻婆豆腐的味道,一个凉萝卜丝,汤是鸡蛋窝莴叶汤。
大锅大路菜,都是些省工夫的,还都是些现代的家常菜,但我相信味道却不会差,原来好友若敏就常常来我家磳饭就是为了品尝我的好手艺,后来还发展成自己买菜来喝令我做她想吃的菜。
她的鸭霸行为现在想起来反而是一种温馨,让我的心好痛。
这船上连水手、伙计、老爷什么的一共有八十七人,汪老爷自与孙子若男和李长贵一块单独开伙吃饭,余下的八十四人,只吃得眉开眼笑地夸赞,汪若男出来时,回锅肉已经抢完了,他拈得几挟的萝卜丝回舱。
雷鹏也吃了我做的菜,我原以为他是不吃的,虽然他那张千年寒冰脸没有什么变化,不过我注意到他挟菜筷子倒是去得蛮勤的。
我在洗甲板时,李长贵来通知我,从明儿开始小厨房的饭菜我负责了,这就算是立定脚跟了吧。
不过我有些歉意,以前小厨房的饭菜也是雷鹏做,是泥人都有三分的土性,一来就抢人家的饭碗了,怪不得人家对我撂脸子呢。
也许这就是竞争吧,残酷冷漠如自然界的生存法则。
不过随便得罪人也不好,一个馒头还能引发一场血案呢,一个工作吔要是会引起什么大乱子也说不太准。
人心都是肉做的,所以我决定每天除了忙小厨房的事情外,还时常的去帮雷鹏料理大锅伙食。人太空闲了也不太好,尤其是处身在我现在这样的环境下的,空闲了就说明有大把的时间要打发,有大把的时间会乱想,帮人也等于帮已,这名言是秦婧玉说的。
当天晚上我故意的磨磳了很久,又四处看看再拖很久才回航房,与汪若男住的舱房,虽然他只是个孩子,但以后与他住在一起就是好几年的事,我不想让他看出我是女儿身。
以前读花木兰时,就无比疑惑,“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两兔傍地走,安能辩我是雌雄,”这木兰辞写了半天,也没说出个究竟,具体是怎样让人不能辩出雌雄的办法来,有那些。
是我太笨了点嘛?我与他们得同行多少年?
那孩子没有睡,他从被子底下探出头看我,眼睛转啊转的,一脸的无邪。我也看他,一脸意外,我们大眼对小眼,看了好一会,我想到我能留下有一部份职责是要照顾他做他的保姆的。
记得了职责,于是我走过去给他掮了掮被角,拍拍他的肩,柔声说:“快睡吧。”然后我只除去外衣,就上了床,听得那孩子瓮声瓮气地说:“你故意这么晚回房,是因为害怕我看得出你是姐姐吗?”我差点从床上滚了下来。
脑子一下子成了一团浆糊,连个小孩都知道我是女的,我还费心地掩饰个屁呀,我能蒙得住谁呀?“你怎么看出我是姐姐的?”总得问出个究竟来嘛,才好想对策呀。
“是爷爷看出来的,小时候母亲告诉我,我奶奶就是女扮男装出来认识我爷爷的,而且我也是女扮男装的,你没看得出来吗?”小女孩很有些骄傲。
她说的话我一时之间消化不了了,怪不得今天觉得那汪老爷的眼神怪怪的,说不定他也是想到了自己以前的情事,也怪不得他会让我与若男一个舱房,让我照顾她,想不到连女扮男装都会遇上相同志向的人,有够荒谬的。
“你的兰字不是男孩的男而是兰花的兰吧?”我问那女孩,“对哦,姐姐,你做的菜真好吃,以后教教我好不好?爷爷就怕我与伙计们厮混以后没个女孩样,现在有你可太好了。”汪若兰很高兴。
嘿,想不到我的功用这么多呀,怪不得汪老爷要请我吔,现在我又是厨子又是伙计还身兼保姆与行为指导,他准备给我多少银子开我的工钱呢?
怎么我先没想到可以开个好价钱呢?不过我可以在女性这个方面给汪若兰什么好的榜样?这我表示怀疑,以前是常年的大衬衫、牛仔裤的角色,未必还能言传身教出个淑女。
不管了,以后他也只能怪他自己走眼了,对我无论如何来说这也是个好事情,至少掩饰身份没这么困难了。
海上早晨的光景是很美的,我们向着阳光行驶而去,太阳在水面上舞出万道金芒,那光芒是流动的活动的变幻的,就如万条金蛇粼粼蜿蜒延伸到很远很远我们目力所不能及的地方,让人睁不开眼来,有水鸟在飞翔,时不时地停上我们的船帆,有时候也停上甲板,人一走近它们又飞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