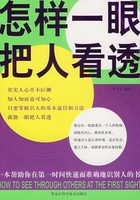“喝花酒包相公?”他重复了一句,果然他的脸如我预期的铁青了,一个小孩子脸上青白交替,有够好瞧的,他冷冷的说:“你这种女人,看怎么嫁得出去。”
“我本身就不想嫁出去,不劳你老人家费心。”嫁人,在现代我都没想到嫁人,未必还巴巴的来这男尊女卑的地方嫁,看着对方三妻四妾来碍我的眼,我又不想早死,还是被酸酸的醋泡着酸死的那种死法,想起来浑身就冒鸡皮疙瘩,止也止不住。
气晕他了,一根手指指着我说:“一夜未归,还没半分后悔,你还是个女人吗?”手指还抖啊抖的,就没别的说辞了吗,太不新鲜了。
我横眼说:“关你什么事,你那只眼睛看到我一夜未归了,你又那只眼看到本小姐不是个女人了,小屁孩管好自己就得了,居然敢在我面前充老大,当老大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教训他,收回拧他脸的手再改为敲了敲他的头,长点记性吧,叩的脆响,这爆粟手劲不小,他抱着头愤愤地盯着我好半晌才无言地转身回房。
我们雇了辆马车回落霞镇,一上马车开始还好,我强撑着与子望说说话,秦天大概是刚才就气饱了气炸气晕了,还虎着一张脸不理人,冰得如同块万年寒冰,我也不理他,摆一张马脸就让我怕他了,好大的笑话。
看看沿途的风景,一路没太大的变化,有些无趣,我缩回头呆坐,然后随着马儿不紧不慢地走着,走着,走着,不多时随着车厢内很有节奏感的晃悠着时,我的瞌睡虫统统的顺隙跑了出来。
很快我的意志就全线崩溃,抗不住睡魔的引诱,进入它甜蜜的瓮中,开始我的眼皮不由自主地合拢在一起,如万年强力胶粘合,我使劲睁开不一刻又合上了,然后我又睁开不一会又闭上,后来也就只好随它了,睁开又闭上也太累是不是。
然后我的头就随着车厢晃动的频律一下下地低下去又一下下的低下去,有时又一下下的左右摆动着,象是给马儿行进的脚步打着拍子,拍子打多了,我想我就睡过去了。
这马车不大,舒适的我也租不起,就是租得起也没必要共花这个钱是不是。
因此这车上放了我们买的布匹和一些车夫给人家带的货后就没多大的空隙,我们三人挤在一起,象沙丁鱼罐头一样。
我是坐在中间的,秦天和子望分坐我左右,子望一路上大多数时间都在呆呆地望着窗外出神,百分百的少女怀春的怔忡症状,有些疯魔。
我想我不打瞌睡都是不可能的,不说是因为昨夜的一晚未睡,就说身边这两人吧,一个出神一个马着张脸又不可能让我分散分散想睡觉的注意力。
我估摸着我是睡着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只到中午打尖时停车我也醒过来,记得睡着时仿佛靠在一个什么温暖的东西上面,那东西是什么呢?不是子望就是秦天了。
吃午饭时我看到秦天的肩头上有一滩水渍,别不是我的梦口水吧,他没提,自然我也是不会提的,也太丢脸了。
不过这小子人还不错,居然没有一掌将我推开,好人啦,好人,顺便的我想问一句,我睡着了会流口水吗?
然后一路无话,回家。
在我们走的这段时间内媚姨将小店照顾得很好,每天的收入很平稳,我们的小店生意上轨道了。
这时已经开春了,她雇了个短工叫什么朱大宝的,是邻村人,负责给我们犁田下种,不过在插秧的关键时分,那个朱大宝忽然的对我们给他的工钱不满意了,要求涨工钱,一天五十文,不二价。
什么跟什么嘛,十村八乡的雇短工,那一个不都是三十文一天,欺负我们这一帮子老弱妇孺吗?
就知道在这个春耕忙碌的时候请不到人,故意的憋屈着我们,算准了我们就算是不服这口气也得按他所要的价给。
就不,我的火气也上来了,滚走吧,我的钱就不塞他那狗洞,活人还得给尿憋死,我就是不受这肮脏气,就不给,要比起损失来,他自己也不小,自作自受吧,他。
朱大宝倒是灰溜溜的走了,我扬眉吐气了吗?
不,没想到自作自受的人也包括了我自己,我原想的是,众人划浆好撑船嘛,一家子八九口,全都上,中国什么都不多人口资源嘛那还是有的,照那样还不是两三下就搞定的事。但预想和实际总有段距离。
让媚姨去种田这件事首先我就搞不定,想不到同样是劳动在她心里还是很有贵贱之分的。
下田啦,不行,那可是粗鲁汉子做的事,她老人家就死活不干,有那家妇道人家下田去露出两条白生生的大腿的,有违妇德呀,想不到她大字不识两个背起妇德来倒是条条有理,这尊神就请不动,我也无颜再去逼迫其他的弱小了,乖乖的自个儿上吧,不是还有个奴仆吗,一起揪着上啰,有什么好客气的。
“你不是说只要我教你家人识字,你就减免我做事吗?而且你不是还说过只要我教你们,你就不能当我是你家的奴仆,而做你的弟弟吗?”秦天不肯就范,搬出我以前在京城里说的话来堵我的嘴。
我他妈的以前怎么这么多话呀。
他现在确实在教这家里的几人学习,不过女孩子们我看都兴致缺缺,我也不好逼迫他们,女子无才就是德嘛,这观念这么的深入人心,我看我是扭不转这个观念的。
但子宝是一定得认真学的,好在全家人都有这个督促他的自觉,因为他是男孩因为他还小因为以后秦家就靠他了,他是一定必须得好好学习的,这不公平待遇让子宝的小嘴巴嘟得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