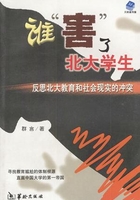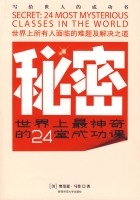所以最初的劳动教养没有期限。它只是改造城镇游民的一种措施,带有预防犯罪的性质。“条例”中说得很明确“劳动教养,是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应当按照其劳动成果发给适当的工资;并且可以酌量扣出其一部分工资,作为其家属赡养费或者本人安家立业的储备金”;“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教养期间,必须遵守劳动教养机关规定的纪律,违反纪律的,应当受到行政处分,违法犯罪的,应当依法处理”;“在教育管理方面,应当采用劳动生产和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并且规定他们必须遵守的纪律和制度,帮助他们建立爱国守法和劳动光荣的观念,学习劳动生产的技术,养成爱好劳动的习惯,使他们成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或者它们委托的机关批准”。在城市里待着,又没有收入,长此以往,不就得干犯法的事吗?
田炳信:就是管制起来了。
王学泰:不是管制。你到那里去,也照样每个月32块钱(这是北京,听说外地就要少得多)。当时劳动教养32块钱,就等于你去就业,给你找工作呀。
田炳信:就是找工作,你也可以叫个好听的名字呢?为什么非叫劳动教养?
王学泰:“教养”这个词现在听着是难听了一点,因为多年以来用它处理轻微犯罪人员。实际上自古以来为统治阶级所用的儒家思想对于老百姓就是主张“养之”“教之”的。何况解放初强调“不劳动者不得食”,有的人甚至把“劳动”就简单地理解为农业劳动,而且这种劳动是最光荣的。那些提笼架鸟的人们在新入城的干部眼中就是“二流子”(反右时,吴祖光“二流堂”事一公布引起许多人的愤慨,就是把这些文人的自嘲视为以“二流子”自豪)。其实“改造”这个词要深究起来好听吗?“脱了裤子割尾巴”,“夹着尾巴老老实实做人”好听吗?不过大家都这么说,习惯了。普希金诗剧《叶甫盖尼·奥涅金》有两句诗说“上帝本没赐给人幸福,习惯就是它的礼物”。我们习惯了也不觉得怎么样了。我们历来不被尊重,被大人物喝来斥去,反复训导,但习惯了也就不以为然了。阿Q当赵太爷尊重他叫他“老Q”时,他还不知道叫谁呢。
田炳信:人最大的特点是,在现实的经度中的缺陷,总喜欢到历史的纬度中去寻找一种慰藉。这是人的一种正常的心理需求,但并不能代替你做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在活生生的社会中的阴阳冷暖。一个时代和一个时代有变化,可是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它的缺陷总会像是一层油垢漂在历史的河面上,这也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一种客观。
王学泰:没错。又说到普希金。他有首抒情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最后一句是“而那逝去的将变为可爱”。这是人性的弱点,人们怀旧时总爱为逝去的时代增添一些诗情,应该宽容,但道理要说清楚。例如有人说五六十年代如何如何好,现在如何如何糟。这种说法的存在,有时还上了媒体,这本身就说明,现在有了些宽容。1957年你这样说一定被划为右派。因为右派言论中一个典型言论就是“今不如昔”论。
当然,人们的诉求有所不同,有的人说五六十年代治安好。有人忘了那种“治安好”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为此又付出了多少代价。那时每个人都属于一个单位,一生荣辱都付给了这个单位。人们在社会上出了问题都要找单位,单位的领导能够决定你一辈子的命运。多少与领导关系不好的人被压得抬不起头来。人们付出的第一条就是人身依附关系。另外当时不停的政治运动,把人们搞得谨小慎微,怕跌到阶级敌人队伍当中去。过去有句话叫“老百姓怕上纲,干部怕上线”。所谓“上纲”就是阶级斗争这个“纲”。一个人被上了“纲”那是吃不了兜着走的。为了这个“治安好”使大多数人都处于危惧之中,这是第二个代价。第三个代价是人际关系的紧张,彼此提防,不敢说心里话,生活无趣。更重要的是这种治理方式大大妨碍了生产的发展,人们都处于贫困之中。那时小偷少,也没东西可偷。那会儿大家全挣四十二块五,买生活必需品大多靠“票”计划供给。马三立说的相声《逗你玩》,那时候偷东西就是偷个布单子,偷个裤子,现在这些算什么。这些使得中国人活得没有尊严。难道现在人们为了一个“治安好”愿意付出这些代价吗?
田炳信:人有约束和没有约束,人负责任和不负责任是大不一样,过去有句话,赤脚的不怕穿鞋的,这话就带有浓厚的游民意识。
王学泰:所以我给游民总结了四条性格,叫游民性格。第一,游民他是具有天然的反社会性的,他希望天下大乱,他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地位。所以胡传奎唱“世乱英雄起四方”,只有世乱这英雄才能出来。
第二就是有主动进击精神,主动向别人进攻。宗法人不成。儒家的思想意识是属于宗法的,他们强调“温良恭俭让”。因此文人士大夫以个性谦和,不与人争为君子。过去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就是指士人先天的软弱性。他们缺少主动精神,进击精神,在历史进程中往往是被动的。“该出手时就出手”,电视剧《水浒传》这首歌词写得非常好,概括出江湖人在社会震荡中的主动精神。宗法人绝对不敢。没有了这种主动精神,临门不敢一脚直射,患得患失,坐失时机。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一般老百姓要遵守社会规范,有家要考虑老婆孩子,即使打架也不敢乱来,可是流氓过来拿砖头就敢往你脑袋上拍。
第三,游民要在社会里争夺属于自己的利益,或是不属于自己的利益时,往往要跟自己相似命运的人结成同伙,他才敢干。游民最简单的结合就是《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复杂的就是明中叶以后出现的秘密帮会。这种结合是他们生存与发展的保障。所以他们很看重这种结合,并成为认可的价值之一。因此这第三点就是只讲敌我,不讲是非。这在《水浒传》中有鲜明的表现。同样的事情比如劫道吧,梁山好汉(包括梁山系统的)做了就是对的,而其他山头干了则是伤天害理。
第四个特征是游民脱离了宗法网络的同时也脱离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宗法文明,而当时又没有其他文明的存在,游民更趋向返回原始的野蛮。游民在社会中没有了角色位置,更缺少社会的尊重与监督,这样他们就不需要社会文明的规范,从而表现出赤裸裸的残暴与野蛮,毫不掩饰地追逐眼前的物质利益,容易流于极端主义和把传统文化非规范的一面推到极端。
田炳信:社会现实生活中,看来不在于你是否是游民,但游民文化、游民意识一旦附在一种所谓崇高的政治意识上,那产生的后果也是灾难性的。在一个人员流动,时空转变越来越快的时代,游民文化的影子是否比过去更加清晰起来?
王学泰:这要历史地看,一百年来,列强敲开国门,宗法制度逐渐解体,游民泛滥,特别是新开放的沿海商埠,如上海、广州成为游民汇聚之所。他们在那里求生存,谋发展,在他们没有接受新的思想时还是传统的游民文化在支配着他们的行为。而传统的游民文化就在江湖艺人演说的通俗小说和他们表演的通俗文艺作品之中,要扩展自己的力量还是“桃园三结义”或兄弟聚义,结为帮会;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还是采取不符合社会规范的手段;要与人斗争不是阴谋诡计就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稳定了,把每个人都纳入了单位。
此时并没有进行公民教育(1954年到1956年刚刚通过《宪法》时,一度进行过法律教育),人们变成类似宗法人的单位人。那时的教育基本上是阶级斗争的教育,“政治正确”是唯一选择的教育。所谓“政治正确”就是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要搞清方向,不要站错队。几十年了,我们这样要求老百姓,至于其他都是“小节”可以忽略不计。可是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来临,老百姓的头脑空了,人们不知道何所皈依。于是沉渣泛起,游民那一套卷土重来。当然说“重来”也不一定准确,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走。许多时候它(如打砸抢行为)是躲藏在革命语汇之后的。革命词语没了就是赤裸裸的游民行为了。
田炳信:游民文化不仅仅是百姓受到影响,有时达官显贵也会受到影响,在某一个时期,一旦变成主流思想,那对整个社会的伤害就大了。
王学泰:宗法社会里不管你受过什么具体的教育,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为什么?因为儒家本身就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表现。不管你读过儒家的书没有,孝的观念,谦和仁爱忠信这些观念是避免不掉的。这是宗法人的一些特征,成了游民这些特征就没有了。这是我们老百姓在中国几千年的宗法社会中主要的文明积淀。这个文明积淀如果没有了,那就全没了。人们常说西方思想泛滥摧毁了儒家思想,这是不确切的。摧毁儒家思想的还有清代极端的皇权专制和游民文化的瓦解。“五四”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失之于简单化,不够深入,对于极端的皇权专制和游民文化缺少揭露与批判。此后使得这些垃圾得以冒充革命思想横行无忌。
田炳信:我也研究过单位问题,也买过几本关于单位的书,所以我认为单位的确很像宗法制度。农村虽然不是单位,但是从公社之后,组织生产队之后,也很像一个单位。它和单位不同的地方就是,保护功能非常差,控制功能非常强。当然我们承认,单位的保护功能还是比较强的。只要你跟单位领导关系搞得好,你即使犯点小错,甚至犯点小罪,他都可以帮你兜过来。所以现在说到单位,有些人是怀念单位的这种保护功能,实际控制功能他不要,他也不喜欢,你说对不?
王学泰:现在老百姓非常厌恶腐败,于是有人就说腐败与改革开放俱来,五六十年代就没有腐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什么是腐败?腐败的本质就是有权者对公共权力的滥用。人们为了生存发展,结合在一起,组成了社会。这样必然要产生出一批人掌握公共权力,为社会服务。现在掌握为公共服务权力的人用它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我们称之为腐败;而五六十年代一些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不为老百姓服务,说假话、空话,迎合上方,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升官发财,这叫不叫腐败?还有一些掌握权力的领导对自己看不顺眼的人加以迫害,这叫不叫腐败?那时一个单位领导如果跟你不对劲,能把你整得死去活来。
凤凰卫视有个栏目叫《人间冷暖》,讲了上海的一个工人,就因为十几块钱,从50年代起就被单位领导送去劳教。劳教了半年时间,因为错误很轻,被解除劳教。那时是劳教有期,就业无期。他在劳教农场就了业,但一有运动就挨整。他想逃跑,跑了又给抓回来,整得更厉害了。文革中,领导把他弄到江西省做农民,但户口在他手里拿着,当地不给他上户口。他拿着户口,又回到上海,此时他把户口丢了。在上海二十多年,他是一个没有户口的黑人。没户口的黑人所经历的种种苦难,那是常人所不堪的……没有户口,他得到的唯一的好处是:一次他被汽车撞了,人们以为撞死了,送到火葬场了。火葬场一看是没有户口的黑人,坚决不给烧,要警察找到户口再烧。过了三天他又醒了,留下一条命。从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出来,一个单位的领导的权威,他能决定人一生的荣辱生死。对于这样的滥用权力者难道不腐败吗?
所以说,改革开放,打破单位垄断,使人有了多种选择的权利,这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当然我们目前还有许多人不习惯自己选择,这是因为我们在单位怀抱中生活得太久了,我们许多能力退化了。另外公民社会还没有形成,这也影响我们公民意识的形成。应该说我们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法制社会,公民社会。每个人都懂得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并能自觉地运用自己的权利,这样的公民才有可能对腐败形成有效的监督。
田炳信:在你的研究领域,你为什么认为游民群体的形成是在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