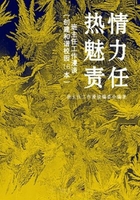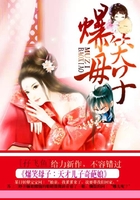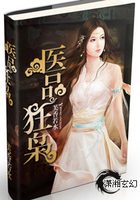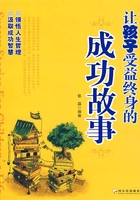由于传统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一直在统一庞大皇权国家承担着重要的结构功能,于是直到17世纪初《利玛窦中国札记》评价中国的制度时,仍然把中国的国家体制是由受过系统教育的知识分子来操纵运行的,作为一个优于欧洲的特点:“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人们“宁愿做最低等的哲学家,也不愿意作最高的武官,他们知道在博得人民的好意和尊重以及在发财致富方面,文官要远远优于武官”。——今天,我们在评价科举乃至更广义的中国传统教育与行政制度的优劣短长时,应该对它们曾经具有的历史作用有一个理解的态度。
不过当我们承认科举对于传统中国文化起到过相当重要作用的时候,同时更应该对于它基本的制度性质及其与近现代教育体制的悖逆之处有清楚的了解。具体罗列起来,这些悖逆之处当然很多,但是我觉得最应该注意的就是在科举乃至皇权时代整个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中,知识的标准、知识谱系的源头只能掌握在权力者手里这一点。说得直白一些,就是有权力就有知识,有权力就有真理,有权力就有道德;或者说,有权力就可以在知识、道德等一切方面对教育和学术耳提面命、颐指气使,就可以按照统治权力的需要来安排教育和学术的内容、方向。明代末年著名的思想家黄宗羲在他的《明夷待访录·学校篇》中有一个很概括的说法:“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擿以为非。” 这个传统当然是因为科举制的长期发展而日益牢固不移,而这样的趋势对于中国教育制度形成自己的体系和尊严,对于教育走出中世纪的阻碍实在是太大了。
王学泰:统治者把住入仕口,也就是做官的门槛,通过选拔和淘汰确立了教育合格标准。你不符合我的需要,不死心塌地臣服于我,你就不要做官嘛。读书人只有通过这个入仕口才能确定自己士大夫的身份。这样即使不外出做官,在家耕读,他也是乡绅。因此,通过科举带动教育的做法本质上是个奴化教育。
王毅:教育和官僚选拔制度的奴性化的确是中国体制的大问题。抗战前夕,王芸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傅斯年曾对他说过一段话:“傅孟真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他想写一篇‘中国官僚论’。他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 ——“姨太太作风”竟然成为了一种制度特征,这是很可怕的。而造成如此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科举对所有读书人思想的牢笼,对他们社会性格和社会角色的强制性塑造。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有一段深刻的话,大意是:在专制国家,教育是在培养坏的国民,但同时他又是在培养好的奴隶;他还说:“专制国家的教育所寻求的是降低人们的心志。专制国家的教育就必须是奴隶性的了。甚至对于处在指挥地位的人们,奴隶性的教育也是有好处的”。而为什么“降低心志”的奴化教育对于身处“指挥地位”的官员们尤其必需,科举发展史可能就是最直接的说明:明初开始,一方面是读书人“不为君用”就要杀头等等;另一方面对于官僚的选拔一定要通过科举这个制度化、标准化的“筛子”,所以除了况钟等极个别的人因为实际行政才干突出而得以升迁为重要地方官员之外,不经科举(“正途”)而进入官僚体系者几乎没有,就说明了这种将知识分子塑造成为标准化工具的制度定式已经多么强劲。
居身于这样大势之下,受教育者、应试者个人是无可奈何的,他只能压制自己而适应这套制度,就像现在无数家长都明白“应试教育”是苦海,但是除了督促自己的孩子加倍努力在这个苦海里面挣扎以外又没有任何办法。晚清曾国藩《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中再三叮咛:“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切嘱切嘱,千万千万”,这是从正面对教育制度原则的强调;而康有为从反面的批评是:“(八股)立法过严,以为代圣立言,体裁宜正,不能旁称诸子而杂其说,不能述引后世而谬其时,故非三代之书不得读,非诸经之说不得览”(《请废八股试帖法试士改用策论折》)——连“诸子”都不能涉猎,可见教育考试制度已经走到何等逼仄狭窄的死路上。
由于选士制度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建立和维系统一皇权体系的运作,所以这一制度对士人知识和能力的考察,也就必然集中在他们是否将“内圣外王”那一套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说与自己的生命和思维融为一体;而一切与维系和强化皇权社会伦理没有直接对应关系的其他知识和技能,就越来越被作为了强化“科举型知识体系”的牺牲品。早在中唐时期学者刘禹锡就指出: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官员往往只是注重儒家伦理而没有起码的具体行政能力(“修身而不能及治者”)。
这种情况当“策论”在科举考试中尚有相当地位的时候,就已经如此,宋代苏轼曾说:近来的读书人,将经史上事例与时务题目编纂在一起,等到考试的时候,用这些鸿篇大论吓唬考官。其实应试者并没有真才实学,于是这样的考试比仅仅以诗文为考试内容弊病更大(《议学校贡举状》)。后来就更是如此,所以明代初年的著名学者宋濂说,当时的学者只知道“以摘经拟题为志”,结果是除了几本经书之外,其余别的知识一概茫然无知,对他说起一件事情,则瞪着两眼,僵着舌头不知如何回答。
王学泰:明清两代的八股,八股是科举制中最受诟病的。其实考八股与科举制度的设计是一致的,对于选拔官吏的作用基本上是正面的。也就是说做八股文是培养这种专制体系下合格官员的重要手段。
为什么选择了八股?这种文章又称经义,就是阐述经书中所体现的儒家思想,要代圣贤立言,也就是设想自己是圣是贤。你想一个人数十年设想自己是圣贤,这种思想意识必然是牢记在头脑里,融化到血液中了,最后还要落实在行动上了,这就所谓的“内圣”。心中除了“圣贤”这一套外,对于其他是一无所知。特别是明清两代,地方官的一些纯技术性的工作分给师爷做了。诉讼有“兵刑”师爷管了;催租收税有“钱谷”师爷管了,连书写公文书信一类的文字都有文案师爷代劳。这些“内圣”的官员把握好原则就可以了。朝廷六部九卿的官僚也是如此,技术性的工作都有吏胥去做,而吏胥几乎是祖辈传流的。因此,南宋的叶适感慨地说“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官不世袭,而吏世袭)。这种胸怀“内圣”的呆瓜做了官,基本上还是守臣子的本分,不会犯上作乱的。这就是“外王”的最低标准。以上是价值上的原因。
还有技术上也就是操作上的原因。
一篇八股七八百字不需长篇大论。全文分为八段,各有程式,考官衡文时容易有共识(本来对于文章好坏很难有共识的,八股则例外。这有些像现代体育竞技中为跳水、体操等项目打分一样。考官可以把一个连续的动作分割为若干片段后一一评判)。另外,八股题目基本上是从《四书》中出。参加考试者有最基础的书——宋儒注的《四书五经》就可以了。如果搞对策,就要比谁读的书多,熟悉历代兴废治乱,那要看多少书?古代没有公共图书馆,书非要自备不可。所以只有考八股文才能最照顾下层有志于读书跃龙门者,相对较为公平。
人们责备八股三大罪状:第一,说八股使人无学无文。八股不是培养文章家、学问家的,它只是培养官僚的。做官僚的首先要熟悉统治者阶级赖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合理性的意识形态。以八股为业,实现的就是这一点。第二,人们说八股束缚思想,的确是束缚思想。但古代从经济上说是农业社会,从人际组织上说是宗法社会。政务相对简单,儒家经籍中基本上告诉了人们如何“牧民”?思想有所束缚对于官来说是必要的。第三,八股最便于乡曲之士,实际上这个制度设计就是想把最底层的读书人也纳入政权系统。这种批评所触及的,恰恰就是八股所以乐于被统治者所用的原因。
王毅:如我们刚才回顾的,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对于发展和维系皇权时代统一完整的制度体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即使是在1898年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吁请光绪废除八股,但是他仍然留恋地陈说中国的科举选士如何远优于欧洲中古的贵族制度,并且是西方现代文官制度的先导——“任官先试,我莫先焉,美国行之,实师于我”。
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上述属性及其与近现代世界教育发展方向的悖逆,其实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由中西教育制度在根基上的区别发展而来的。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到这种区别的关系重大:明代初年国子监的太学生们,对于朱元璋钤束天下臣民之酷虐颇有怨怼,于是有个名叫赵麟的学生带头写了一张没头帖子,朱元璋闻之大怒,查出事情是赵麟所为,于是将他枭首,并在国子监立一长杆,将赵的头颅挂在那里示众。事情过了十年,他的怒气还没有消,一次又召集国子监全体教职员和学生训话,训词原刻南京国子监的碑上,在北京国子监也有一通副本并一直保留了下来:
……敢有抗拒不服,撒泼皮,违犯学规的,若祭酒来奏著凭呵,都不饶,全家发向烟瘴地面去!……今后学规严紧,若有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售,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钦此!
碑的下半段更刻了对国子监工役膳夫的管束规矩以及违规之后的处罚:“打五十竹箅子”、“处斩”、“割了脚筋”等等。因为这类训示最明确地表明了统治权力对于教育制度和受教育者的绝对凌驾,所以后来汪曾祺先生说,它“比历朝皇帝‘崇儒重道’之类的话都要真实得多,有力得多”。
王学泰:科举制是个选官制度,并以此来拉动教育。这种制度普及社会,深入人心,凡是受教育者都把读书当官作为唯一的目标与出路。这样教育也成为一元的、单向度的。由此出发,其评价体系也是一元的,也就是说要求受教育者都能达到掌握“孔孟之绪言”,领悟经典的“精微之奥旨”的程度。这与孔子时还讲求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比起来是远远落后了。孔子的教育反映了当时的知识水平,囊括了当时大部分知识(只是缺少医农);到了科举时代的读书人,不能说全部,但其中的大多数人是除了孔孟的糟粕外,别无所能(如《儒林外史》的范进、周进)。这种教育也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
其一是官位有限,读书人数无穷。读了书做不了官的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宋代就出现江湖游士,靠奔走于官僚豪贵之门为生;明代山人之多成了社会的灾难性问题,因为进入统治阶层的窄路根本无法容纳那么多读书人,所以被挤在外面而又对里面的利益无限艳羡的读书人,就只能采用更加卑微和流氓化的方式寄身于权力阶层的末端以图分一点残羹,这在《万历野获篇》中有生动记载;而读书人的这种生存方式,对于知识和知识阶层应有的尊严,其戕害之大是不言而喻的。清代则更是如此。这些都成为令统治者头痛的问题,但又无法解决。
其二是1840年后,中国在西方列强压迫下逐渐向近代社会转化。社会对知识需求的多样性产生了。外语、声光化电医、军事、政务等等人才不是只通过科考造就出来的。他们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教育培养,于是统治者感到有开办学校的必要。
新式学校,不是明清那种有名无实的学校,这是西方工业社会造就人才的工厂。这种培养人才的方式与中国传统主要靠自己读书的方式来实现是根本不同的。它要通过上学、听课、试验、分科教学等许多种教学方法来系统和批量地培养人才。这种工业化的批量生产人才的方法与农业社会中以手工业方式培养人才的方法是根本不同的。学校与科举不两立,科举的废除成为必然。
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格外曲折以及对其原因的反思
王学泰:1905年废科举后,中国近代教育正式开始。然而,数千年的传统和社会心态也不是说变就变的。从统治者方面说,他们废科举、兴学校,改革教育,无非是培养能够维持其继续统治的能臣(说到底就是培养能适应新的需求的奴才);而老百姓接受教育,无非是读书做官,使自己有个好前途,改换门庭。这样新学校的等级也要用科举来比附,如小学毕业相当于秀才,中学毕业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相当于进士;不仅对国内,对外国回来的留学生也是如此。如对去日本的留学生,如果毕业于文部省管辖的高等学堂的给予举人出身;在大学某专科或数专科的毕业生,则给予进士出身;获得博士学位,则给予翰林。于是后来就有“牙科进士”的笑话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