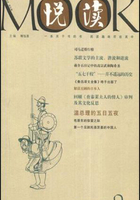他也知道“士可杀而不可辱”,但他又认为士大夫洁身自好,立端行直,就不会出现受辱的现象。如果真是遇到了“昏暴之主”,又触犯了“妇寺之忌”,那么就应该像东林党人高攀龙一样投水而死,而不受辱。这就是这位在野的士人为士大夫设计的一条出路,有点像鲁迅所讽刺的“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走”。他认为绝对的君权是“天下之公理”,不能“以私乱之”;他还认为唐宋一些士大夫关注到自己的权利,这就是“君臣之道丧”,而且是“唐宋之大臣自丧之也”,所以他们应该受到惩罚(上引见《读通鉴论》卷二十二)。明清时代的极端专制正是在“道统”辅助下促成的。“道统”在帮助“治统”建立制度以压制自己,迫害自己。连民间的儒者都作如此想,在朝者谄媚权力更可理解了。
乙:提到王夫之,其实还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地方,比如他总结历史规律时说:百姓平时受暴君和官府百般搜刮欺凌的时候,人人都盼着天降神威,将自己头上的这些压迫者统统诛灭;但是等到社会大动乱来临,百姓们如鸡猪、青蛙、蚯蚓一样被任意宰割,这时候遥想当初自己被官府用刑具锁着追逼租赋的日子,就觉得那是很甜蜜的,而这时再回头看那些暴君和贪官污吏,就会觉得他们如尧舜时代的统治者那样是难得的圣明了(《读通鉴论》卷27)——抛开如何评价王夫之个人不说,只就一个民族的政治理念、历史哲学、对百姓命运的设计等等来看,这个传统中竟然能够堂而皇之产生出如此不惜一切、彻头彻尾以统治权力为归宿的法理逻辑,不是让人毛骨悚然吗?而在这套法理体系从来不会受到认真质疑的环境中,“道统”对“治统”的制衡、对自身固有价值的维护又能有多少实际效果呢?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制度环境,所以“传统”中许多理想的设计都被冷落了下去,而“反文化”的膨胀却在权力需要之下有了最大的驱动力,流波所及几乎涵盖了整个社会。从四五百年前流行的民谚“自古有天理倒没饭吃”“黑心人倒有马儿骑”等,直到今天仍是妇孺皆知的“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无奸不成商”等等,所有这些大家痛心疾首的丑陋现象,其实是出于一种深刻的原因。因此,如果现在真要去动员人们“学习传统”乃至“读经”等等,则号召者自己先应该知道,假如大家正在认真“学”和“读”的时候,偏又遇上凭着芝麻大的权力就可以“摸摸孔圣人头脑”之类事情,那么我们何以自处呢?
甲:“道统”不仅被“治统”随意修正和压抑,以便皇权的极端和任意的伸张,“道统”还被流行于下层社会的游民文化所瓦解。儒家的传统是弥漫在文人士大夫所著述的经籍之中的,它的影响有多大?清代钱大昕说“六经、三史之文,世人不能尽好,间有读之者,仅以供场屋饾饤之用,求通其大义者罕矣”(《与友人书》)。文人士大夫如此,对于下层社会的影响可以想见。对于广大民众影响最大的无非是自宋代以来开始流行的大量的通俗小说和由此改编的戏曲。鲁迅先生就说过“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马上之日记》)。清代史学家钱大昕在其《正俗》一文中指出:“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
”而这个“小说教”所倡导的价值观与儒释道不同。钱大昕又认为儒家自不必说“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以恶。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虽然作者这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说的,我们不必全部接受。但是他说的还是有几分道理的。因为许多小说作者是江湖艺人,而江湖艺人是游民的一部分。游民由于自己的生活处境和经历有了不同于宗法人的思想意识。生存是他们最迫切的追求,为此他们冲破了许多规范,把本来具有非规范倾向的文化推到极端,因此他们缺少是非观念,总以对自己是否有利划线。他们具有反社会性,只有社会动乱才能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些反映到通俗文艺作品中,不仅影响着广大民众,而且也波及到其他阶层。我们看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些保守旧传统的人物,如鲁四老爷、四铭、高尔础又有多少“传统”呢?一切在他们那里都是吃饭之道,求利、求名、求官之道。
所以我以为:传统不仅是被西来的异质文化打倒的,更多的是被游民文化瓦解的。在社会安定时还好一些,在社会动乱时刻,下层社会人们的求生与上层社会的人士安定社会的手段都会不约而同地采用游民的办法,圣经贤传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
乙:“传统”在发展过程中,被我们自己体制的内在因素不断消解,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可能也是我们许多提倡“继承传统”的学者们未能注意到的。多年以来一直有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就是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文化激进主义,是这个运动对西化的提倡和“否定传统”导致了民族精神的缺失。
其实,持这种看法的人对于到了“新文化运动”之前我们的“传统”是一副什么样子未见得了解,所以就愿意把“传统”想象成一种纯粹和理想的东西,可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举一个例子:1900年义和团运动高潮的时候,北京乃至华北都是“传统”的天下,其狂热程度甚至到了有人用了几根火柴(因为是从西方传入的,所以当时叫“洋火”),结果全家八口人都被以“二毛子”的罪名杀死。但是转瞬之间,当八国联军占了北京以后,北京的大街小巷却到处挂满了“顺民”旗,联军设在各街道的衙署里陈设的也都是士人和百姓送去旌扬联军的匾额,送匾者为了使匾额的内容与接受者的身份更为贴切,于是在德军驻地特意都用与“德”字相关的颂辞,如“德兴”、“德昌”、“德永”、“德丰”等等,其他如意、美、英、日等军队驻地也皆是如此。民间也以使用洋货为荣,甚至“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穷裤,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草楷杂糅,拼切舛错,用以自附于洋,昂头掀膺,翘若自喜”。
这种刺目的现象刺激着每一个稍有廉耻心的中国人追问:我们对于自己国家和文化的自信力、我们的“传统”怎么会脆弱衰朽到如此地步?而这也是从清末到“新文化运动”时主张改革的思想家们思考的主要问题之一。比如梁启超在举了“联军入北京,而‘顺民’之旗,户户高悬;‘德政’之伞,署衙千百”的可耻可痛景象之后,指出正是我们自古以来“国民权利”的缺失,才导致了国家和文化信念的崩溃,他的结论很要紧:能够安然忍受专制官府无穷苛索的国民,必然也能够忍受外国侵略者割去我们国家一省土地的耻辱;“其能奴颜婢膝乞怜于权贵之间者,必能悬‘顺民’之旗,箪食壶浆以迎他族之师也”(《新民说·论权利思想》);而后来胡适强调,一个自由的国家不是一群奴隶所能建造起来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可以知道:后人重建对民族传统的自信,这固然是极好的事情,但要想使这一努力获得成功,首要的前提乃是真正摆脱千百年中“(百姓)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的状态;也就是康德所说的“对所有人来说,首先的责任就是进入文明社会状态的关系”。平心而论,近代国门被打开以来的确进来了很多不好、恶劣的东西,但是有一样现在全世界都不得不公认是比较好的东西,除了外来则我们的传统里万万没有,这就是用宪政和法治制度来有效地对付“宁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无权”那样专制欲的膨胀。1621年,英国国王詹姆斯不得不接待十二位代表国民来抗议他专制行为的下院议员,而此时英王要做的准备就是吩咐手下:“你们摆好十二把交椅吧,我要接待十二位国王呢”——统治者非但不能像刘瑾、万历皇帝那样把臣子和草民们吓得尿裤子,还必须根据法律的传统,恭恭敬敬地把被统治者的诉求当一回事,唯有如此前提之下,人们对“道德”“传统”等等的珍视,才能免于随时被踩进专横泥水里的厄运,对社会伦理的建构也才可能有一个必需的良性空间,这个道理并不难懂。
关于中国科举教育制度与
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感想
——废除科举一百周年纪念
2005年是废除科举制度100周年纪念。科举制度自7世纪初实行,至20世纪初废除已经行世1300年,有利有弊,影响巨大。其废除100年后,在一片颂扬传统风中,对科举也多颂扬之词,因此,我和王毅先生有了这篇对话,最初发表在《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9期。
王毅:今年之中,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就是废除科举制度一百周年。
科举被废除虽然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之久了,但是它的影响,它给中国历史留下的许多值得思考之处,这些东西的意义还远远没有消逝。所以恰逢这样的时候,我们似乎可以就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以及科举制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关系作一点讨论。
王学泰: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在这个题目之下,有些什么值得今天特别回味和深入认识的问题。
科举之废与晚清局势
王毅:现在人们对于科举与科举时代的教育和考试制度可能已经感觉十分遥远,举一个例子,汪曾祺先生在1957年发表一篇介绍国子监来龙去脉的散文,文章的开头就说他以前虽去过国子监,但是从外表看不出这座皇权时代国家大学有什么制度要领;他又从首都图书馆借了几十本有关的书来看,还是所得不多;最后他是听了一位当年在国子监当差、侍候过翁同龢、陆润庠等晚清“祭酒”(类似后来的国立大学校长)的杂役聊天中对许多当年情况的介绍,才明白了有关国子监的许多事情。对于传统文化有深厚修养的汪先生尚且如此,别人的情况就不难得知。所以在更具体的讨论之前,还是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废科举的具体过程。
王学泰:一百年前,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1905年9月2日)上谕,接受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六位大臣的吁请,“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也就是说实行了1300年,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影响极深的科举制度就此终结了。这个决定似乎有些突然,主持科举的礼部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刚刚费了好大的力气破除迷信(人们认为明代修贡院而亡国,修贡院不吉利,所以一直任其破败;庚子事变后简直不能用了),准备重修已经很残破不堪的贡院,没想到贡院从此没用了(北京贡院拆毁最早,一进民国就成为居民区了)!
废除科举是件大事,因为它面对的是几十万读书人和一千多年深入人心的影响。戊戌变法时,康梁虽然也提出“兴学校”,但没有敢提“废科举”,那时只提“废八股”(也许这是个策略,因为学校与科举不两立,学校兴,科举必废),“八股”已经作了五百多年,可以说连新的题目都出不来了(清代八股文题目都要用“四书”原文),八股文的“截搭题”(上句之尾与下句之头,凑成的题。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可以截搭为“说乎有朋”)的荒谬,使得这种文体已经弄到人神共愤的地步。
王毅:这种考试方式的荒谬程度,可举一个例子以见一斑:陈独秀在《自传》中记述自己当年参加科举考试的情况,当时出的截搭题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陈独秀回忆说:“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
王学泰:戊戌变法在老佛爷的干预下失败了,“新政”几乎被扫荡殆尽,但戊戌政变后仅两年就是庚子事变,经过事变,转危为安的老佛爷性格有些改变,用唐德刚先生话说“气焰也低了,私欲也少了;年纪也大了,把握也小了。自此军政大事,也不敢乱作主张”(《晚清七十年》)了,对于社会上变革要求逐渐能够感应了。当时热衷新政、兴学校的地方官都切实感到“学校养士”与“科举取士”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宋代徽宗时,搞“三舍法”也一度废科举),长期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首先提出要在十年之内废科举,当时的军机大臣是遇事模棱两可的、人称“琉璃球子”的王文韶在废科举问题上却态度坚决,持反对态度,而且毫不退让,并扬言“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另一个军机大臣是荣禄,他是满人,非科举出身,不好表态,拖到1905年5月,王文韶因老病离开军机处,主张立即废止科举的袁世凯看准了机会,联合端方又拉上张之洞等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废除了科举制度。
科举虽废,余绪犹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