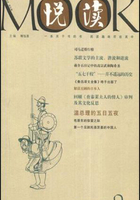主持人:今天我们想请王老师和我们交流的是“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的话题。《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这本书是1999年出版,已故著名学者李慎之先生曾为之作序,以“发现另一个中国”为题,总结该书为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所带来的新的思考。同时,也根据该书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问题: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大传统(士大夫、知识精英们的文化传统)和以关王爷为代表的小传统(游民文化传统),究竟哪个影响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更多一些?根据李慎之先生提出的思考,引申出来的问题是:孔夫子和关王爷是两种完全不同,并且正相对立的文化还是彼此有很深的交织?中国历史上的游民文化和生活准则对理解如今的中国社会是否仍有帮助?今天的“游民”和以往的“游民”有何不同?中国历朝历代如何解决游民问题?如果把视野再拓宽,中国传统的游民文化和西方一些国家的游民文化有何不同?西方国家的游民如何被重新纳入秩序之内?针对这些问题,王老师今天做客和讯读书频道将和网友进行交流。
游民:脱离了宗法秩序的人
主持人:我们首先问王老师第一个问题,请您具体解释一下游民的定义,还有构成游民的各色人等。您在书中说游民形成群体是在宋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呢?
王学泰:首先说一下,我们谈游民问题是有一个历史前提的。这个历史前提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国古代传统的组织方式是宗法社会。从经济、经营角度来说是小农社会。而宗法社会中,人是靠宗法组织起来的,所以说人一生基本上就生活在某地、某个宗法之中,生活在他的家族、宗族之中。这些人我称之宗法人。
另外我们的行政控制自古以来也是非常严谨的,由于行政和宗法的双重控制,正常生活的人们基本上是不流动的,我指的是广大农民和广大手工业者,他们基本上是不流动的,他们终身都生活在一个地方。我是山西人,我50年代回老家去,有的老年人一生连县城都没有去过,他们行为的距离最多在数十里之内。这种社会中,人们必然产生独特的思考方式。
但是游民是脱离了宗族和行政管制的那些人。从儒家的理想来说,社会组织很合乎儒家理想的是无旷土,也没有游民。就是每块土地都耕种到了,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生产的地方。一个人的亲缘关系、血缘关系,甚至包括他的朋友都在他的土地上,所以他很少与外面交流,这样就形成了他独特的思考方式。
但是游民是指什么呢?因为人口不会是固定不变的,人口它要增长,特别是中国古代以来特别注重繁殖,注重传宗接代,所以中国古代的人口基本上是四五十年就翻一番。人口增长了,但是土地没有增长,这就使得一些人占的土地越来越少,逐渐到了临界点,在那块土地不能生存了,他就很自然地被排斥出去了,这就是所谓游民。
儒家的理想是没有游民的,土地与人民的匹配正好合适。但人口增长是动态的,不可能永远正好下去。所以就有游民产生,但游民这个群体在宋代以前是旋生旋灭的,它产生了以后又被消灭了。怎么被消灭了?就是如果别的地方有多余的土地,他就在那里耕种下去,娶妻生子,建立新的宗法。大多游民就会死在道路上。
等到宋代以后,城市发生变化了,使得部分游民在城市中能够谋生和生存了,这种情况在宋代以前是不存在的。唐代的城坊制使一个乡下人进入城市是很难生活下去的,但是到了宋代情况就不同了,宋代的城市结构变化了,改成街巷制了,加上宋代的一些特殊条件——比如说统治阶级的收入非常高,而劳动力又特别地廉价,这样造成了一些大城市经济上的繁荣,工商业的畸形繁荣,特别是消费业和服务业的发达。比如说饮食业和以娱乐为主的一些行业的畸形发展,使得游民进入城镇能够谋取生存,大城市(如汴京、临安)中游民逐渐多了起来,形成了群体。恰恰是在这个时候,也是中国通俗文学成长和发展的时期。所以说我们的通俗文学一产生就跟游民发生了关系,而且演播者、创作者很多都是被宗法排斥出去的游民,游民的想法跟主流社会的宗法人就是不同的。游民的生活环境变化了,他就有了一些跟宗法人不同的其他想法。他这种想法又渗入了我们最早的通俗文学中。
第一代江湖艺人的产生
主持人:您所说的游民,包括各色人等,具体都有些什么人?是什么样的人在创造通俗文学?
王学泰:通俗文学的创造者应该是多少有点文化的人。这与宋代情况非常匹配。宋代的文化有几大变化:第一,它有印刷术了;第二,印书很方便了,人们得到书很容易,在唐代还比较难得;第三,宋代的科举制度与唐代不同,宋代的科举制度采取一系列的政策,就是要在各个阶层当中选拔官员,科举招的人也比唐代多多了。使得一些平民出身的人也有了改换门庭的做官梦,这鼓励更多的人读书。于是,有文化的人多了,但科举取士数目虽然比唐代增长了许多,要与读书人相比,还是很少的。应该说宋代每一个时代都有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在念书,但是真正能做到官的人只有一两万人,宋代最多的时候官吏也不过就是几万人,几万人又不能都从科举制度出来。宋代科举取士最多的是一千人(三年一科),这个数字跟念书人总体数目相比还是比较小的。
那么,宋代有些人有点文化,但对做官绝望了,他就会寻求另外一种谋生制度——可能去为贵族服务,也可能去做帮闲,也可能去创作通俗文学作品。
另外,艺人也是这样。宋代产生了第一代江湖艺人,我们都可以看到江湖艺人的名字很多都有外号。比如说叫酒李一郎,过去他是卖酒出身的;尹常卖,“常卖”就是走街串巷卖小商品的。这些人本来是小买卖人,后来发现自己有演艺方面的才能,转行做了艺人,如演戏、说书等。此前他从事过的行当遂成为其绰号。宋代不仅产生了游民群体,而且还产生了理解和能够表达游民意识的江湖艺人。因为这一代江湖艺人与游民有差不多的生活道路和经历,所以他们创作的通俗文艺作品中描写游民生活和渗透有游民意识是毫不奇怪的。
一治一乱的游民问题:中国的历史轮回
主持人:我在阅读您这本书的时候注意到书中一开始对“游民”和“流民”有所区分。流民是天灾人祸导致的群体性迁徙,虽然他们也是游,但是对于群体的每一个体而言,并没有脱离宗法秩序,因为他们还是在一个群体当中。今天的中国游民可以说与以往不同,流民可以说已经没有了。但是游民变得很多,不仅是乡村人向外游,小城镇的人也在向大城市游。以前如果说在外会问别人“你是哪个单位的”,但是现在大家就会问“你在哪儿混”。这种情况被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的过程,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我想请教您的是,就您的研究,中国历史上游民数量最庞大的时期是什么时候?给统治者造成最大麻烦的是什么时段?当时的统治精英采取了什么样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又是什么阻碍了中国历史上游民的城市化进程?
王学泰: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对于游民我们很难有确切的统计。如果要从人口统计的绝对数字来说,肯定是清代末年游民最多,因为这时候面临着宗法解体,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侵入,使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很难维持。宗法制度是依托于小农经济的,所以宗法制度随小农制度的衰落而瓦解,导致了大批的宗法人的流动——包括上层的一些贵族家庭,一些年轻人也不愿意遵守宗法老旧的统治,他们也要流动起来了,像巴金的《家》《春》《秋》里面写的那些,他们游的方向一般都是上海、日本。
但底层的游民活跃的地区主要是小城镇,到这些小城镇出卖劳动力,也有的到大城市的,但是大城市的容量还是有限,像上海这些地方。因为中国工商业化的大城市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容纳量有限。游民数量激增带来许多问题,但是那时的处理方法很少。当时中国不统一,统治阶级很少有一致的想法来处理这些问题,有些好的想法(如梁启超的想法)也难付诸实施。想要搞革命的人,大多觉得游民是一种最好利用的力量(像阿Q 这样的人很容易被利用),想把这些人团聚起来,纳入革命的圈子,推翻旧的统治,这是一些革命者的想法。
梁启超的想法就是发展产业,使这些人有就业的机会,从无业变成有业,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解决社会的乱源之一的游民问题,中国也才能发展,这是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思考。
应该说过去的条件很难解决这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施过“游民改造”(当时的游民定义主要指没有职业、没有收入和从事不正当职业的人——娼妓、乞丐),并在计划经济原则的指导下实施了社会改造,对社会基层组织重新编制。简单来说就是农村是集体化,城市单位化。把每个人都固定在一定位置上,形象的说法是每个人都是社会这台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这种组织形式短期内使得社会稳定、游民绝迹。其问题是:第一、这种组织形式是依托计划经济体制,某种程度上是妨碍了生产发展,再加上各种政治运动,导致1976年国民经济达到崩溃的边缘。所以为了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基本上摧毁了这种组织形式。第二,这种组织形式实现的是静态稳定,三十年后,中国人口翻了一番,这种体制不变也得变。改革也正是适应了这种“变”的要求。1978年以来的变化逐渐把农民和城市居民从过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农民从“集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包产到户。从人的解放过程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从生产的角度来说,的确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基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但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
城市改革的过程基本也如此,只是更困难一些。在实现向工商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许多企业垮台了;企业重组过程中,大量闲散人员出现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和城市闲散人员构成人数庞大的群体,仿佛像过去社会游民一样引起各个方面的关注。
应该看到既往社会的游民是浮游无根的一群,他们前途无望,挣扎在生死边缘,因而是一种反抗社会的力量,他们希望社会动乱,从而在动乱中改善自己的处境。统治阶级也拿不出有效的办法,解决游民问题。而当前是社会处于转型当中,工商社会发展必然要吸引农村和中小城市的劳动力到各种产业中来,特别是目前中国尚不发达的服务业正在等待大量劳动力的投入。因此经济越发展,社会转型越快,社会上“多余人员”各安其位则会越迅速地实现。
由农耕社会转向工商社会必然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控制体系,这就跟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不同。
这些控制体系应该是什么呢?总的来说就是法制社会,从个体所承担义务和享有权利来看则是公民社会。过去我们所处的是熟人社会(农村人是几辈子相熟,城市中每个单位也是数十年相熟),而现在所处则是陌生社会。熟人社会可以靠道德、舆论,单位靠惩罚制度来控制,那时单位的领导对下属人员享有绝对权力(文革时除外),一个人在外面乘车不排队,反映到你所在的单位都可能造成严重问题。农村也是如此。陌生社会靠什么来控制每个人员呢?方法很多,最根本则是法治。每个人都是社会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享有权利,遵守义务,遵守法律。我们现在已经是世界工厂了,进入工商社会已经是确切无疑的事实了。但在社会控制体系方面,和相应的政治改革方面还没有跟经济发展完全配套,所以现在显得有点混乱,许多应该建立的制度还没有建立或还不完善。
例如与每人相关的社保制度、医保制度,不要说还没有实现全民社保、医保,就是部分城市居民实现了,也有潜在危险(如有权者挪用社保、医保基金)。孟子说“无恒产者无恒心”。解放后我们都变成了“无产者”,那时城市人可以依靠单位,农民尚可依赖那一小块土地。这是当时人的根。随着改革,单位解体,部分农民失去土地,产生了大量“无根的人”。过去的根是很具体的,就是固定在某一个单位或者地方。当然最牢靠的是,每人皆有恒产(没有经济保证的人不会有权)。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大量的“中产者”,如北欧一些国家。但目前尚不可能。其补救方法就是大规模实现社保和医保,使人们不管走到哪里,总是有一根“保险带”在维系着他。这是与社会发展相平行而形成的根,这个根的牢固且被人们坚信(起码这些基金不会被挪用),不是靠某几个人的许愿,需要形成被人们和世界广泛认同法制社会,需要起码的政治改革,如摒弃政治运作的秘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