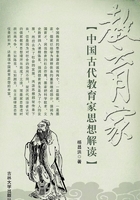评选城市(区)美的风光,最应该关注清洁、特别是空气的清洁度;否则,我们得到的是一场空欢喜。什么时候,站在银锭桥上又可以看到西山了,那时,我们的欣喜将会超过获得任何“最美”的称号。当然,要做到这一步,只靠西城一个区的努力是不够的,必须全北京城集体行动起来。
从标语治国到标语抒情
说实在话,北京建设得益于这次奥运会不少,特别是街区的整治,真是大见成效。许多乱搭乱建的违章建筑、老大难的烂尾工程都得到清扫。我所居住的小区前的街道两旁原来被小商小贩所拥塞,不仅走车困难,连人出门也要蜿蜒蛇行。经过了整治,街道拓宽了,齐整了,小区中的幢幢高楼一律粉刷见新,靓丽光鲜。这些赢得居民的一致认可。最后当主持者美化街道时,却招致许多不满和议论。
有些人很生气,有点“上纲”“上线”:“这不是回到文革去了吗?”“为极‘左’招魂!”“怎么不写点迎奥运的词儿!”听到议论,我出去一看,原来为了美化环境,胡同口和街道两旁涂写了许多标语口号和宣传画,如胡同口立了一面做成“三面红旗”形状的屏障(正逢搞“三面红旗”50周年),上书“心怀祖国,放眼世界”。胡同两旁的墙面:“工业学大庆”;“艰苦朴素”;“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学习‘老三篇’”;“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等,四五十年前流行的标语涂写了数十条,并配以那时流行的“学大庆”“学大寨”“学铁人”“学**”“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锻炼”的宣传画。这些使得一些老同志不高兴,改革开放都三十年了,怎么极“左”的阴魂还不散?是不是有人还要回到文革去?然而,更可气的是单拿出哪条标语你也不能说它错,不能找他说理。但这些标语和宣传画凑在一块儿却构成文革时政治氛围,散发着极“左”气味。这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能感受到的,这使一些人愉快,一些人深以为忧。
我却有点不同的想法,我认为这种现象不足怪、更不足忧。我们曾经有过标语治国的时代,那时写标语、贴标语是政治生活中重要一环。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革当中,建国初制定的法律尽废,国家机器的运转大多靠“最高指示”“领导讲话”和内部的政策条文。这些怎么能让广大群众都知道呢?往往是靠把“指示”“讲话”“政策条文”的精神通俗化、简单化为标语口号,然后贴到城市农村,工厂公社,部队学校,大街小巷,告诫人们警戒遵守。那时没有法,连宪法都被当做一张废纸撕掉,没有作废的大约只有一部《婚姻法》了。史学家唐德刚曾俏皮说那时是“一部婚姻法治天下”,当然,这是笑谈。那时应该是“标语口号治天下”。
由于这些标语都是直接宣传上面精神的,一丝一毫也不能错。记得在大批判时,一条“兴无灭资,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前进”被定为“反动标语”,使我们大吃一惊,我们认识不出它在哪里“反动”?后来传达说反动就反动在“兴无灭资”上。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它却说“兴无灭资”,这是“先立后破”,是与“最高指示”唱反调的,实际上他们是借“立”之名,在反对“破”,反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对文化大革命。可见那时对标语要求多么严格,不仅字词语句不能有错,就连语序都不能稍作改动,几乎每条标语口号都有“微言大义”。对标语口号如此敏感,今人很难想象,因为它们体现了“治国方略”,是“治天下”的工具。
改革开放以来,早在三十年前就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政府通过法律行政,国家依靠法律整合社会。标语口号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渐下降,然而,什么东西行之既久都会产生惯性,全国在“标语治国”环境中运行了几十年,它也会有个惯性在,不会在一个早上消失。另外,在改革过程中还有一些领域相对滞后,例如“运动式工作方法”,就远未消除,一个中心工作来了,总要大轰大嗡一番,开大会,刷标语,表决心就是其中的最有代表性的项目。这些都是标语口号还常常流行的原因。
我们还常常看到不时变换的标语,有时甚至会出现与法律相悖标语口号,错误的标语还常常被网友贴到网上示众。前些日子,听说有人出版了关于标语口号的书,把作者所见的可笑、可怜、可气、可恶、可悲、最后都归为可令人喷饭的标语口号,汇为一编,似乎目的也是为了逗大家一笑,并非是讨伐。标语口号是“对”是“错”,是“好”还是“坏”,以及其中反映了什么心态,编者、受众也不会太关心了,也不把它当做一回事了。即使那些在网上被示众的标语口号也没有得到认真的追究,大多是骂一顿了事。
各种各样令人瞩目的标语口号除了主持者意在告诉上级他在工作以外,好像没有什么其他作用了。我觉得大家应该知道的是,现在还出现了一些抒情式的口号标语,主事者喜欢点什么,他就写点出来贴给大家看,只要不太离谱,也没有人会认真对待。去年,据说有“文明办”的同志把“四书”《三字经》《弟子规》一些片段,语录似的摘出来贴在我所在的小区,听说都是“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等老旧的话头,并号召大家学习。这与新贴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地球也要抖三抖”两相对照,总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的滑稽。但仔细一想,也觉得都可以理解,前者可以说是“古代文人学士”和“新儒家”的弟子,后者有可能是年华逝去的“红卫兵老将”。他们主持了刷标语这件事,把平时郁积想法情绪,大笔一挥,写了出来,贴了出去,大多还是以正面语汇为主,谁也挑不出毛病来。而主持者得到点摅写者的快乐。这种带点抒情意味的标语,可称为“抒情标语”。
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已经沦落成为一种摆设的标语,我们希望它在社会的进步中逐渐被淘汰,但人们也别幻想它很快会消失。它正像子贡非要除去的而孔子又期期以为不可的“告朔之饩羊”。现在一些主事者就颇有点孔老夫子的气味,“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对于“抒情标语”大家要学会适应,有书写权而又怀旧的人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贴出一些营造“红八月”氛围标语,以抒心志,正像《芙蓉镇》里的王秋赦夜深时常常呼喊“运动了”一样。
也说老北京的“梦华录”
说起老北京及其风貌,我们就会想起老舍、金受申、邓云乡……其实,远在台湾还有一批描写老北京并寄托着他们思念的作家。如大家都熟悉的、曾在北京度过了她的青少年时代的林海音先生(林海音的公公夏仁虎先生也是熟悉北京的学者,有《旧京琐记》)。八十年代“上影”出品的《城南旧事》就是根据林先生作品改编的,它感动了几代北京人,连带影片中插曲李叔同先生谱曲作词的《送别》也走红了数十年。家住南小街、抗日战争中在重庆曾与老舍一起说相声的梁实秋先生在《雅舍随笔》中也有大量回忆北京的美文。不仅这些专业作家,就是早年不以写作知名的人士,在他们退休之后,也写下了许多以老北京为题材的散文,在台湾文坛上形成一股浪潮,台湾评论家王德威先生就此介绍说:
1972年春,台湾的《联合报副刊》刊出唐鲁孙(1915—1985)先生的《吃在北平》。这篇文章谈民国时期的北平饮食文化,从福寿堂的翠盖鱼翅到同和堂的天梯鸭掌,从东兴楼的烩鸭条鸭腰加糟、盐爆肚仁、乌鱼蛋汤到什刹海会贤堂的什锦冰碗,外加玉华台汤包、春华楼银丝牛肉、丰泽园糟蒸鸭肝、厚德福糖醋瓦块……正是南北荟萃,如数家珍。唐鲁孙此前并不以文章知名,但他一出手就不同凡响,大家气派、雍容丰瞻,径自流露于字里行间。果然,唐出身八旗世家,少年即遍历故都富贵繁华,之后游走大江南北,以迄来台。晚年他蛰居台北,北望故国,油然而兴莼胪之思,寥寥数笔,已足以让知之者动容,不知者垂涎了。……唐鲁孙的文字在当时颇引起回响。像是号称“老盖仙”的夏元瑜(1913—1995)、名报人及小说家陈纪滢(1915—1997)、学界耆宿梁实秋(1920—1987),以及后来以《喜乐画北平》见知的喜乐(1915—)、小民(1929—)夫妇等,都曾与唐相互唱和。透过他们的文字,旧京的风华仿佛又熠熠生辉起来。
可见当时台湾文坛写老北京和追忆老北京的盛况。这批作者中有两位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唐鲁孙,一是夏元瑜。
唐先生出身于八旗贵族,光绪皇帝的珍妃、瑾妃是他的祖姑,庚子事变时珍妃被害,瑾妃一直活到辛亥之后。唐先生得以追随长辈到宫中会亲,其笔下的清宫旧事,多系亲历亲闻,后曾任公务员、搞厂矿管理,其足迹遍及全国,经历十分丰富。晚年以写散文为消遣,一鸣惊人。夏先生也是名家之后,其父是清末“诗界三杰”之一的夏曾佑先生,其兄夏元瑮是第一代物理学专家,曾任北大理科长(陈独秀是文科长)。夏元瑜本是生物学家,标本制作大师。退休后,放下解剖刀,拿起原子笔,写幽默散文,受到台湾不同阶层、不同年龄段读者喜爱,成为特别拉风的文化人。
记得2002年我参加了社科院与世界龙岗亲义会合办的“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关羽学术研讨会”,在会下,我问一位从台北来的老先生:“夏元瑜先生还写作吗?”不料,他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老盖仙走了。”“老盖仙”是夏先生的绰号(“盖”有能说之意)。这位老先生还说当年一提起“老盖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您要是向人打听老盖仙,人们准是笑着回答,“老盖仙”最近又干什么了(夏先生除了写作,一度还在电视台作嘉宾或主持节目)。可是自从老夏走了后,台湾少了许多笑声,特别是对我们这些老头子来说。我没想到六十多岁才出道的夏元瑜竟有如此大的感召力。
唐、夏二人的文章都是可读性特别强,分析起来,两人也是各有所长。唐的风格是典雅、细腻、生动;夏的风格是流畅、幽默、风趣。
唐鲁孙的文章是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写吃的。这与他的旗人身份有关,旗人经过二百多年铁杆庄稼养着,把常人应有的锐气全磨没了。他在自序中就说,在操觚之前给自己订了一个原则“只谈饮食游乐,不及其他”,因为“如果臧否时事人物,惹些不必要的啰唆,岂不自找麻烦”。虽然“饮食游乐”都是俗事,但唐先生落笔却不俗,时时可见其博雅。如他在回忆北京郎家园所产的各种名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