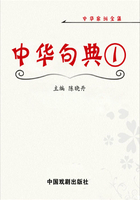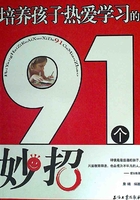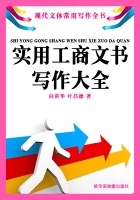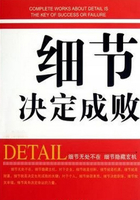一是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影片。转到一监不到一个月主席逝世,接着就是“四人帮”垮台。本来“反击右倾翻案风”该刹车了,但北京的运动并未停止。那时旧电影(1966年以前拍摄的)大多没有解放,社会上放的电影也多是1975、1976年间拍摄的。经过文革,文艺政治化搞到极端,当时最大的政治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因此这时的影片内容就是谎言的汇聚,是对观众智力的侮辱,也不妨说是一种测验。有个片子的名字记不清了,但它的第一个镜头,即使过了30年仍然记忆如新:一个革命派的姑娘,风风火火,怒气冲天,从岸边跳上一只小船,一把抓住船上一男人的肩头,刺啦一声,撕下一大块布来。这是一个大特写。
原来这位女革命派阻拦其男朋友进城做小买卖,“搞资本主义”。这位女士的形象就是当时极其时髦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角色。另一个就是《欢腾的小凉河》,这是个针对性很强的政治片。影片中有个“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一出场就是要“整顿”,要以“三项指示为纲”,要搞“四个现代化”等等一类大多数民众听着合理,却被主流舆论狠批的口号。这个副主任在外在造型上都模仿邓小平,留着小平头(“四五”之后,“小平头”就成为一种“反动”的政治意象),穿着藏蓝色的中山装,并在与无产阶级革命派争论时,引“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句邓氏名言。虽然影片把这个副主任当做反面人物来塑造,但他颇具气势,言辞尖锐,与造反派辩论时侃侃而谈,影片想贬损这个人物,反而增加了我们普通观众对他的好感。
印象最深的影片是1975年中国新闻纪录影片厂拍摄的访问“民主柬埔寨”的纪录片。这个片子很长,分上下集,大约有三个小时。我很佩服拍摄者的毅力,这样一个没有色彩、没有欢笑的空间,他们居然能够专心致志地审视那么长时间。当时柬埔寨内,人们穿的一律是黑色(仿佛是秦始皇时代的“尚黑”),无论男女,女的只比男的多一条黑围巾。不过这让一监犯人(犯人服装都是黑色)感到亲切,看看银幕,再瞅瞅衣裤,真有“天下同此一色”之感。
歌舞团的演出也一律着黑装,其歌唱如诵佛经,不知是佛诵取法于柬地民歌,还是柬埔寨人由于深信释迦惯用佛音梵呗以表达情怀呢?舞蹈只是顿足扬臂,颇具古风。女舞者持镰刀,男扬斧头,两者携手,就是工农团结;举枪展臂,昂首扬眉,便是消灭敌人。一看就懂,非常大众化。
影片中的首都金边,更令人惊讶,宽阔的大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只有军用卡车往来疾驰,扬起阵阵沙尘,大约革命政府的车子在执行任务。这个片子中给我印象最深的镜头是一位十来岁的小革命军人。这个孩子大约也就一米三四高,穿一身工作服,面无表情、专心致志地在车床上加工机器零件。因为个子矮,只得站在一个肥皂箱上工作,车床旁边还竖着一支冲锋枪。旁白说,这个孩子六七岁时父母被美帝国主义者杀死,为了报仇,他参加了红色高棉革命部队,用枪打击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为革命建立了功勋。现在革命胜利了,他放下武器,拿起工具为柬埔寨的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工作,再立新功。当时还不知道柬埔寨发生了人间浩劫,但我想这样小的孩子,如果在革命战火中没有条件上学的话,革命胜利了,为什么不让他们读书呢?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根本没有学校了,因为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地方,统统被取缔了。
电影这种有刺激的娱乐往往会引起犯人的遐想,特别是1977年下半年,旧电影开放了,许多电影的放映都能带来点震撼。例如“政治犯” (当时不承认有政治犯,因为刑法中有“反革命罪”,“反革命”也是刑事犯罪)对影片的政治含义很敏感。改革开放前,中国文艺、学术都是政治信号,开放旧电影简直就是发布政治信号。荧屏播放了写海瑞的湘剧影片《生死牌》是一声春雷,大家议论,文革中第一个倒霉者吴晗要平反了,文革有点儿站不住脚了,彭总也要重新评价了;放《林家铺子》知道所谓“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又快成为文艺红线了……政治是个谜,时时放出些微信息让大家“猜一猜,谁来吃晚餐”。这真是一种益智活动,连监狱的犯人也能半公开地参加。
文革中拍的“革命电影”特别适合监狱中放映,因为影片中一律孤男寡女,不食人间烟火,不会引起犯人的遐想,有利于思想改造。因此,我想,当时积极提倡的“为工农兵服务”,似乎也没忘了犯人,也是为犯人服务。可是文革前的影片中还一些是有点爱情内容的,尽管这已经是“革命+爱情”,或“劳动+爱情”了,最不济也是爱情不忘革命,爱情不忘劳动,与现在拍的爱情片根本不是一回事。但就剂量甚微的爱情也有副作用,足以使一些定力不足者心动。
有一次放完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这是一个歌颂大跃进农民改天换地的影片。其中女主人公孔淑贞,很是抢眼。第二天一早在三角院洗脸时,碰到大老黑,他拿着一块新的花毛巾擦他那张黑脸,因为对比鲜明,我不禁赞叹“真花啊”!大老黑用手拍着毛巾说“知道吗?孔淑贞给的”!我笑了说“你真是至死不悟啊”!他案子在北京很有名。老黑本是某工厂的书记,当过兵,去过朝鲜,为人嘻嘻哈哈,很豪爽,很有人缘。家在河北农村,独居北京,平时与工人打成一片,没大没小,偶尔失足,与食堂女炊事员发生关系。
70年代的北京“备战备荒”,挖了许多地道,这位女炊事员常值夜班,卖完夜宵后,常常从地道溜进老黑的办公室,宵入晨出,“来非空言去绝踪”,很是秘密,真是“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后来,终于被女炊事员的男友知道了,气愤异常,要去捉奸。老黑厂里的朋友、耳目多,马上把这件事告诉了他。老黑把电灯的火线接到门把上,想电来人一下。没想到那天恰好下雨,电工怕穿胶鞋出声,光着脚板,提着鞋去捉奸,一拉门把,陡然中电,因无防备,猝然摔倒。老黑知道出事,抱着电工抢救,不治而死。最后老黑被判“死缓”,老黑劳动表现好,乐于助人,又由于当时判得有些重,缓刑期满直接改为18年(一般是改为无期),不久又减两年。是不是女炊事员就是他的孔淑贞呢?没有探究过。
娱乐记往录
各个龄段的人们都有娱乐,但只有青少年时的娱乐才会在生命上留下深刻痕迹。我是个过早地结束了青年时代的人,一轮轮的政治运动、厄运都没有忘了关照我,要是买奖券能碰到这样运气多好(我也没买过奖券)。1964年被批判、定为反动学生,1965年发配劳改农场监督劳动。当时曾有诗云“此生二十三回秋,唯有此秋偏淹留”。23岁就开始了生命的秋天,还谈什么娱乐?年近不惑,摆脱厄运之后,又为谋生而奔忙,失去了静下心来欣赏艺术的耐力,逐渐也就失去了欣赏艺术能力。
80年代,我供职于文学所《文学遗产》期刊。有一天中午正在编辑部看稿子,所里科研处打电话叫我马上去到首都剧场去看日本能乐演出。我不想去,科研处同志说:“这是文化部发的票,我们所里十几张票,没人去,上头要批评的。”于是只好奉命前往。
过去我都没有听说过“能乐”这个词,懵懵懂懂到了剧场,演出正好刚开始,偌大的剧场没有多少人,显得空空荡荡。我脑子里还回荡着第二天《文学遗产》的发稿问题,有几篇还没有“齐、清、定”(这是对送交印刷厂之前对稿件三项要求)呢。此时根本没有放松看戏的心情,只见舞台上几位穿浅色和服的演员像鬼魂一样飘动。“能乐”是日本的国粹,但我真的没有能力欣赏,演员戴着面具,动作缓慢,一招一式,仿佛是电影的慢镜头;伴奏尤其令人烦闷。三只鼓(大中小),节奏单调,还有一只短笛,但音似乎走调,有点沙哑,这情景要写在诗中很好,唐人有“短笛无腔信口吹”的名句。可是到了现实中,耳朵是受了很大委屈的。
剧情要比昆曲和京剧还慢,剧中人拖着长腔对话,一句述说很紧迫的事情的句子也要拉长腔,真是对性情的折磨。最后实在忍不下去了,悄悄地弯着腰离开座位,趁人不注意时溜号。不料到了门口,发现门被反锁了起来。旁边的剧场工作人员低声但颇有点严厉地说:“对外宾要有礼貌,遵守外事纪律!”这居然是外事活动!鲁迅曾说到他家乡的戏班——“群玉班”,名实不符,没有人要看。乡民们编过一支歌:“台上群玉班,台下都走散。连忙关庙门,两边墙壁都爬塌。连忙扯得牢,只剩下一担馄饨担。”这场演出,幸亏早早地关了大门,否则连馄饨摊也没有。当然这不是说人家演得不好,而是说这种艺术形式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太陌生了。
从这件事上,也感觉到工作紧张已经使我失去了欣赏艺术的心境,对于一时难以进入其境界的艺术缺少耐心。其实上大学时不是这样的。有一年纪念肖邦,在音乐厅听波兰女钢琴家的演奏,也完全不懂,但静心听下来,还是有些感悟的。困难时期,中央音乐学院学生每星期日都有音乐会,一毛钱一张票,有时是整场的交响乐,我不懂也去听,贝多芬的“田园交响”就是在那里听的。那时是学生,困难时期的政策也稍稍宽松(文艺界尤松),没有烦心事,听戏、看电影、听音乐既是娱乐身心,也是增长知识和提高审美能力。在有压力的生活的情况下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了。几十年了,几乎没有进过电影院、剧场、音乐厅,而且逐渐失去了涉足娱乐场所的兴趣,不想去了。不用说花上几百元买门票,就是白送票也要顾虑重重,天冷、天热、散戏后如何回家都成了不想去的理由。
前几年写过一组文章叫做《看电影的记忆》,文中曾说看电影是北京人最普通、也最普及的娱乐活动,但这只限定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包括文革),至于建国前则不是这样。那时最大众化的娱乐活动则是听戏和看“玩意(儿)”(指曲艺与杂技,这个称呼对艺人有污辱性,逐渐被淘汰)。看电影则是新派人物和青年学生的营生,为老派人物以及社会普通人所不取。四十年前,有次向电影导演的郭宝昌请教有关电影的问题,他家是旧式家庭出身,不赞成子弟们看电影,可是他却阴错阳差干了电影这一行,干得还挺起劲。他说:“有一次几个青年人商量看某个片子,老太爷病卧床榻听到了,颤颤巍巍地高声制止:‘不要去看电影,那里面有kiss!’”其他的老北京虽然不一定会说这样的话,但总觉得看电影的都是轻浮子弟,甚至是洋场恶少的嗜好,庄重的人、老实人不应该涉足那个男女混杂而又黑洞洞的神秘世界。至于听戏、捧角、戏迷的紧跟不舍地跟踪盯梢当红“角”都发生在光明正大的世界,谁也不觉得那么下作,还被看做是风流。
“听戏”主要指听京剧;昆曲虽然也有听,但其主要观众是从江浙一带来的文人;梆子(主要是河北梆子)还有一定的叫座率,但主要是周遭进京的农民欣赏;评剧则是没文化的家庭妇女和老太太陪着戏里的主人公一起去掉泪(评戏多是苦戏,如《烧骨记》《杨三姐告状》《杀子报》等);而京剧则是雅俗共赏的,全体北京人都喜欢,特别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
为什么不叫“看戏”而称“听戏”?北京的老戏园子最初都是酒楼茶肆兼营的,既然是茶楼酒肆,方桌必不可少。茶酒吃食都摆放在桌子上,客人围在方桌的四周一边吃喝、一边聊天、一边听戏。他们大都不是面对舞台的,只是闷头听,遇到精彩处,抬起头来,抻着脖子叫一声“好”!以说明他们是知音的。因此早期的京剧(京剧这个词是建国后发明的。起初有“乱弹”“皮黄”“二黄”“国剧”“平剧”等名称)注重唱、不太注重表演。小时候,要是说“我去看戏”还要受人讥笑呢!
建国前关于听戏我印象特深的有两件事,一是程砚秋先生重返舞台,程先生重新登台唱的什么记不清了,但“满城尽说程砚秋”的氛围至今想起,尚很鲜活。日本占领北平期间,程告别舞台,隐居京郊青龙桥务农,抗日胜利后重出,受到北京人热烈欢迎,称赞他“耪了八年地”。不只是赞许程砚秋的民族气节,还是对追星一族更有刺激力的新花样。就记得常来家串门的女眷们说“他耪了八年大地,手怎么还那么细嫩,真不容易”。另一件是梅兰芳先生抗战胜利后回北平在长安大戏院(西单)登台演出,我们家买了一个包厢。那时长安大戏院包厢很简陋,在二楼前二排围个圈,圈中有四把木头椅子。演的是梅派名剧《生死恨》,全剧已经没有印象了,只记得韩玉娘抱着其丈夫程鹏举靴子哭诉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