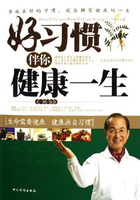女子也是有些许功夫底子的,或许也不低,她直觉想躲,却仍旧不可避免的让风刃伤到了她的肩膀。
压抑的痛呼自门外传来,月璃却并不关心,甚至连受伤的动作都没有丝毫的停顿,一如既往的分药,称量,碾碎,研磨。
女子双目含泪,似是伤心欲绝,却又好像早已习惯了这样被对待。她紧咬着下唇,最后深深看了一眼映在房门上的月璃的身影,然后狼狈的离开了。
月璃听着那女子越来越远的脚步声,最终消失不见之后,才几不可闻的冷哼了一声。
“愚不可及。”
这就是他对那女子的评价,在他的眼中,这世上若是有什么轻如尘埃、令他觉得嗤之以鼻的东西,那便是爱情。
一直到正午,月璃才打开了自己院子里的大门,一夜未睡的他多了几分颓唐,衣衫也显得有些凌乱。他直接走到了唐水烟的床边,丝毫不顾石榴惊讶的眼,双手一捞就把那个已经昏迷不醒的师妹抱到了怀里,然后一如来时一般沉默的回到了自己的院子,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月璃的房中放着一个巨大的木桶,里面满是黑乎乎的药汁,还散发着热气。他小心的将唐水烟的衣衫褪下,将她放到了木桶之中,又取出了一排银针,计算着时间一点一点的给唐水烟下针。
隐隐约约想是有血腥味混合着药味蒸腾而上,原本全黑的药汤表面上浮起了一层诡异的蓝。唐水烟身上的银针越来越多,月璃丝毫不敢松懈,专注于手上银针的轻捻。
“嗯……”许是不舒服了,唐水烟皱着眉嘤咛了一声。
月璃有那么一瞬间抬起头,看到她隐忍的小脸有些心疼,又飞快的低下了头,手上的动作丝毫不感停。
“乖,再忍忍,忍忍就好了……”
轻声的哄着,就像是小时候唐水烟受了师父的罚,又忍耐不了时候,月璃在一旁耐心的安慰时候一样。
就这样一直过了四个时辰,当月璃将最后一根银针放到了一旁的矮几上,这才将唐水烟从木桶里抱了起来,拿过毛巾仔细的为她擦净了身体,换上了一身干爽的衣服,让她躺在了自己的床上。
而月璃,也因为是在是太过疲惫,满室的狼藉都没有力气去收拾,只接坐在床边,靠着床柱睡着了。
石榴粘在院门口,是进也不是走也不是,急得团团转一点法子也没有。她可是担心死她家小姐了,可又不敢贸然进去,只能上火的抬头朝里张望,就盼望着能瞧见点什么。
自那一日起,唐水烟就再也没有醒来。月璃每日一次为她沐浴施针,倒出的药汤一次比一次蓝,那诡异的颜色看得石榴心惊肉跳,看不到自家小姐更是让她忐忑不安的日夜不能成眠。
前后思付了许久,还是把这事儿给宁之盛说了。
宁之盛当即就赶紧摆摆手,表示自己坚决不跟在里面掺合,“月公子是你家小姐的师兄,你不也说了么,是你家小姐请他来治病的。那就相信他,别乱想。”
“可是现在我连小姐一面就见不到,能不着急吗!”石榴跺脚,小姐醒来了若是没有她的服侍,那肯定是不习惯的,月公子再细心也是个男子,能比得过她去了吗?
再说了,这孤男寡女的,若是传出了府,可怎么办?小姐的名节还要不要了?
宁之盛觉得石榴这完全就是瞎操心,那月璃是什么人哪,只要他不想,这事儿就一定不会传出去。
到第十二天的时候,唐水烟终于睁开了眼睛,她眨了眨有些模糊的视野,看着陌生的房间,一时间有些发懵。
这哪里?
“师妹,你终于醒了。”
月璃特有的醇厚嗓音在头顶上响起,还带着些许的如释重负,唐水烟抬起头,看到的就是月璃依旧魅惑风流的模样。
“师兄,我可以……活下去了?”有些不敢置信,长久昏迷的嗓子沙哑无比,就像是朽木被拖拽在满是枯枝的地面上时发出的声音一般,就连她自己都吓了一跳。
月璃没说话,只是那只大掌揉乱了她满头的青丝,嘴角噙着的笑容,便是最好的回答。
唐水烟一瞬间喜极而泣,她没有死,她可以活下去了!
因为唐水烟刚醒,四肢根本是一丁点儿的力气都没有,每日都要针灸药浴来回于主院和别院之间又太过麻烦,干脆就在月璃这里住下了。
而世上总是没有不透风的墙,事情总是喜欢向着最具有戏剧性的方向发展。就如同最开始石榴所担心的那样,八王妃趁着八王爷在外出征的时候,耐不住空闺寂寞,竟然偷人的传闻,就像是雨后春笋一样,在京城里迅速扎根疯长。
“听说了吗,八王府的八王妃,耐不住寂寞,竟然偷人了!”有人津津有味的传播。
“哼,本公子早就说了,这种品行不端的人,肯定是这样。”有人嗤之以鼻的不屑。
“这种不守妇道的女人,就应该拉去浸猪笼,沉潭!”也有人义愤填膺的不满。
许多闺阁女子,当年因为八王爷大婚而芳心碎了一地,又因为传出八王爷龙阳之好的传闻,而倍感绝望,如今却全都抱成了一团,同仇敌忾。
“那个唐大小姐简直太不要脸了!”
“就是,八王爷那样的良人,竟然被这种女人背叛,阵势太可怜了。”
满城风雨就像是惊涛骇浪的大海,怎么也止不住。而在这样的京城里,关于八王妃一枝红杏出墙的传闻,还有着另一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