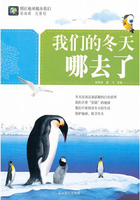爸爸的这个决定对于蒂姆和伊丽莎白来说意义重大。在伊丽莎白长大的菲律宾,把自己年迈的父母放在养老院里面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她一直在游说希望妈妈能够跟他们一起回到新泽西州生活。尽管他们的家在一栋没有电梯的高层楼房里,尽管他们只有一间小卧室。玛丽乔也一直表明自己的立场,告诉大家她如何能够在做社工的同时,照顾好妈妈。而我也考虑过把妈妈接到自己家来住。尽管我明白这让我和珍妮的婚姻生活危机四伏。
爸爸看起来不会接受我们这些善意的却不切实际的计划。对于照顾妈妈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他了解得最清楚。他说:“你们的妈妈属于路德斯。”“或许刚开始她不喜欢,甚至会发脾气,但是她会慢慢渡过难关。忘记不痛快的事情并重新开始生活。路德斯是最好的选择。”
蒂姆和我互相看看,都点点头。我们答应爸爸会去和路德斯的管理人员做个委托,等爸爸一出院,就把他们老两口一起送到那边的养老院。爸爸对这个承诺点点头。放下了心头的一件大事,他看上去神情舒缓了很多。就算是在重症监护室,爸爸的心里还在打点着他需要完成的事情,让一切都井然有序。他向来都是一个事无巨细的人。他还会提醒我们除草机和除雪机需要在冬天妥善保管。水管里面的水要倒干净,以免结冰。
谈话内容渐渐变少,到最后我们都安静地守在爸爸的床前。耳朵里是氧气泵有规律的声音。护士在门窗上探头示意我们,这次探护时间剩下最后的五分钟。
我说道:“爸爸,我想我们该走了。”
“明天我们再来探望您好吗?”蒂姆又说。
爸爸点点头,示意我们可以离开了。我们开始穿外套。就在这时,伊丽莎白用她不太熟练的英语说:“爸爸啊,喜欢我们做个祷告?”
爸爸的眼睛变得有神起来,他的头上下点了点。
于是我们都低下头,开始了祷告。“我们仁慈的主啊,在天堂里俯瞰众生……”问题接着就来了。我和蒂姆竟然忘记了那曾经被教过成千上万次的祷告词。很多年我们都不曾自己念过祷告了。每每在家庭聚会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跟随着爸爸的提示,附和着他的声音嘟囔着糊弄过关。可是今晚,爸爸的声音压在厚重的氧气罩下,完全听不清楚。伊丽莎白那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英语水平更是爱莫能助。我和蒂姆犹如汪洋中的一叶小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您的名字圣洁无瑕;那个什么,什么,这个啥啥啥;在啥啥啥,就如同这个啥啥啥,什么什么。”
我们继续结结巴巴地往下瞎编,祷告过程也变得冗长无比,就像我们在背诵古代史诗《贝奥武夫》一样。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无功,无法掩饰。我偷瞄了一眼爸爸,他眼睛紧闭,高声祷告着。接着我偷瞄了一眼蒂姆,这无疑是个非常不明智的举动。当我们四目相对的瞬间,他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这突破了我的忍耐极限,也忍不住小声咯咯咯笑起来。我使劲憋住从胸口冲出的一股气,想笑又不敢笑出声音来。肩膀已经不受我的控制,上下抖动起来。情况无比糟糕,糟糕无比。糟糕中又夹杂着让人无法忍受的滑稽。我的鼻子里不时地发出哧哧哧漏气的声音,眼睛里已经笑泪泛滥。我低头盯着自己的膝盖,努力去想那些不搞笑的事情。可是,越是这样强制自己不笑,笑的却更加厉害。
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参加祷告的情景。来自波兰神学院的斯坦罗老教父在耶稣受难日主持神圣而又严肃的祷告,他高声唱颂祷告词,我们在下面则咯咯乱笑。你明明知道那时那景不能笑场,可你却无法忍受,笑声泛滥。
床对面,我听到像是猪哼哼一样的哧笑声。抬头看看蒂姆,他也是双肩乱抖,双眼紧闭。可他继续忍耐着,口中还念念有词: “……请赐予我们啥啥,我们的这个那啥是啥啥的……”我也随即加入这呓语一般的祷告中。“……和嗯嗯我们一起来自哦啊啊,为了嗯嗯和啊啊。阿门。”我和蒂姆提高了嗓子,同时重读了最后一句词,阿门。这句话,我们可是烂熟于心。祷告终于结束。我和蒂姆擦擦眼泪,假装祷告进行得十分顺利。而爸爸只是用他那疲惫、认命的眼神看了看我们。
蒂姆和伊丽莎白已经走向走廊。我在门口停下来,转身看了看爸爸。他正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每一次吃力的吸气,他的下巴都要微微抬起;每一次吃力的呼气,他的头都要轻轻地沉入枕头中。医生嘱咐他每次吸气都要用力,只有这样氧气才能到达肺部,达到治愈的效果。呼吸才能活命。爸爸集中精力,使出全身的力气,抓住每一次呼吸的机会,抓住每一丝生命的痕迹。“做个好梦,爸爸。”我轻轻地说着,把两根手指放到嘴唇上,送给了他一个飞吻。
伴随着圣诞越来越近,我们探望父亲的时间也固定下来了。我早上过来,蒂姆和伊丽莎白中午到下午守着,晚上我跟迈克尔再回来接班。玛丽乔奔波在自己家和工作单位之间,只要一有时间就开一个小时的车赶来看望父亲。我们大多时候跟妈妈坐在一起,一边守护着爸爸,一边陪妈妈讲故事,给她按摩肩膀。
又是一个阴沉而凄凉的黄昏,我在客厅陪妈妈坐着;蒂姆和伊丽莎白去了医院;迈克尔出去办事了。伊丽莎白拉了一串串节日灯,放在长久没人碰过的钢琴上,然后缠到窗台的花盆上,她鼓起勇气,努力使家里至少有那么一点点节日的喜悦气氛。但是这些装饰却使房间看起来更加冷清,让我们更添一份惆怅,想起了往年的圣诞节,那时壁炉烧得噼啪响,到处是孩子欢叫的声音和圣诞树的芳香。坐在那儿,我忍不住回忆起当年父母还正年轻,他们想方设法、不遗余力地为我们营造圣诞的神秘气氛。爸爸布置的欢快餐厅,我们修剪的圣诞树,妈妈制作的圣诞布丁,还有我们比赛包装礼物并装饰圣诞树。
从小我就发现别人家都是从商店买来节日灯挂在圣诞树上,而我家不一样。爸爸总要花费几个小时亲手制作设计独特的节日灯,他的灯用一个电线串联起来的,可以确保它不会引发火花事故。这其实是说一支灯泡熄灭的话,所有的都会连带着灭掉。这使得我家有了另一个节日传统,那就是大家拧下每一支灯泡,挨个检查找出熄灭的罪魁祸首是哪一支。有时我们在圣诞前夕摆弄那些让人发疯的灯泡一直到很晚,然后不顾寒冷跑去圣母庇护所进行半夜的弥撒,在那里,耶稣诞生的盛大场景,一簇簇圣诞红,再加上我们打破宵禁的激动,着实让人觉得神秘。
屋子里从来没有这么安静过。
“只有我和您了,露丝。”我说。天色越来越黑了。
“只有我和我的第三个儿子了。”她说。
“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点东西吃吗?”
“好像有点,好啊。”她说,我扶着她坐到餐桌旁,我的手用力扶着她的胳膊,以免她摔倒,然后用微波炉热了一盘剩饭给她。
“您可真是饿了!”她吃完时我惊叹道,“您把一盘全吃光了。”我感觉到一种幸福,跟把饭放到我的孩子们面前看他们吃得精光时一样。她现在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像个孩子。我的母亲的生命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小时候的样子。她不再为自己的孩子们担忧了,不再为我们生活道路上的选择和精神健康发愁了,也不再强迫我们遵从她的意愿。所有以前看得特别重要、使她劳心伤神的事情都如同遇难船上的货物随大浪漂走了。现在我们不得不藏起糖果不让她看见;督促她多吃蔬菜、多喝水;提醒她刷牙;给她好处来哄她吃药。
我们回到客厅,我带她坐到她心爱的椅子上,我们一起坐在闪烁的节日灯光下,屋子里如此寂静,我甚至能听到暖气通风口上升的气流声。
“还有五天就过圣诞了,妈。”我说。
“你爸爸会回来过节吗?”她问。 “不知道,妈妈,”我说,“我觉得不能吧。”
我们坐了很久,听着暖气口的气流声。 “还没有下雪。”她终于开口了,看着窗外的暮色说。 “圣诞时也许会下。”我说。
这时候她开始唱歌了。柔美而婉转,她的声音有些颤,像是一只小鸟或者小女孩在唱歌。 “我在期待一个白色的圣诞节……”我惊叹于母亲的头脑。这首歌是从她哪块遥远的记忆中飘出来的?我几十年没有听她唱过白色圣诞节了。 “就像我以前度过的……”我现在有两种选择:干坐着听她那哀伤的寂寞的歌声还是加入她。于是我们一起唱起来: “树梢在闪耀,孩子们在倾听,那白雪中的雪橇铃……”我俩都只记得第一段歌词了,所以我们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地唱。直到实在唱够了,她停下来叹了口气。 “去世的歌星平·克劳斯贝要是还能唱该多好。”她说,然后她在椅子上睡着了,寂静又一次笼罩了我们。
第二天,星期二早上,我10点到了医院,发现爸爸支撑着坐起来了,一个较轻的塑料氧气罩松松地罩在脸上,看着呼吸得比较顺畅。那个笨重的压力氧气罩被放到了墙角。“我的血液含氧量还不错,”爸爸说,“所以他们给我戴这个轻的,让我休息下。”透过轻氧气罩,我可以清楚地听到他说话。
“那太好了,爸爸,”我说,“您在好转呢。” “我不确定,约翰,”他说,“我不清楚。”他用探寻似的目光看着我。“你觉得呢?你觉得我能撑过去吗?”
在这件相当重要的事情上,他还从来没有问过我的看法。我犹豫了。当时我的真实反应是升起的希望很快跌落下来。前一秒钟,我还幻想着爸爸完全康复,重新过上他们一生为之打拼的生活。后一秒钟,我又意识到他们独立生活的日子已经没有了。即使最好的情况,我的父母也得要保姆照顾、靠辅助器械活动。家里再看不见爸爸开车,看不见他们修剪草坪,看不见他们去杂货店买东西。然而我又想到最可能的结果是爸爸害怕的事情会发生,他再没有走出重症监护室。医生用尽手段给他治疗,但是肺炎和白血病却疾速冲向爸爸生命的终点,没有半点缓和的迹象,我找不到爸爸能战胜病魔的任何线索,而且希望一天天在萎缩。所以我试着面对现实,不想施舍给爸爸希望。
“我不知道,爸爸,”我说,“我们需要的是继续努力。我们需
要坚持与病魔作战。” “还有祷告。”他加了一句。 “还有祷告,爸爸,您不能放弃。”
他点头表示同意。“我只是想好起来以便照顾你妈妈,”他说, “我想在她有生之年的每一天照顾她。”他仍然全心全意地爱着妈妈。她是他的一切。而且看起来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能活得比她多一天。我把他的氧气罩摘下来,取出玻璃杯中的吸管放到他嘴上,让他可以吸一点水喝。
“一天一天慢慢来,爸爸。”我说。 “知道吗?我在担心圣诞节。” “你是说还没有出去给我们买礼物吧?”我不露表情地说。 “我不想破坏大家的圣诞节。” “哎呀,爸爸,您不会。” “你应该在家陪珍妮和孩子们的,”他说,“我们都清楚这一点。”
“我到时随机应变,”我说,“也可能圣诞前夕飞回家,到时候看吧。”其实我已经告诉珍妮可能会错过节日了,她说让我不要担心她和孩子们。“你现在应该在那里的。”她说。
然后我改变了话题,“迈克尔和我昨天去路德斯养老院跟管理人谈过了,”我说,“她很好,告诉我们他们非常崇敬您,对您这些年来对那里的帮助表示感谢。”
爸爸睁大眼睛期待地问:“然后呢?”
“他们有很多的申请人,但是她说他们无论如何会给您和妈妈找个房子,”我说,“我们还去看了一下小教堂附近的那套给夫妻用的房子。里面有两个卧室、一个客厅,对您和妈妈非常合适。文件都已经填好啦。”
“那太好啦,”爸爸说,“谢谢你为我们做这些。”
我没有告诉他那个套房很快就能入住,更没有告诉他原因:现在的住客,一位年迈的神父,已经生命垂危了。在这方面,养老院跟重症监护室很相像,都是生命的最后驿站。
我们坐着沉默了好一会儿。
“你看,”他开始说,从他舔嘴唇的动作我知道他是要谈思索很久的事情了,“现在跟你说这件事正合适。”他伸出手来让我握住。我将手指放到他的手指缝里,坐在他旁边听着。
“好啊。”我说。
“对于孩子们的宗教信仰,你打算怎么办?”
我感觉心脏猛然一沉。他重新拾起我们一直避讳的话题了。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会有什么结果的。“爸爸,”我声音变得跟小,只把叫他的名字悬在空气中,“我在尽力了。我知道这不是您以前对待我们的方式,也不是您希望的做法,但是我在努力地把他们教育好。”
“你教育得很好,约翰,”他说着使劲攥了下我的手,“你是位好父亲。我只是怕他们就那样长大,没有宗教信仰、也不祷告。尤其是祷告,非常重要啊!”
我本想给他吃个定心丸,告诉他他所希望听到的:他的孙子们将会接受圣礼并参加每周的弥撒,会被教育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我知道那么说我是违心的,对他也不诚实。我应该真诚对待他,因为我是那么尊敬他而不愿意欺骗他。再者说,他是个聪明人,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渐渐意识到我的糖衣包裹着的谎言一刻也不曾骗过他。可能骗得过妈妈,爸爸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