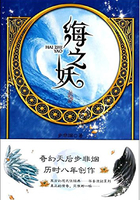一天晚上,他来到我们家,我们俩都惊奇地看到一个穿着短裤、T恤和拖鞋的小伙子。他头发浓密、胡子拉碴,他看上去更像是来教我们冲浪而不是宗教教育。大卫神父看到我们已经同居了似乎一点也不感到困扰。即使他心里正在评判我们,那他也没有表现出来。珍妮立即就喜欢他了,到深夜时,我们已经像老朋友一样把酒言欢了。
天主教正统要求双方父母庄严宣誓:以天主教的信仰来养育孩子,即使一方不是天主教徒,也要这么做,并许诺他们会经常地参加弥撒,接受圣礼。对珍妮而言,这简直像强迫一个法国人向大不列颠宣誓效忠。为什么?她问,难道要她用一种她自己既没有实践过也不相信的宗教理念去抚养自己的孩子吗?善解人意的大卫神父似乎明白他不能逼得我们太紧,那样恐怕会激怒我们。他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只要她同意到时候考虑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天主教徒。她说当然她会同意考虑这个方案,又说:“约翰是一个天主教徒,如果他想以他的信仰来培养孩子,那他自己必须是那个实施的人。”她答应不会阻挠我那样去做,于是大卫神父似乎满意了,我们签了保证书。
“多好的一个人啊!”在他走后,珍妮说,“他真的不错,非常通情达理。他不像你爸妈在的社区里那些假仁假义、大腹便便的神父。”如果真有圣主,大卫神父就是主赐给我们的礼物,他就是那个能帮我在我未婚妻和父母的感受间游刃有余地过关的再合适不过的神父。
但是在我们下周见面前,郁闷的大卫神父打电话告诉了我们一个坏消息。他的上司突然派给他一个与社区居民隔离的工作。 “他们可能认为我有点太标新立异了。”他说。
“你不能和我们做完吗?”我问。
“不能,”他说,“我也想但是我不能,非常抱歉。”
教区给我们安排了另一个神父,他是个圆胖的小个子,油光光的皮肤,两只眼睛距离很小,使他看上去目光猥琐。不像大卫神父,他给我们发布的是绝对的法令。告诉我们应该怎么结婚,应该怎么过婚后的生活。他看上去很陶醉于跟我们这些小两口讲做爱的事情。他在最后一堂课上简直完全专注于讲享受性爱这部分了。他越讲越来劲,越讲越兴奋。
小圆眼神父想让我们明白只要结了婚,我们就能忘掉以前被教导的那些性的罪与恶了。“再不要那么想了,”他说,“从婚礼那天晚上开始,以前的说法都不适用了。”已婚夫妇之间的性行为是遵循自然规律的,是美好的,甚至是神圣的。人可以追求性爱,不要犹豫不要有罪恶感,甚至可以由衷地喜爱它。“享受它吧!拥抱它吧!为它庆祝吧!”他说这话时声音越来越大,语调越来越高。他用眼睛扫射每一对恋人,好像看到了我们新婚夜在房间里赤身裸体、大汗淋漓地享受性爱。
我俯身凑到珍妮耳旁小声说:“我觉得他有点过分享受这个话题了。” “太过分了,”她小声回我,“我都想溜走了。”
这个下午最大的讽刺不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而是这个站在满屋子情侣前面提供性爱建议的单身男人,极有可能他从来没拉过任何一个异性的手。这就好像雇一个瞎子来教射击。
但是他实践经验的缺乏丝毫没有放慢他的进度。当他为各式各样的性爱前戏送祷告时,他甚至更加有活力了。“让事情保持有趣一点没错的。”他劝道,“随意给性爱加点刺激吧!”神父提醒我们,自由自在的天主教式做爱的唯一约束是阴茎一定、一定、一
定要在阴道里射精。“不许阻挠精子与卵子的结合,不许破坏圣主的计划。”
这引发了神父对允许我们使用的唯一一种避孕方法的详细描述。神父解释,这种方法的美妙之处在于夫妻之间只需要在每个月容易怀孕的时期停止做爱。在圣主的眼里这种安全期避孕法不是犯罪。因为它只是适当避免做爱,而不是因为害怕怀孕才这样做。神父还强调这招很管用。但是我知道真实情况,因为我亲眼目睹了我们圣母庇护所周围那些拥有十个、十二个,甚至十四个孩子的家庭。我妈妈就有八个亲兄弟姐妹,而且她对这种安全期避孕法极其信赖。但是我们都认同的一件事是:除非你不做爱,这个方法才百分之百起效。
我能感觉到珍妮已经忍受到了极点,每时每刻她都有可能站起来告诉小圆眼神父她对他本人和他所给的性爱建议的真实看法。她甚至还会说出神父眼神淫荡的事情。“我们就快熬过去了,”我轻声安慰她,仿佛她在忍受牙根管填充手术的折磨,“再忍耐一会。马上完了。”我把手伸过去让她握住。
神父留给我们一个最后的思考:“当你和你的配偶在性结合的时候,记住你们不是在和彼此做爱,你是正和主耶稣基督做爱。”我们都低下了头,在神父的指导下,祈祷在我们新婚夜结合的时候耶稣的同在和祝福。
小圆眼神父把官方文件交给了我们,证明我们已经成功完成了宗教婚姻培训,我们接着就开门冲了出去,沐浴在阳光下。当我们走到车前时,我把珍妮摁到车门上,然后吻她。“和主做爱!”我惊呼,“三人行!这会儿我真希望自己没听到。”
珍妮放声大笑,我能感觉到她在我怀里轻松多了。我知道这段时间让她来说很难熬,我一定会好好补偿她的。
我们把婚礼定在劳动节的周末,但是之前正赶上石头的婚礼。在所有邻家老朋友中,石头是跟我关系最铁的一个。虽然大学和工作使我们相隔甚远,我们仍然是最好的朋友:一起旅行、一起野营、一起约会女孩。我跟汤米、布袋还有其他大部分朋友失去联络了,但是跟石头还在联系。现在他就要在芝加哥结婚了,仅仅比我的婚礼早了三个月,我不想错过。订完飞机票我才发现邀请单上有我父母的名字,很多年,他都经常来我家,对于他们来说石头几乎就是他们的第四个儿子。我们小区的其他长辈也将参加婚礼,我们都被安排在一家旅馆。这将是我跟珍妮同居以来第一次见我父母,我害怕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儿子和未来儿媳婚前就住在一间旅馆会感觉痛苦——不只是道德上,还有公众层面上。他们无疑把我们同居的事情当做秘密,现在显然来参加婚礼的邻居和朋友都会知道。这如同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
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告诉自己:“你没有什么可隐藏的。你没有什么可感到羞耻的。是他们有问题,不是你们。”为了准备我们的婚姻生活,也因为感觉我们得到的天主教培训不够全面,我和珍妮跟咨询师签约进行婚前咨询。这种咨询是为了帮助夫妻提前理解并准备解决婚后将会遇到的各种挑战,并学习处理关系的技巧,例如:如何解决冲突,并且不给双方留下心理的创伤。咨询刚开始,我就开始长篇谈论因为我们同居跟父母之间的关系紧张问题。我满心期望这位和蔼可亲的咨询师,约翰·亚当斯,能够跟我站在一边,责备珍妮不体谅我的处境。我想让他告诉珍妮她应该对我父母的敏感更加包容一些。
但是亚当斯医生似乎不赞同我的想法。“容我再问一次,你多大年纪了?”他问我。我回答后他又问道: “你还住在父母家吗?”
“没有。”
“你现在还靠他们养活你吗?”
“不。”
“你欠他们钱吗?”
“不。”
“大学贷款呢?”
“没有。”
“他们负责你的汽车保险费?你的日常费用?”
直到此时我才明白他的意思。他向空中一挥手,“那为什么要让他们主宰你的生活?他们会对你做什么呢?”
“这样的,你看,只是……”
“你不想让他们失望,”他接了我的话,“这个我理解。但是我们会有办法在尊重他们的道德观同时不让他们控制你的生活。”
亚当斯医生把我们大量的婚前咨询时间用于帮助我找到摆脱父母控制的方法。我早就到了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不用担心父母如何评判的年龄了。医生告诉我做想做的不必向他们道歉,接不接受我的做法是他们的事情。带着医生的建议,我到了芝加哥,决心跟我的住在了一起的女朋友好好度过这个周末,就像父母不在那里一样。我愿意承担任何后果。
但是当我在旅馆大厅碰见父母时,气氛非常轻松愉快。他们邀请我们吃午饭,并且谈话很随意舒服。没有说一句重话。我们互相交换了礼物,珍妮简要向妈妈介绍了我们的婚礼安排。妈妈用她说过无数次的笑话款待我们,她讲在她和爸爸的婚礼上,爸爸是多么紧张,乔神父则差一点睡过头错过婚礼。爸爸坐在旁边一直笑,不住地点头,跟他平时观看妈妈训我们时一样。
那个晚上,我们在婚礼弥撒上和父母坐在一起,当我应石头的请求站在圣坛旁读那段圣经时,妈妈和爸爸都向我投来微笑。他们看上去很为我开心。但是到了第二天清晨,就在我们准备退房回去时,我才明白他们无比快乐的表面下埋藏着熊熊烈火。我留珍妮在我们房间,然后越过两道门去拜访我的父母。我刚进门他们就把火释放了,终于有一点时间跟儿子独处,这是他们直话直说的好机会。
“约翰,我们有重要的事情想跟你谈谈。”爸爸先开口。立刻,妈妈接着说:“我们觉得你的婚礼不应该举行弥撒。”刚开始我不懂他们是什么意思,还以为他们觉得如果我和珍
妮真的不喜欢就省去那么长的仪式呢。我想他们知道我们为他们着想比为我们自己还多了。“不用,真的,我们不在乎,”我说, “我们都感觉有弥撒很好。”
“你不明白,”爸爸说,“我们不赞成那样做。” “不赞成?” “鉴于你们现在的生活方式,那样做不妥。” “我们的生活怎么了?” “生活在罪恶中,”妈妈说,“约翰,你们现在生活在罪恶的状态中。而且你们还在炫耀这些。看看你们,在旅馆里住在一起让
别人都看见了。” “你那样做是蔑视弥撒。”爸爸继续说。 “哦。”我应一声。 “珍妮不是天主教徒。就我们所观察,你也不再履行天主教教
义了,”爸爸又说,“那样做太虚伪了,弥撒不应该华而不实。”
他们的话慢慢沉淀在我脑子里,我感觉眩晕。我不再是他们的骄傲,也不再适合参加对于他们来说异常重要的、改变人生命运的圣体圣事。
“好吧,”我说,“我们不必举行弥撒。”
“我们感觉你失去你所有的信仰了。”爸爸说。就在两周前他们去了波黑的默主哥耶小镇朝圣,在那里,教徒们声称圣母玛利亚先后出现在六个农民面前。他们扣人心弦、毫不怀疑地讲述那些据说的奇迹使我感到无趣。爸爸说从我迟钝的反应可以看出我不再热衷他们的信仰了。
“爸爸,”我说,“信仰是天赋,你不能把它强加给谁,那样只会徒劳。” “告诉我们实话,”妈妈插进来,“你现在还去礼拜吗?”我看着她待了好一会。仔细看着她,看着我那么多年来对着撒过那么多次谎的她。“没有,”我说,“很长时间不去了。”
妈妈的反应像是有东西砸在胸口上,把她身上的元气撞了出去。她把一只手搭在椅子靠背上盯着窗外,似乎在研究远处州际公路那里的什么东西。“啊,我之前都不知道这个。”她说。
“不是因为珍妮,”我赶紧说,“不要以为是珍妮的原因。我早在认识她之前就不去教堂了,很早之前。”我们三个站成一圈,什么都不说。“瞧,我得走了,”我说。我正要开门,爸爸叫住我。 “约翰!”
我愣住了,然后转过身。他冲过来抱住我,脸埋在我的肩膀上,紧紧抓住我好像永远不会放我走。他的胸膛贴在我身上,我感到他在颤抖,然后我感到肩部被暖暖地浸湿了并听到他在抽泣,断断续续地抽泣着。这个我从来没见他流过一滴泪的男人,我家的顶梁柱,正在我的怀抱里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