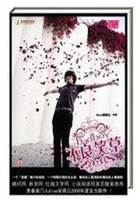她笑着说:“要继续努力啊,不要觉得你们没有改变什么。”也许艾金森女士还另有所指。当我在秋天再回到学校时,我已是一名毕业班的学生了,《内心洞察》成了遥远的回忆。但发行《直肠》的编辑们却有了明显的变化,他们变得更加自信了。我们的指导老师更喜欢挑战我们了,故事也越发精彩了。我们开始更频繁地、更积极地写作。即使这样,卡温先生也不管了。他听从指导老师的建议,不再把他的意愿强加在我们的作品中。成员们不用再顾虑校方领导的监视,可以尽情地发表关于避孕、老师合同纠纷以及其他热门话题的相关文章了。我也许是在吹嘘自己,但卡温先生和校董事会好像不想激起学生记者太多的热情。为什么要去惹那只沉睡着的狮子呢?
在那个秋季,还有一件事发生了变化,是关于三位一体洛酸娜的故事。第一天上学时,那形影不离的三姐妹变成了两个人,只剩下洛丽和苏。就在那个暑假,安娜家人不顾安娜的反对,搬到了新泽西。洛丽和苏在校园里一前一后地走着,中间空出了安娜原来站的位置。感觉她们中少了一个就变得不那么完整了。我和她们相处得很好,看见安娜走了,我也很难过。安娜的文雅聪慧、热情独立令我钦佩,她那飘逸的长发和灿烂的微笑令我着迷。
深秋过后的一天,洛丽在走廊里遇到我。她抓着我的胳膊,笑着说:“猜猜有什么好消息?安娜要回来看我们啦!她要回来待三天过感恩节哪!”安娜在新城市和新学校里过得很可怜,以至于她爸爸妈妈突然买了飞机票让她回密歇根,她会在洛丽家过周
末,苏也要过去住。简单来说,亲密三姐妹,将要重聚了。
“这太棒啦!”洛丽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还有更好的。我爸妈最后一天晚上会外出,家里就是我们的天地了。你必须也过来。”她给了我一个最新的完美笑容,她的牙套已经在暑假的时候拿下来了。
“我必须,哈?”我有些害羞地说。
“你必须。”她灿烂地笑着
“那好吧,我会去的。”我说。
于是我去了,不像皮特·格雷鲍斯基的大派对那么张扬,洛丽的小聚会办得小而谨慎——四个人的派对。我之前发现了一个不用出示年龄证明就能买到酒的商店,所以我在那里买了两捆六罐装的啤酒。洛丽做了煎蛋卷。我们四个坐在一起,边聊天边听阿洛·格思里的唱片。苏第一个熬不住了,午夜后不久拖着脚上楼,趴到床上马上睡着了。洛丽是第二个,慢慢地不说话了,最后在沙发上沉睡过去。我和安娜肩并肩坐在沙发旁边的地板上,一边聊着,一边看唱片封皮。她对我微笑,“看来我俩是坚持到最后的人了。”她说。
之后,她的手移动到我的膝盖处,我的手插进她那固执的头发,从她脸上轻抚到后面,她闭上眼睛,我用了一点时间观赏她的面容,发现她好美——比我以前容许自己注意到的更美。我吻了她的脸颊,然后鼻子。我们找到了嘴唇开始亲吻,开始时很温柔然后就无所顾忌起来。几乎就在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与春天那个晚上在翻倒的独木舟上的吻完全不同的感觉。当她的嘴唇向我靠过来,我惊奇地愣了一下:这才是吻的感觉。我心脏狂跳,呼吸急促。我只有安娜。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忘记了过于明亮的灯光,忘记了我还在宵禁中,忘记了近在咫尺的正在打鼾的洛丽。
“你在发抖。”安娜小声说。
“我知道。”我说着,抱起她平放在地上,而我就压在她的身上。她一只手滑进我的T恤衫。我一边亲吻她,一边笨拙地解开她衬衫的扣子,然后拉开她的牛仔裤。
我们完全沉浸在二人世界中。听到哈欠声时我们已经处于危险的姿态了。安娜的衬衣打开着;裤子拉链也拉开了,可以看见内裤。而我上衣卷在肩部。我们身后,洛丽又是打了一个哈欠,这次声音更大,而且带有戏剧效果,竟然让我想起了《绿野仙踪》中那只怯懦的狮子。我们俩像是正在演音乐剧时,音乐突然停了一样怔住了。安娜睁大眼睛,我知道她跟我想的一样:洛丽什么时候醒的?用了多久想办法逃避眼前我们的行为?我想象到她在沙发上挣扎了一个小时作抉择。
该安静地逃离不让我们发现?还是假装睡觉直到我们俩去卧室里?或者发出无聊的哈欠声,好似她对这样的事情习以为常?我听见沙发吱吱作响,洛丽从我们身边迈过去上了楼,路上把灯给关掉了。
“哦,天啊。”我小声说。
“哦,没事的。”安娜回应我,并戏耍似的啄我的下嘴唇。
我们接着上演我们的好戏,两个人身体越来越火热,全身要蒸发。用十几岁男孩的地道语言形容,我已经上了三垒,进行最后的本垒冲刺。这时安娜在我几乎没有察觉到时撤退了,亲了一下我的鼻梁。
“约翰,”她对我耳语,“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我们都还是处男处女,都在体验我们的第一次。即使我在摸她的乳房、拉她的内裤时,也有些担心。也许因为这就是修女和修士们所说的大罪,他们说我们的身体是耶稣的庙宇。也许也因为妈妈和爸爸经常宣扬“婚姻关系”的神圣。再或者担心真的会不幸怀孕、毁掉梦想和人生。虽然不愿意承认,但是我真的也没有准备好。
“只是……”安娜说,“我们进展得太快了,我们能放慢一些吗?”
“我尊重你的想法。”我伪造了一个最俗的回答,好像我经常和女生上床,这次要做个超脱的选择。其实当时只想到那么一句。
我们半裸着躺在地板上,亲吻对方,抚摸对方,咯咯笑着。直到我有意识地看了一眼手表,已经凌晨3点了,让我吃了一惊。 “我得走了。”我说。“我几个小时前就该回家了的。”我没有提这个,不过现在已经是星期日早晨,几个小时后妈妈就会叫我起来准备参加弥撒。我们一起穿好衣服,安娜把我送到门口。
“早上回来跟我吃个晚点的早餐吧?”她问。
“听起来不错。”我说。
回家的路上,我构思好了对策:不惊动爸爸妈妈溜到楼上被窝里。关键是要确保肖恩不狂叫。它是只聪明的小狗,通常可以认出我的脚步声。
我把爸爸的大蒙特卡洛拉进车库,在开门进洗衣间时吹了一声温柔的口哨,从肖恩很小时我就对它吹口哨。然后我小心翼翼地拧开门走进去。肖恩在那儿迎接我呢,伸了下身子,又甩了甩,尾巴摇来摇去。我弯下膝盖挠着它的耳朵。“嗨,兄弟,”我小声说着,“想我了吧?”然后我脱掉鞋,踮着脚摸着走进厨房。正当我安静地走过客厅,伸手寻找楼梯时,黑暗中小拿破仑的声音响了。
“你去哪里了?”
“哦——嗨,妈妈。”
“别跟我嗨。不知道现在几点了吗?知道我等你多久吗?知道我
多么担心你吗?”黑暗中,我能听到她手中玫瑰念珠叮当响的声音。
我迅速编了个情节:我跟朋友看电影,我们四个人都打瞌睡了,然后醒来一看表,妈呀,知道都什么时候了吗!哦,天啊,夜都这么深了。黑糊糊的,妈妈穿着睡衣拖鞋向我走过来,怀疑地看着我。我能感觉到她在闻我的气息,检查是否有酒或者其他不合法的气味。在这方面我是安全的。喝最后一瓶啤酒已经是几个小时前的事情了。“真的,妈,只是我们四个晚上一起玩了。”
“我还以为你跟死了一样躺在路上了,”她责备道,好像她看到了我又一个肮脏画面,“她父母都在家吗?”
“谢尔登先生和太太?他们夫妇?哦,当然,要不然他们去哪里?谢尔登太太给我们做了非常棒的爆米花。让我们看电影时吃,很好的奶油味,香极了。”
妈妈瞪着我,想找出哪句是真。还好这次我脸上没有被咬的痕迹。“我真搞不懂这些父母怎么想的,让男孩和女孩一起待到半夜,”她说,“这太危险了。”
“他们夫妇一直待在我们身边,妈妈,”我说,“谢尔登先生真是个猫头鹰,喜欢看内战片,一晚上都在那读关于内战的文章。”
“我快担心死了,”妈妈继续斥责,“电话打不了,连他们姓什么也不知道。”
“我是应该提前打个电话给您,妈。”我说,“但是,您知道,我们都不小心睡着了。”然后我感觉她说话的语气又柔和起来,她应该又开始相信我了,至少是假装相信我了。
“上去睡觉吧,”她说,“在我改变主意之前。你还没有长大到翅膀硬得可以不听话,知道吗?”我赶紧在她脸上亲了一下上楼去了,我脑子沉浸在今晚发生的事情里:安娜,安娜,我的安娜。我一遍遍重复她的名字,像
诵祷词一样,直到幸福地进入梦乡。
第二天——或者说,那天早上过了几个小时后——我挣扎着跟爸爸妈妈去望弥撒,然后回头去洛丽家。我想象着我们四个人还像好朋友一样唧唧喳喳地围坐在餐桌旁吃早餐。然而当我到那里时,安娜自己来开的门,洛丽和苏不见了,显然她们故意躲出去给我们单独的空间。安娜朝我微笑,迷人的笑。我明白有些东西变了,重要的东西。就在前几个小时里,所有事情变得都不一样了。我们不再是四人组的朋友。不用问,我和安娜成了独立的一对。我忍耐着悄悄爬上心头的恐惧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