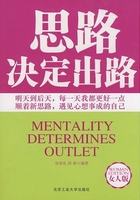是我那个还未出生就死掉的姐姐的名字。爸爸从此开始了学习航海的历程,就像他对待生活中出现的其他任何挑战一样,埋头苦学,一丝不苟。他找来专业书籍、手册、杂志阅读,不但如此,还去参加一些讲习班。爸爸简直就是把一项休闲的业余活动变成了工作量巨大的差事。玛丽乔和迈克尔一直都不喜欢帆船,不过蒂姆和我倒是有挺大的热情,而且我们用的是一种爸爸永远都没法做到的方法——全凭直觉。我们从来不看书也不研究,只是简单地去感受风向,然后随风而行。很快,蒂姆和我就自己驾驶帆船出海了,我们经常带上我的“忠诚四人组”的伙伴汤米或者石头或者布袋。蒂姆当船长,我们是船员。我们把船头的三角帆弄整齐,调整好帆的角度好让船保持平衡。那个时候我上九年级,我的航行技术已经相当可以了,当船长没什么了不起的,了不起的是我可以独自驾驶一艘帆船。当我得知大家都准备前往道奇公园后,在假期的第一天我就独自一人驾驶帆船出行了。
我并没有想要违背爸爸的意思,这一点我很确定。可是当我航行了几分钟后,我就开始朝着道奇公园海滩的方向行进了,并且开始给自己的行动找理由。他没说过任何不要靠近道奇公园的话呀,我在心里自我辩解道。靠近点看一下能有什么坏处呢?心里这么想着,帆船驶过了标示游泳区域的浮标,这时我想,或许我可以把船靠岸一小会儿,舒展下筋骨。反正这也不能算是进了公园,只是在边缘嘛。我看准了海滩边一块泥泞的平地,然后把帆船驶往那个方向。当我的船触碰到海滩的一刻,我意识到:在海滩上稍微走一下然后马上回到船上,爸爸肯定不会知道的,他怎么可能会知道呢?我放下帆,然后径直朝那个嬉皮士人海走去。时间还不到中午,但空气中弥漫的大麻气味已经浓重得足够让人感到兴奋。
这片广阔的沙滩是在从道奇公园分离出来的人工岛上,和公园的其他部分之间隔着一条没有活水的运河。游客们一般都把车停在公园那边,然后通过一座桥走到海滩上来。我的帆船停靠在靠近公园的运河岸边。一踏上通往海滩的桥我就感觉到我正在靠近一个巨大且喧闹的毒品市场。
毒贩们沿着栏杆排列开来,几乎是肩挨着肩,声调低缓地向人们叫卖着手里的毒品,例如大麻、安眠酮、酶斯卡灵。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所有的交易都一目了然。大麻我并不害怕,对于毒品倒是还有些恐惧。即便我带了钱,我也没打算买任何东西。但是这一路走来挺叫人毛骨悚然的,到达海滩后我折回来,再次从那些正在交易的人们身边经过。我一边慢悠悠地走着,一边看着眼前嘈杂的一切。
当我过桥的时候,竟然碰见了赖斯修士学校的一个同班同学。 “嘿,咱们搞点钱去。”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很容易的,”他说, “你就走到别人面前然后告诉他们你饿了,问他们是不是有多余的零钱。”为了给我示范一下,他走到一群年纪稍微大一点的青年人那里,和他们攀谈起来,过了一会儿手里拿着一个25美分的硬币走了回来。他如法炮制,又从另外一群人那儿要了一个25美分的硬币。
“好,现在轮到你了。”他说。
我扫了一眼周围的人群,把目标锁定在一个看起来稍微年长我几岁的女孩子身上。她盘着腿和几个朋友一起围坐在一条毯子上,看起来应该不是个难对付的人。“嘿,你有多余的零钱吗?”我问道。
“什么?”她回问我。
“有没有多余的零钱。我饿了。你有没有多余的零钱?”
“多余的什么?”
“多余的零钱,”我提高了嗓门,“有没有多余的零钱?”
“不好意思,没听清楚,再说一遍?”
“多——余——的——零——钱!“我几乎用喊的了。这女孩好像听力有点问题。
“我听不见。”她招呼我再靠近一点说,并且把手放在耳边。
“零——钱!”
我们这么来来回回地几遍,简直要手脚并用了。我发现她所有的朋友都在大笑。有的笑弯了腰,互看一眼,更夸张地笑起来。有的哼哼地轻笑两声,一些轻蔑的样子。我马上发觉,他们是在笑我。那女孩根本没有听力问题。
“算了算了。”我嘀咕着转身离开。
“大声讲出来嘛,小家伙,”她在我身后叫我,模仿老太太的语气,“再来一次?”
“哎,真不走运。”我的那位同班同学一边说,一边留下我自顾自朝反方向走去。
我没见到汤米或是其他庇护帮的人,我想再去那个毒品交易的桥上走一次,就是觉得好玩。我在桥中央的位置停下来,眼前的这一切让人有虚幻的感觉——空气里弥漫的味道还有那些烟雾中透出的或浓重或稀释或如彩虹般多彩的画面。我发现一辆卡车轰隆隆地朝着桥的一头开过来,车斗被帆布严严实实地蒙着。不一会儿,又一辆同样的卡车在桥的另一端停下来。我觉得奇怪,怎么两辆垃圾车同一个时间来了呢?突然,车都上的帆布被掀开,从车上跳下来一大群戴着头盔背着武器的防暴警察,手里挥舞着木制警棍。他们封锁了桥的两端。刹那间,无数的袋子、瓶子在空中乱飞,都被扔进了运河里。那场面让人想起《圣经》故
事,只不过这落下的不是以色列人得到的甘露,而是大麻和酶斯卡灵。
警察们大声地呵斥,命令大家按照他们的指示行动。还有警察在拍照。很显然,他们已经盯上这里的交易很久了,很清楚他们要抓的都是些什么人。我拼命从混乱的人群中往外挤,想赶紧离开这座桥。
“现在谁也不能上桥或者下去。”一个警察用他手里的警棍朝我胸前狠狠地来了一下。我赶紧掉头,可是在桥的另一端碰上了同样的情况,警察已经筑成了一道人墙。“我只是想来买点小吃,”我向警察解释道,我害怕极了,声音都在发抖,“我过桥的时候被人流挡在中央了。”那个警察戴着一副眼镜,留着个板寸头,看起来年纪并不大。他看了我一眼,凶巴巴地对我说:“赶紧走,别在这待着。”一边说一边把我推了出去。
下是下了桥了,但是我却在小岛这边,可我的船却在桥的另外一边呀,中间隔着一条充满了污水的运河。好在我没有被逮捕的危险,打算在那儿等着看好戏上演了。一大群孩子从海滩向那座桥聚拢,人流越来越多、越来越急。不一会儿就听见有人开始骂骂咧咧起来。
“去你妈的!你们这些猪!”我听见有人开始骂脏话。人群里有人学猪叫,伴着好些轻蔑的咒骂声。警察们用警棍把人群往后推。
“退后!退后!”警察大声嚷着。
“滚!去你妈的!”
“哼哼哼!噜噜噜!”
突然,一个瓶子从我身后朝警察的方向飞过去,不偏不倚正好砸在那群警察里。接着是第二个瓶子,然后就是一连串的瓶子,像炮弹一样砸向警察。接下来的场面更壮观了,但凡能被扔的东西都开始在天上飞起来,易拉罐、酒杯、装防晒油的软管、吃了一半的热狗。一部分警察退到桥上,把毒贩们也拉到桥上并用手铐铐住他们。一部分警察背过脸去,等他们再转过来的时候,已经戴上了防毒面具。也就几秒钟的工夫,第一个烟雾弹就在我们这边的人群里炸开了浓烟。有个男孩用衬衫捂住脸,急忙向前跑,捡起烟雾弹扔回去。可是,烟雾弹一个接一个地扔过来。
双方僵持的局面持续了接近两个小时。警察逮捕了计划逮捕的人后,缓慢撤离了。聚集的人群也渐渐散去。我知道我在岛上待的时间太长了,得赶紧回去,回到湖的那边去。过桥,回到公园那边,幸好我的船没被弄坏,我支起帆赶紧往回开。
《奥克兰新闻报》是一家本地的报纸。它的前身是《庞蒂亚克新闻报》,爸爸小时候还给这家报纸送过报。那时的庞蒂亚克还算是个不错的城市,不像如今只剩下些濒临倒闭的工厂,现在可再没有一个公司想和城市的名字扯上任何关系了。《奥克兰新闻报》是份晚报,每天下午4点派送到各家各户。
我到家后也就一个小时光景,电话响了,是石头打来的,他在电话那头喘着粗气。
“老天!你知不知道报纸上都有什么?”
“都有什么啊?”
“你上头版啦!你的照片,他妈的上头版了!你就站在那些乱扔瓶子的小屁孩旁边。”
“等等!”我立马跑到门廊捡起报纸,打开一看,一张照片占去了头版一半的篇幅。照片里面一张愤怒和嘲讽的脸,是个青少年,抡起胳膊正要扔出一个啤酒瓶。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站着一群流里流气的小孩。离他们不远处,一个矮胖的、戴着黑边眼镜、穿着松垮的大裤衩的男孩孤零零地站着。“他妈的,”我大叫,
“是我!”照片里的我眼睛盯着扔酒瓶的男孩,嘴巴张得老大,看起来就像是嗑了药,刚刚被突击搜捕。 “真他妈的倒霉!”我忍不住又骂了一句。得赶紧想个法子躲过这劫。
我挂了电话,确认妈妈没在身边,然后拿起报纸头版藏在T恤衫下跑上了楼。我把报纸藏在床垫的下面。我急匆匆地又跑下楼,把剩下的报纸散乱地铺在桌子上,让它们看上去尽量自然一些。随后我把蒂姆和迈克尔叫到我们楼上的房间里。
“最好是有什么好事啊。”蒂姆显得很不耐烦的样子。我把床垫
下的报纸抽出来递给他看。 “天啊!”蒂姆惊呼一声。 “你死定了!”迈克尔说。 “我该怎么办?”我简直慌了神。 “肯定不能让爸爸看到。”蒂姆说。 “不管怎么样也要藏好它。”迈克尔说。 “你们得替我保密啊,”我几乎是恳求的语气,“爸爸每天回来
就读报纸的。”他俩都答应一定替我保守秘密。
毫无疑问,像往常一样,爸爸吃过晚饭后就坐在客厅里他最喜欢的那张椅子上开始看报纸。我在楼上坐着,静静地数着时间。一千零一秒,一千零二秒,一千零……
“谁拿了报纸的头版?”从客厅传来他低沉的声音。没人回答。 “有谁见过今天报纸的头版吗?”还是一片沉寂。“蒂姆?迈克
尔?”他朝楼上喊了一嗓子。 “没见过,爸爸。”他俩异口同声。 “约翰?你在楼上吗?是你拿了报纸的头版吗?”
“不是我,爸爸。”我答道。
“妈的。谁总是在我看报纸之前就把报纸拿走?”报纸这事让他特别生气。要是哪次妈妈打扫房子,早了一点把报纸给清走,肯定被爸爸说一顿。
“露丝!”爸爸朝厨房喊,“是你把今天的头版给扔了吗?”
“我没有啊,亲爱的。”妈妈答道。
我躺在床上,屏住呼吸,期待爸爸就这么算了。他的怒气持续了一会儿,顺带骂了其他一些让他不顺心的事情,然后才坐下来看国家地理杂志。“妈的,”我听见他自言自语起来,“我是付了钱的,看都没看一眼就不见了。”
我朝蒂姆和迈克尔看了一眼,用手指比划出胜利的手势,“搞定。”我动动嘴唇,没敢出声。
第二天早晨,蒂姆和迈克尔还睡着,我醒了睁眼躺在床上,脑子里开始回想前一天发生的事情。也太巧了吧,我想,公园里那么多人,怎么就拍了我,还上了头版呢?最起码我没有像其他小孩那样扔瓶子啊。想到他会遇上什么麻烦,我忍不住开始偷笑。一切都结束了,想来觉得挺搞笑的。这故事可够精彩的,可以好好跟学校里那伙人炫耀一番了。他们会知道在赖斯修士学校的一年并没有让我改变。我都不用添油加醋,有照片为证啊,头版,照片的中心位置,还有随后的一场暴乱。警察甚至动用了催泪瓦斯。还有什么能比这些更刺激的吗?谁也不能否认我的这份荣耀。至于我之前担惊受怕的事情,都已经结束了。
正当我躺在那自我陶醉的时候,门铃响了。我听见妈妈的声音:“哦,丹教父!见到您真是太高兴了。快请进。来杯咖啡怎样?”是丹·沙利文教父。他是几年前来到我家所在的教区的一位助理牧师。我在教区的办公室做勤杂工,他是我的监督人。他刚
到教区不久就解决了一个祭台侍者盗酒的事件,措施得当,之后再也没有类似事件发生了。
丹教父已经是我家的一个好朋友了,他常来我家,而且常常是吃饭的时间。妈妈总是会加一副碗筷,他也总是欣然接受。他这点蹭饭的伎俩明显的很,不过妈妈并不介意。能和一位牧师在一起用餐,对妈妈而言是一份巨大的荣幸。而且能让牧师来家里吃饭,妈妈觉得她的厨艺在这片教区应该是数一数二的了。不过,今天丹教父并不是为了吃饭而来的。
“您看昨天的报纸了吗?”他问妈妈,“您看到约翰了吗?”他的声音听起来挺愉快的,就像刚刚发现我发表了一个告别演说一样,他应该是觉得我露脸了。
“约翰?我家的约翰吗?”妈妈还搞不清丹教父具体指的是什么,“在报纸上?” “就在头版!”丹教父的声音里竟然透出一丝炫耀的意味。 “看!”他带来了他的报纸,生怕我家没有报纸似的!老天!蒂姆看着我,脸上一副同情天底下最倒霉的倒霉蛋的神情。我又开始数数了,一千零一秒,一千零…… “约翰·约瑟夫·格罗根,你给我滚下来,立刻!”
我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抓起一条裤衩就往身上套。“我说立——刻!马——上!”妈妈咆哮着嚷道。妈妈的身高也就五英尺,不过当她厉害起来的时候,也是相当吓人的。我和兄弟们背着她给她起了个外号——“小拿破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