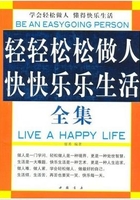大多时候,我都愧对于他们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信任。但是有一次我被错怪了,从那儿以后我再也不把他们的这种信任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了。
湖边的那棵吸烟树,除了作为我们这一伙儿人用来藏匿香烟、偷偷说脏话、存放从伯尼农场偷来的东西的据点之外,也是我自己一个人打发时间的好去处。我独自前往的那几次,最常做的就是坐在那儿盯着湖水发呆。从小,父亲就给我灌输了热爱大自然和野外的思想,我可以在小树林里坐上几个小时,幻想着野外生存的情景。我还是童子军时,父亲就经常带我到树林里去,教我怎样把太阳用作指南针,怎样用松树枝做成单坡屋顶,以及怎样从森林植被中找到可食用的植物。能找到的相关书籍我都读过了,我知道怎么用树枝做夹板固定受伤的腿。我还会用树藤编绳子、用鹿角漆树沏茶。生火是我最引以自豪的拿手好戏。即使再潮湿的环境下我都能找到引火的柴火,把柴火摆放得透气通风,然后小心翼翼地照看微弱的火苗,让它慢慢着起来。经过反复演练,我练就了仅用一根火柴就能把火点着的绝技。每次练习完我都小心翼翼地把火完全弄灭了才离开。
升入八年级不久的一个寒冷的秋日,放学后,我一声口哨叫上肖恩就直奔吸烟树。肖恩把鸭子都赶到了水里,从水底叼上来几块石头。我决定点个小火。我从白桦树上撕下几片树皮用来引火,又捡了一些易燃的干柴,把它们堆成圆锥形,只用了一根火柴就点着了,火焰上方飘起了几缕稀薄的烟。我坐在欢快燃着的小火堆旁,又开始幻想自己是在加拿大育空地区探险,浑身上下只有一把折叠刀和一块儿打火石。天色渐暗,太阳向湖面沉下去。我把小火堆弄灭,又把余烬踢到沙子里。二十英尺以外的水面上是邻居家的木头船坞,挤在边上用来过冬。船坞下面有几块烧焦的浮木和一堆乱七八糟的用过的火柴,看样子像是刚点过篝火。我在心里嘲笑道,哪个笨家伙用了那么多火柴才把火点着啊!除此之外,我一点儿也没多想。
我吹了一声口哨,唤过肖恩。想到自己在一个清爽的秋天的傍晚能带着自己的狗出游,我感到格外的兴奋,于是开始欢快地奔跑起来。我冲上陡坡,飞快地穿过野地往家跑去,那架势好比后面有一头发怒的狗熊在追赶我。肯定是我在狂奔的时候被辛普森先生撞见了。辛普森先生就挨着空地住,是所有邻居中脾气仅次于老彭伯顿先生的大人,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把我们一伙人从空地上赶出来。
不一会儿我就到家了。正洗手准备吃饭的时候,门铃响了。我打开门,发现是辛普森先生。他要找我爸爸说几句话。爸爸闻声走过来请他进去。他们俩在门口小声交谈了几句,然后爸爸走了出去,站在门廊上,并把身后的门关上了。两个人站在寒风中谈了一会儿,爸爸才又进来了。从他脸上的表情看,我知道出事了。
“你刚才穿过街道去湖边了?”爸爸开口问我。
“没错啊,”我说,“我带肖恩去游泳了。”
“你玩火柴了吗?”
爸爸知道我用一根火柴就能点火的技术。我惊奇的是他的措辞。我告诉他我点了一个小火堆,在旁边烤了一会儿火,临回家之前已经把它弄灭了。
“那你为什么跑呢?”爸爸又问。
我的大脑飞速地运转着,该怎么说呢?总不能说从火堆旁狂奔而过什么都不为,就是为了享受那种轻风拂面、心跳加速的感觉吧?“我就是想跑了。”我说。
爸爸这才说:“辛普森先生以为你想把他的船坞点着。他看见你跑过去,等回去看时,发现了一堆燃过的木柴和火柴,附近的木炭还有余温。你是唯一一个去过那儿的人。”
“爸爸。”我说。
“这不是小事,约翰。辛普森先生想报警。”
“爸爸,不是我干的。我也看见那些火柴了。真不是我。”
这些话听起来跟我之前撒过的那些谎一样苍白。没错,我是带着火柴去过那儿,也的确点过火,旁边的沙土里确实还有冒着烟的木炭,我也的确是从现场狂奔回来的,可是我是真的和这件事一点关系也没有啊!
“爸爸,真的,我真没……”
“我知道不是你干的,”他打断我说,“我会跟他解释的。”然后又加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相信你。”
这些年来,我有太多的理由让他不信任我。而这一次,也是第一次,我需要他的信任,他也的确给了我一份信任。他宁愿相信我说的,而不信一个大人的话。我真想扑到他怀里,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让他知道这次真的没有信错人。但是作为一个格罗根家的男人,我还是以格罗根家的人特有的方式表达了这种情感。不拥抱、不亲吻,甚至从不会说“我爱你”。我猛地向他伸出手,他紧紧地攥住,使劲摇了摇——一个结实的、格罗根式的握手。
“好了,吃饭去吧!”爸爸说道。
八年级很快过去了。临近毕业的时候,伙伴们都在议论升入距离果园湖路几公里远的一所新建的高级公立中学的事。那儿有游泳池、网球场、干净的跑道、阳光明媚的校园,还有音效很好的大礼堂。走廊上都铺着色彩鲜艳的地毯,也是为了增添活力。因为学校的建立得益于社区缴纳的税款,所以他们几个都去那儿上学。汤米要去,石头、布袋和狗仔还有周围所有的漂亮女孩都要去。我指的是所有人,除了我。
我的父母一直都把让他们的子女终身接受天主教式的教育这件事看得非常重,绝不可能让这种教育终止在八年级。他们给我在赖斯修士学校报了名。那是距离我家半小时车程的一所天主教男子中学,在底特律最富有的地区之一——伯明翰。去赖斯修士学校上学的孩子们的父母都是我曾经做过球童的那所乡村俱乐部的成员。他们是那种在十六岁生日的时候不是收到卡玛罗牌就是收到火鸟牌汽车作为生日礼物的孩子。在我之前,蒂姆和迈克尔已经去那所学校上学了,他们都给我描述过学校的修士们所使用的那些虐待性的惩罚条例,让人感觉毛骨悚然。相比这些新奇招数,圣弗历克斯的修女们所使用的那些倒显得老套过时了。蒂姆讨厌在那儿度过的四年,他提起那儿的严格、奢华、伪善和强行灌输的宗教教义就汗毛直竖。
如果说有一个因素能导致蒂姆对天主教信念产生敌意的话,那这个因素必定是赖斯修士学校,而我父母当初送他上这所学校的本意却是希望能增强他的天主教信念。迈克尔的传教热情在早些年就已经消退了,但他仍然热爱关于天主教的一切事务。他倒是在那儿待得很舒坦。而我,根本不想离开我的朋友圈,尤其是我那三个特别要好的死党。但是我还是接受了家里的安排。那儿是格罗根家的男孩该去的地方,就像格罗根家的女孩必须去玛利亚学校,一所只收女孩的天主教学校。玛利亚学校就在赖斯修士学校隔壁,和男校之间隔着一条护城河。玛丽乔和蒂姆目前正在天主教大学就读,迈克尔到秋天也会去一所天主教大学上学。看起来,这对接受天主教教育模式的我们来说都是注定的。在这件事上,我向来节俭的父母毫不吝惜口袋里的钱。
在被滚烫的蜡油泼过以后没多久,我就永远收起了法衣,不再做祭童的工作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选择不去参加弥撒礼。在我们家,做弥撒和呼吸一样重要,你必须无条件地去做。每个周日的早晨都是一样,妈妈总是用她的那支羽毛叫醒我们,一边挠一边说:“快醒醒,小懒虫们。该起床了,可不能赶不上做弥撒哦!”
几乎每个周日,爸爸都去祭坛边帮忙。他是传道师,负责诵读经文、传达病患者的意愿、唱赞美诗和带领众教徒做礼拜答复。他甚至还在圣坛围栏里帮忙分发圣体,就站在神父旁边。爸爸相当认真地履行他的职责,每次走过圣体跟前他都恭敬地屈膝半跪。他把头埋得低低地祈祷,竭尽全力大声地唱颂词。妈妈则跟他不一样,即使是教皇亲自要求,她也不能准确地把歌唱完。爸爸有一副好嗓子,并且丝毫不羞于把它展示出来。他闭着眼都能唱颂歌、背诵祷词,因为他把每句歌词和祷词都深深地印在了脑子里。每次献祭的时候,神父一向天举起圣体,爸爸就会深深地弯下腰,用一个拳头抵住胸口,好像见证了一个多么伟大、耀眼的奇迹。很难理解他能忍受在圣坛旁边待那么久,而他的虔诚却一点都不像是伪装的。有些人却不这么想,包括一个高傲的神父,据我们所知,他嘲笑地称爸爸为“圣理查德”。但是并非如此,他只不过是沉浸在自己信念的喜悦中。不管旁边有没有人看着,他都一样。爸爸很能熬夜,总是最后一个睡觉。有时候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瞥向父母的房间,都发现他在跪着默默地祷告。头埋在离他熟睡的妻子几寸远的被子里。他的虔诚不是装出来的。
我妈妈也一样。她在领圣体的时候必定会哭。我的意思不是说小声抽泣,而是大声号哭。就像知晓太阳会升起一样可以预料到她每次都这样。每次列队走过圣坛围栏,她都会双手交叠,恭敬地低下头,但是看起来却很平静。如果认出队伍里的熟人,她还会微笑着打招呼,甚至会挤挤眼。然而等她吞下圣体、回到长凳上重新跪下之后,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顺着脸颊流下来,就好像刚刚收到全家死于海难的噩耗。按规矩来说,所有人在受领圣体后都应该重新跪下,但是妈妈是以一种完全折服的姿势跪着:脸埋在手掌中,伏在前排座位的后面上,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脸颊滚落到地板上。天主现在就在她体内,而她根本无力抵挡这种召唤。
领圣体礼结束后,神父一般会在圣徒们继续跪着的时候例行公事地在圣坛那儿清理圣杯。清理完,他就会宣布:“请全体起立。”然后所有人都站起来了。所有人,除了我妈妈。她仍然保持着跪着的姿势,低着头,脸埋在手里,抽泣着,吸着鼻子,深深地沉浸在和天主的交流中。我小的时候,还觉得妈妈这种呼天抢地的架势很有意思,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最害怕那种在人群中引人侧目的感觉。我多么希望别人站起来的时候她也能跟着站起来,然后压低哭泣的声音。有的时候直到退堂诗都结束了,人都走光了,她还在埋头大哭。看到她这样真让人惊奇。
她完全地投入了,忘却了周围的一切。我惊奇于这一切是如此的自然——吞下一小块儿圣饼——竟然能引起那么大的情绪波动。我也想学。我吞下一块儿圣饼,使劲闭上眼,尽量想象天主就在我体内。但是我什么也感觉不到,除了感觉胃里有点焦灼,我想那是主在暗示我已经禁过食了,该吃早饭了。为什么呢?我想知道为什么我就不能像妈妈一样感受到同样的福佑呢?也许是因为我做错事情了。我极力地集中精神,学着妈妈的样子把头埋在手中,期盼着天主能进入我的灵魂。还是什么感觉都没有。即使天主真的来过,也是悄无声息地来的。我也不在乎了,很快我就学会了一边虔诚地做祷告,一边胡思乱想。
蒂姆有时从学校回来,我从未怀疑过为什么他总选择我父母没去参加的弥撒。然而就在一个周日全家照例去做弥撒的时候,我尾随在他后面,不经意地发现了他的秘密。他把我带到一边,悄悄地问我:“你是进去呢还是跟我走?”一开始我不明白他说的
什么意思,但是我很快就会意了。他根本不想去做弥撒。他也从来没去过。从那天我才得知,蒂姆早就在多年以前就不参加弥撒礼了,只要让他能逮到机会,他就会谨慎地溜掉而又不被爸妈发现。若是被他们发现了,肯定不得了。
蒂姆的一个打掩护的方法就是在弥撒开始的时候经过教堂,从门缝里往里看。他知道,爸爸总是会问是哪个神父站在祭坛上,并不是想考考他的孩子们,而是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他紧盯着神父们,就像是赌马的人紧紧盯着赛道上的马一样。为了在爸爸那儿签个到,蒂姆总会淡淡地回答一句“施罗德神父”或者任何一个蹦到脑子里的名字。
“咱们得盯紧了神父,那样咱俩就有一个小时可以打发了。”蒂姆说道,“我一般去圣玛丽高中溜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