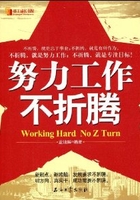惨淡一片月光之下,丰王爷当庭独立,思念正浓人已远。冥冥中,他总有些不安,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他此一生,活得刻意而兢兢业业,几度鬼门关闯过,也就无甚所谓有什么彻底失不得;及得终于随意些了,却不期然仍是命运棋盘上的子,规则面前动不得半步。
在王后怀孕之后,护国夫人自请带着孩子离宫去南州,丰毕岑如今记得她走时淡然回头,轻声问:“若当初世子妃不答应,你会娶我么?”丰王爷叹口气,摇头。池妙溪努力微笑,旋即调转头上马。她着初来邺城时的武士劲装,她扬起马鞭抹掉眼泪,道:“希望王爷自此不再如意,否则臣妾一生无法展颜。”
倾心一场,误得佳人一生,丰毕岑只是心中愧疚,而和风却哭得不可自抑,倒是吓坏了王爷与千伶。
此后,丰王爷常常想起那一幕,他估摸着,王后许是想起故人了,那俊逸如仙的男子,在睡眠中不曾与她道别,此去经年已五载,二人再不曾见过。待得一度原本能见了,他亦忘了。这样想着,丰毕岑心中多少有些不自在,却也不再逼她要那一句:“自始忘了南宫穆,只在心中装下我一人。”
扬州城,夏夜更胜白日,绕城而盘桓的河上传来阵阵丝竹曲乐,雕龙戏凤的游船多为乐坊或妓院,偶尔一阵凉风,便是脂粉之味。丰王后一行打算次日动身北上,此时睡不着,便领着千伶着男儿装扮随意走走,索然无趣中,便折回去,却不期遇上施施然等着的白万宁。
关于这美艳女子的情况,和风是知道的,木一事无巨细已经八卦过了,只是真见上还是另一番感觉。想当初,白万宁执意追着南宫穆北上,已经5年,彼时17岁年华的少女,眉目依然美丽,却是覆上了日久天长的化不开的忧郁。未及她走近行大礼,和风远远止步,遥遥施礼,道:“这许多年,谢谢姑娘。”
白万宁还礼,却为再动身,只冷声道:“他又不是王后的人,何苦您来说这一声谢谢?”
丰王后也不见外,她自白万宁身边走过,招招手:“进屋聊。”
待得二人进屋,千伶带上门侯于门口。
“本宫谢白小姐,不代表南宫穆,我没有权利代表他,我谢你,因为我想谢你,”和风亲自为白万宁倒茶,这姑娘令她想起池妙溪,热情如火又骄傲异常的女子,往往伤得最深。
白万宁盯着杯中水,苦涩摇头:“王后倒是有心。”
二人再无话说,只各自静默,最后白万宁终于行礼起身离开,对着和风道:“其实我只想知道自己输给了怎样的女子。”
和风摇摇头,背对她,声音清幽:“我们,总是在问同样的问题。其实,从来不关另外一个女人的事,在那么一个人正当情动的时刻,你在,他便爱上了你;你不在,他便爱上了别人。而所谓日久生情,不过是向岁月妥协,有人妥协了,有人却不会,所以,姑娘要善待自己。”
白万宁停下脚步,转过身,看向丰王后,又是许久。和风知道她听懂了,她能明白这样的姑娘,也渴望解脱,这样的生活,苦不堪言。她没有转过身,无声站着直到白万宁离开。
在见过丰王后的第二日,南宫穆不在她抚琴是练剑,而是走到她跟前,原地盘腿坐下,他满眼通红似一夜没睡,问:“白姑娘,你说你喜欢我是么?”
白万宁当时拼命点头,她从来不是矫情的女子。
“那是什么心情?跟我在一起会紧张么?”他懵懂问。
白万宁微微红脸,再次点头,她收回抚于琴上的芊芊玉手,抚于心房,看着南宫穆的眼睛,轻声说:“会,一直会。”
南宫穆微微皱眉,复又低下头,学着白万宁的样子手捂胸口自言自语:“我也紧张。”
白万宁闻言放下手,仰起头看着远方,而后抱起琴起身回屋。自此三日,她将自己关在房中,于是她夜访丰王后,于是王后告诉她:“姑娘要善待自己。”
最后,白万宁重重施礼,道:“王后,后会有期。”
第二日,白万宁返回和城,星夜兼程赶回去,老父携大姨娘二姨娘三姨娘,他们围着叫:“宁宁回来了。”白万宁拼命点头,继而大庭广众之下蹲下来掩面而泣,遥遥跟在她身后未曾现身的啸三见状正要离开北上追上王后一行,却见白万宁突然站起来,剑指他的方向,叉着腰叫:“丰王后还怕本小姐想不开不成?你给我出来!”
玄衣暗卫无奈叹口气自暗处走出,俊秀的脸上有些不好意思,暗卫当到被一个失恋姑娘识破,真够没脸了。白太守咋见这锦衣青年生得俊俏挺拔,突然眉开眼笑,一个眼色,三姑六婆围着这半辈子也不曾与人多言的青年。
百万宁秀眉一拧,跺跺脚,指着他道:“爹爹,我嫁他!”
白太守道:“女儿爽快!”
啸三脸一红,急急摆手,正欲离去,白太守一个纵身,原也是一身好武功,他右手扣住青年的手腕,左手抚须,连连长叹:“缘分啊,缘分。”
自扬州至和城,白万宁累了靠着马打盹,醒了又赶路,慢一步就怕自己改变主意。官道宽敞,总有人骑马跟着她怎会不晓?无论她哭,笑,吃东西,睡觉,还是拼命舞剑,这个男子总不远不近跟着,不曾说过一句话。
丰王后上得马车,与南宫少主及扬州太守就此别过,一个人静坐车内,她却没有下令动身。伸手一摸,腹部已稍微隆起,她手心冒汗,最后掀开窗帘,看向立于一旁送行的南宫穆,她欠他一世幸福,却无与言表,此生或许真正不再相见,她只静静看着他,眼中几道明灭,只是短暂的瞬间,她将一世不曾有过的任性用光。在这种目光中,南宫穆出奇安静,他只回望她,心中一点一滴被无可抑制的悲伤淹没,他点点头,别过脸。马车声动,和风不顾使节及扬州众官员,大声唤:“穆哥哥珍重。”
南宫穆身形一抖,剑柄在手心印出形状。如果不是今生,也当是前世,他想,他听过这一声“穆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