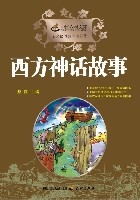待到时局稳定,政令通行,境内互通商贸,南慈王下诏,百姓税减三成,商贾可入朝为官,兴佛学,推书院。当然,这些政策由真正实施到初见成效,花了整整十年的时光。
护国夫人求救后,王军四千自邺州出发,赈灾疏渠泄洪于南州各主河道,围困护国夫人于州城河边上的流民起义军被告知,愿意加入王军抢修河道者,赦免罪行。来势汹涌的王军,以赈灾的名义和实际行动,震慑了起义军。若反抗,他们不仅要被消灭,而且背负百姓骂名;如不反抗,也不过是服从朝廷征召抗洪,成就国君美名。南慈王此招柔中带刚,令各州侯再次刮目相看。王爷解了护国夫人之围。
封王后手谕,王爷尚无子嗣,护国夫人不宜久战沙场,着令即刻回宫。这等于向另外一个女人承认自己无能力为丈夫繁衍后代,王后此诏颇让池妙溪有些舒服,她深知自己与王后都是要强之人,王后此番如此低头,恐怕是王爷授意。王后算是称了护国夫人之心,遂了王爷之意。
思及此,她快马加鞭回了邺州。王爷率近卫兵出城十里相迎,二人自此恩爱有加,一时成为朝堂上一段美谈佳话。
七月,护国夫人与两位贵妃先后怀孕,朝堂一片欢喜。只要三人中有一妃诞下男孩,王爷便有了世子,江山得以巩固。
风波刚平静之时,王后私心以为自此可以与王爷真的过上寻常夫妻那般相依相偎的生活。面对剧变,她一度陷入痛苦,日渐消瘦不堪,幸亏素来坚强,过了三个月也就说服自己平静下来。南宫穆失忆的消息五月传来,王后一人出得王城,爬上昔日二人话别的山峰,于无人处痛哭啼血,此后二月,她未与任何人说话。南慈王以为她吃醋与自己闹别扭,着令太医把脉,诊断结果是,王后真的失声了。王爷错愕,追及原因,太医敬畏王后,斗胆欺君,回曰:“偶感风寒未及时就医,细心调理便可恢复。”
千伶素来寡言少语,心中疼惜王后却也说不出更多安慰的话,只一心一意护着她与小郡主。护国夫人多次想来挑衅,她冒死阻夫人于殿外,不曾让她有机会靠近王后,以免这位恩宠正盛的夫人出言不逊。木一毕竟活泼些,每日伴在和风身边,王后修养好又说不了话,她便代替她将封毕岑和南宫穆骂了千百遍。刚开始,王后也就是失神看着她,慢慢地,她也会微笑,再到几位妃子怀孕的消息传来,她便摇摇头看着木一,手指蘸墨,写下:无关他们,我自当爱护自己,莫担心。
八月中旬,酷暑当头,蝉鸣至深夜。王后带着木一与千伶,在庆广殿外宽敞的大理石走廊上铺上了广玉竹席,吃着冰镇西瓜,纳着凉。王后已能说话,只是不宜久谈,便一人闲闲地坐在台阶上,看会星星,听会木一带着宫人们闲聊,心中是难得的清凉与平静。
子时,宣礼殿太监总管韦弗过来,声音发颤,跪地磕头:“王后,王爷有请。”
睡眼惺忪的王后没发现韦弗的表情异常,她来不及唤来千伶,便被啸骑二卫请上步辇匆忙赶去宣礼殿。
王爷独寝的殿外,齐刷刷跪了一圈宫人,和风皱皱眉,挥手让人都退下,自己施施然进得殿内。
沉香木榻上,锦帐和被子乱成一团,王爷披散着发一身白色丝质里衣衬得人雍容中透着慵懒,他坐在脚踏上,剑柄支撑于掌心,头靠在手背,落寞不安的样子。
王后猜不透他发生了什么事,便轻唤了声:“王爷。”
丰毕岑抬起头,木然看着她,有多久没正面或者不带情绪地看着她了,原来她已清瘦至此,下巴尖俏,五官更加分明,倒是有了些娇柔。月牙色夏衫罗裙,身影单薄得骇人。
见他不说话,王后稍微犹豫了一下,走到他跟前,在距离他几尺的地方就地盘腿坐下,而后安静看着他,不再说话。她的嗓子并没有完全好,即便不是这个原因,她也不知道该说或者不该说什么,所以,不说什么才最稳妥。
“没什么事,做了个噩梦就睡不着了,”王爷直直看着她,又像是眼光穿过她,看向远方。
“没事便好,”她微笑,点点头。登基以后,第一次夜晚被召来,和风此刻才意识到,她居然没有紧张,没有期待,也没有担忧,只是有些无奈罢了。不知道是第几次经历过来来回回的几道情绪辗转,很多次她也以为自己放下了,可最后又被推翻,这次,她却真的确定了。因为,心里没有轻松,没有庆幸,没有期待,只有浓浓的悲伤。她原以为能爱他一辈子,没想到自己也是信不过的。一次次掏出心来,被他践踏地上,自己又捡起修补,这次,却是碾碎了。
谁能够保证心不变,经得起风吹雨打,历得起沧海桑田?她心下冷笑,却是对自己,终是没有不变的情怀,原来自己也不过如此,那又和怪他呢?他连爱都没爱过自己,变卦便情有可原了。
“你没有话要跟我说吗?”丰毕岑皱皱眉看她一眼,实在太瘦了,不觉加了一句:“嗓子还疼?”
和风微笑,轻轻摇头,并无接话的意思。
封王爷尴尬放下剑,站了起来,无聊站了一会,又坐到床上,看了一眼满眼凌乱。王后连忙站起来,轻声说:“我给你收拾一下。”
为他铺好床,整理好锦帐,王后轻轻施礼,便要退去。宫服跐溜一声,她的手被王爷拉住,隔着袖子,苍劲而仓促。她惊讶低头,转瞬即逝的表情退去,她道:“睡吧,等你睡着了我再回去。”
他不松手,也不言语。酷暑退去,隔着袖子仍能感觉她周身清凉,殿外寂静一片,偶有巡夜殿卫士整齐划一的轻声脚步穿过,又伴随他们的远去而消散夜空,衬得深宫寂寥,令人心寒。
她复又抽了抽手,未果,便顺势坐在床边,僵硬地挺直着腰背,心下有些不耐烦。他躺着,只右手仍抓着她宫袖下的手腕,静静闭上眼睛,打算睡了。
“毕岑,你,还在恨我嫁给你了吗?”长夜漫漫,她实在不愿躺下,又挣脱不了,便一个人坐着胡思乱想很久,终于声音嘶哑,轻轻问了句,对着青黛如雾的夜色。明明是很没有安全感的人,丰王爷却喜欢卧寝不点灯火。
“不恨,”声音清晰,毫无睡意。
她惊讶他居然没睡,便动了动,侧着身子,看着他,声音中满是疑惑:“可是感觉你在惩罚我。”
“我说过,嫁给我不是你的错,”他回话:“只是你要的没要到,便觉得是惩罚,王后也太任性了。”
从未认真与他探讨过心中的种种猜想与委屈,如今听他一句话而已,和风便觉得茅塞顿开,暗夜中,她思考了一会,缓缓点头:“王爷说得甚是。我钻了牛角尖了。”
“不要害怕,你会稳稳当当做这一世王后,锦衣玉食,无忧无虑,”王爷看着床边的女子,她点头的侧影清晰,心中一紧,手下用力拽着她。
“其实你若能给我点别的就好了,”她闻言低头,轻声说,吼间痒痛,咳嗽一声,身体轻颤。这几个月,她似是走了一趟修罗场,期间多少内耗与损伤,只有自己明白。
“你还要什么?但讲无妨,”王爷轻轻放开手,看她一手抚于脖颈,一手抚于心房,再咳嗽了一声。她的身影似要溶于夜色化为无形,他一急,复又伸手,拽住她的衣角。
喘喘气,她轻声答:“自由。”
“换一样,”他闭上眼睛。
“我只要这一样,”她抬起头,看着夜色:“待得王爷百年,我在这深宫中,没有根基,也没有孩子,将是何等凄凉。”该怎么诉说,自己只是纯粹担心自己的将来,而不是你爱与不爱我这样的问题?
他久久未接话,她以为他终于睡着,便要去拨开他的手,却拨不开。
“我若百年,王后陪葬,”他的声音再度响起。
“这便真是惩罚了”
“王与王后,本就应当同生共死,共享天下。”
“那得以爱为前提。”
“王后又钻牛角尖了!你看我片刻不离手的那柄剑,而你是另外一柄,为什么要扯上爱?共穿吉服同拜天地那一刻,你我已算洒血为盟,这一世,我在,你在;我亡,你亡。”
“我若不愿意呢?”
“王后没有选择。”
“我不愿意。”
“你心里还惦记南宫穆?”
“王爷你钻牛角尖了,这与惦记谁又有什么关系?王后是你册封的,而我,在这王后的身份下,只是位普通的女子。我的梦想,不是与你并肩治理丰国,我的理想是与相爱的人组建一个家庭,我是他唯一的妻,我的孩子是他唯一的孩子。”
“那有何好?”
“王爷别告诉我你从未这么想过?以前没有想过娶凤止,与她生儿育女?那么池妙溪呢?没有过?你有过的吧,为什么你可以有,我不能有?她们能有,为何我不能有?你说这不是惩罚?那是为何?难道我做错了什么,注定没有资格拥有这些么?”
“因为你成了我的王后,以此为代价,你不能拥有那些。”
“全天下,只有我一位王后要付出这样的代价?我从来没听说别的王后需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除非你恨我,否则这说不通。”
“我不恨你,你没有对不起我。别国的王后,没有嫁给我,谁当了我的王后,都得这样。”
“如果当初是凤止呢?”
“你不可与她相提并论,她是我爱的女子。”
“说到底,还是爱与不爱的问题吧。你不爱我,所以不信任我,担心将来我挟孩子以令天下,是吧?”
“你这么理解也行。”
“毕岑,你不是残暴之人,却为什么自己看不出来,你这样做对我多么不公平?”
“相对于流浪宫外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这不算很为难你。你相通了就不会难过了,和风你是聪明的女子。”
“我也不爱你。”
“以前倒是爱你的,我自第一眼看到你,就爱上了你。但是现在我不爱你了。在这宫中多呆一天,我便多一份厌恶。”
“真是为难王后了。”
“确实很为难。你放我离开吧?”
“我说过。本王在哪里,你就在哪里。”
“你又钻牛角尖了。”
“你不过觉得,王后不在了,你无法向天下人解释,会丢了面子。但是,王爷你可以废后啊,然后放我走;又或者,你可以宣布我死了,然后放我走;又或者”
“我困了,”南慈王一转身,一使力,王后便被他扣住,卷进轻锦薄被。
王后真的开始焦虑了,正要往外挣脱的身体被他拢住:“王后也睡吧。”